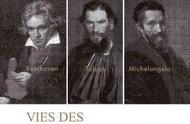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人,满脑子都是“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而第二次、第三次再听下去,这首歌就会在你的脑子里来回盘旋,干扰你休息。
“郭富城”、“BB机”、“霹雳舞”等等,这些90年代的流行元素,再加上一口大碴子味儿的蹩脚粤语,并非恶搞,而是对东北工业时代的追忆。
东北目前还看不到经济复兴的现实,反而让不少东北人没有了约束,没有了包袱,多了不少空闲的时间。
在这种背景下,新时代的东北文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野蛮生长,不断发展。
如果2017年的冬天,你曾去过哈尔滨,或许你会在大街上看到一群穿着印有不明所以英语单词的紧身上衣和一条紧身裤,露着脚脖子穿着一双豆豆鞋,一个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齐刷刷扭来扭去,嘴里喊着麦,旁边还有一个人拿着手机录视频。
他们就是宝石歌词里的“牌牌琦”。

牌牌琦的沙雕视频在快手上爆红,很多人都被这种“土味视频”逗得哈哈大笑。
很快,有了一群模仿牌牌琦的青年,穿着类似的服装,说着各种土味台词和情话,迈着半身不遂的步伐,摇头晃脑走向镜头,就是传说中的“社会摇”。
不久,社会摇又发展成为“摇花手”。
短视频让很多东北人发现,除了“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之外,自己还有可以发挥的“喜剧天赋”。
他们就像来颗华子的李会长一样,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这个新时代的漩涡。
喊麦、社会语录、迪厅迷情、disco金曲,成了东北男人新的情怀。

民国时期,“九一八”后,以萧军、萧红为首的一群文艺青年,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呼兰河传》、《八月的乡村》,还有《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激流》……
他们难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灾难,刻录着黑土地上东北人独特的“民俗”魂。

过去几十年的春晚舞台,东北人有不少时间都是台柱子,在年初就创作出一个个能流行一年的经典词汇,扎根于群众之中。
这些年,国家政策也止不住的东北经济的下滑,人才的流失出走,让东北人被迫或者半被迫地投身直播短视频的舞台,反而创作出了另一种别样的土味艺术。
时间改变了东北的经济水平和艺术形式,但改变不了的是东北人的幽默和艺术情怀。
来颗华子,一切都要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