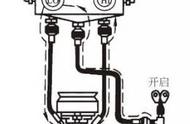俞敏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母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在杨志军老师的书里尤其明显,因为你的几本书都是以父亲形象来写的,我相信这里面或多或少一定有你父亲的影子。徐则臣老师写的《北上》,我觉得其中一定也有你小时候遇见的人物形象在里面。所以也想问各位,你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父母对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志军:我父亲是一名记者,解放前从西北大学新闻系毕业,西进解放青海的时候跟着部队到了青海,他在那儿参与创办了《青海日报》,然后就留在了那里。
俞敏洪:创办了《青海日报》?
杨志军:对,他们一帮年轻人一起创办的。当时的新政府希望他们跟着往西走,他们走到宝鸡创办了《宝鸡日报》,然后将其交给当地。接着走到兰州,又创办了《甘肃日报》,同样移交给了地方,最后跟着部队继续走到青海,创办了《青海日报》。
俞敏洪:你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化人。他出生的年月应该在一九二几年吧?老人家还在吗?
杨志军:不在了,他最后在青海去世的。
俞敏洪:你母亲呢?
杨志军:母亲还在,90岁了,她是一名大夫,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医生。
俞敏洪:《雪山大地》中也有体现,因为《雪山大地》中母亲的形象就是医生形象。那你的父母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后来喜欢读书是不是跟父亲是记者有关系?
杨志军:首先是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些藏书,那时候我看不懂,但没有别的书,就只能读他们,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时候很小,看不懂,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很多字我不认识,但我必须看进去,因为没有别的书。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水浒传》,《水浒传》是我的儿童启蒙读物,我看到的是仗义疏财,以及人的侠义精神。
俞敏洪:我们俩相似,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带点古代色彩的小说也是《水浒传》。
杨志军:此外,就是习惯,我们家都喜欢动物,爸爸喜欢动物,我也喜欢动物,我养动物他绝对不会反对,有时候会把草原的动物带回来养。
俞敏洪:在你的个性和气度上,你父母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杨志军:这个影响肯定很大,有个说法是,你出生后,谁第一个看见你,你的性格就会像谁。
俞敏洪:如果一头老鹰看见你,你就是鹰的性格,如果一只狗看见你,你就是狗的性格。这是藏族的说法吗?
杨志军:汉族也有这种说法,这是青海当地的说法,藏族和汉族都有。
俞敏洪:我怀疑你出生的时候,天上有头鹰看见你了。
杨志军:但我更希望是藏獒,或者是马,我喜欢马。鹰要飞起来,没有坚实的大地,这有些恐怖。
俞敏洪:那就是藏獒,因为你写的第一本最出名的小说就是《藏獒》。那对于乔叶老师来说呢?我从《宝水》中也读出来了,感觉主人公青萍身上是不是也有一点你个性的影子?
乔叶:也不能这样说,它是小说,小说是虚构的。
俞敏洪:你父母是什么样的背景,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乔叶:我母亲是一名民办教师,她快退休的时候才转正成为了公办教师。她教低年级,她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我估计她也是当时的完小或者初中毕业。
俞敏洪:我小时候上课的那些民办老师基本都是完小毕业就当老师了。
乔叶:对,所以她老教一二年级,但她教得特别好。我父母去世比较早,我15、16岁时父亲去世了,23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俞敏洪:从这本书中读到了一点影子。
乔叶:对,但小说中母亲一直都在。我父亲特别不爱说话,沉默寡言,他是比较早的大专生,学的地质,所以后来分到了焦作市矿务局,但我们家在农村,所以我父亲每天从焦作市里返回家中。那时候叫“一头沉”,形容主要家庭成员都在农村,但又在城里工作的情况,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俞敏洪:谁对你的个性,或者对你后来的阅读写作爱好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乔叶:好像都没有,我觉得不能说有很直接的影响。我父亲特别不爱说话,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在我十来岁很懵懂的时候,他得了重病去世之后,我觉得他是以他去世的方式,以他的沉默,来显示了某种存在感,我会不断想起父亲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当初不跟父亲多说说话?
乔叶:我们父女之间说话都很少,我母亲是非常单纯善良的人。书里有写我奶奶,其实直接对我有特别深沉影响的是我的奶奶。
俞敏洪:果真现实中有一个奶奶,我从你这本书中也能看出来你对奶奶深厚的感情。
乔叶:对,她直接管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父亲在焦作市上班,我母亲也整天都在忙工作,我们算是双职工家庭,所以我们五个孩子都是奶奶亲自带大的。
俞敏洪:我姥姥对我也有隔代影响,因为我小时候有很长时间跟着姥姥。
乔叶: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同时又很普通的北方乡村老太太,她基本不识几个字,但她有一种特别传统的美德,非常勤劳、勤勉、节俭,但她有她的封建。
俞敏洪:我们三位的父亲都已经不在了,如果现在回过头来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有哪些大家没做,现在想来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杨志军:在他去世的那天我没待在他身边,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当时青海妇幼保健院刚成立,我母亲带了几个人到北京学习,那个阶段我一直跟父亲在一起。我母亲回来那天晚上,我就回家去了,就那天晚上,我父亲去世了。那时候没有电话,不好联系,第二天早晨,有人通知我赶紧到医院去,我从西宁城的西边一直到东边,骑着自行车穿越整个城,但我到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这是我很大的遗憾,那天晚上不应该离开他,应该一直陪着他。我陪着他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很多他的历史,他自己的故事、家庭,以及他对我的希望等等。
乔叶:这个还蛮难过的。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正在上师范。我父亲住在焦作矿务局医院,两个地方离得很近,我就去看他。后来他病得很重但还能走路的时候,他就说要跟我散散步,但我记忆中好像就散了一次步,因为散步的时候会在路上碰到我的同学和老师,所以我不太情愿跟他散步,再后来他就没力气了。他是很传统、严肃的父亲,我们之间就没有很温馨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
俞敏洪:其实越是严肃、传统的父亲,他的内心越想和子女亲近,但他不知道怎么亲近。
乔叶: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也是很常见的中国式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会表达感情。我们散步时,我父亲表示他认为我和弟弟没有着落,尽管我已经上了师范,将来一毕业就有工作,但他还是表示担心。但我觉得当时可能还是有小女孩儿那种难为情,不希望同学看见我在跟父亲一起散步,就希望赶快回去吧。现在想起来,就觉得非常难过。

俞敏洪:我有类似的感觉,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得了肺结核,我母亲跑到北大来看我。她让我陪她在北大校园散步,我就是不陪,我觉得所有女同学看见我陪妈妈散步,好像不对,人家都是成双成对地散步,结果我陪着一个老太太散步,不行。
我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最后三年没有陪父亲喝过酒。我在北京工作,父亲在乡下,我当时也没有钱,也难得回去,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回去。老头子特别喜欢喝酒,但我当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我每年回去上坟,都会买一瓶茅台酒,直接浇在坟头。
杨志军:你父亲活着的时候,肯定不喜欢喝茅台酒,北京二锅头肯定最合适。
俞敏洪:你知道我父亲喝什么吗?我姐姐是赤脚医生,他就用医用酒精兑水喝,但我就想让老头子在天之灵喝点好酒。则臣的父母对你有过怎样的影响?
徐则臣:我觉得我父亲对我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因为他非常严肃。他是乡村医生,天天上班,特别忙,平时又板着脸,小时候我觉得我父亲特别严厉。这个状态“遗传“到我的时候,我经常会想,我儿子看我现在是不是就像我当年看我父亲那样。
俞敏洪:你会这样吗?我觉得你还挺慈眉善目的。
徐则臣:还是不一样,这就是父亲,我肯定是我儿子的底线,一说他还是有点害怕。我母亲是山东人,是最典型的山东女性,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母亲的性格。我从小到大,不记得她对我红过脸,更是不可能骂过我、打过我,所以我反思自己跟儿子的关系时,我都会以我妈为标准。
俞敏洪:那你从小到大谁给你定规矩?感觉你小时候应该比较顽皮。
徐则臣:是我爷爷。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跟爷爷奶奶住一起,虽然我们那时候在农村住在一起,但中间有道围墙,我就住在我爷爷奶奶那边,常年跟他们一起住。
俞敏洪:那就是爷爷给你立规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徐则臣:对,我爷爷解放前是小学校长,后来被打成右派,回老家生产队喂猪,后半辈子基本都在喂猪,后来又平反了,所以他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俞敏洪:所以你的阅读习惯也是受爷爷影响吗?
徐则臣:对,我小时候读的书主要是《中国老年》和《半月谈》两本杂志。你很难想象小时候读《中国老年》和《半月谈》,因为我爷爷就订了这两本杂志,我们那时候没什么书。刚才杨志军老师说小时候读《安娜·卡列尼娜》,这在农村完全不可能,我都没有想过能读这种书。
俞敏洪:你父母还健在,你要吸取我们的教训,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多为父母做点事情。
徐则臣:对。
俞敏洪:也想对大家说,有时候表面上父母和我们之间言语并不多,但他们的内心对我们有着热切的期待,希望孩子走近他们、靠近他们,这种心情,其实每个父母都有。希望大家,都能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多尽孝,多给他们一些笑脸,多关怀他们一下,多打电话,现在交通也很方便,如果没住在一起,就多去看他们几次。这样的话,等到最后他们慢慢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的内心才不会有太多遗憾。这就像我们常常说的,父母在的时候,有一堵墙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父母不在了,这堵墙就没了,突然你就要直面这个世界的尽头了。

俞敏洪:我们来讲一讲各自成长的时代,到底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影响,给你们的小说写作和人生价值带来了怎样的一种影响?
杨志军:我40岁去了青岛,到青岛后最大的印象就是新东方。当时我女儿要上学,我就想到底送不送她去留学,所以就特别关注新东方。我也知道新东方有一个“新东方精神”——“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我就想,这句话到底是“绝望“生了”希望“,还是“希望”生了“绝望”。
俞敏洪:“希望”生了“绝望”。
杨志军: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只有有了希望,才会绝望。比如你要生而为赢,你要永不言败,你要追求卓越,你还要挑战极限,那你就充满了希望,但你每走一步都是绝望。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循环,你在绝望上再造一个希望,这个精神的启发很好,每个人从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这是一个循环。但它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循环,是螺旋式循环,每一次循环结束后,你会发现又在一个新的高度。
俞敏洪:这里面有深刻的哲学和宿命论。
杨志军:因为讲到时代性,作家面对的是语言,写作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要有现代性,所以就从你的作品里想到了时代性,想到了新东方给我的冲击。
俞敏洪:新东方居然能给中国的大作家留下冲击,谢谢杨老师,大家都说“遇到高手了”(笑)。其实有一点,没有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正是人心中有了一次一次的希望,在现实中才会遇到绝望,而遇到绝望恰恰表明你内心有希望,并且有希望再次变得更好的希望,这个是对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说,俞老师,你把这个口号改了吧,“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现在国泰民安,哪有什么绝望?我说绝望是一种心理,全世界大富翁跳楼的最多,为什么?不是说他没钱,不是说他生活不富有,不是说他没车开、没饭吃,而是他内心的一种心境,一种心理状态,他的心中找不到希望了,觉得有困境解不出去了,这个时候能把你从困境中拎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远方有一盏灯在等着你。
我相信在杨志军老师身上或多或少还是会有时代的烙印,因为你懂事的时候,十年特殊时代还没有开始,到十年特殊时代时,你已经懂事了,我相信你父母应该也受到过冲击,后来又遇到改革开放。你觉得你是生得太早、太晚还是恰逢其时?你作为50后,经历过的这60到00年的时光中,你觉得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杨志军:我生得刚刚好,一切都是合理的安排。
俞敏洪:这个有点禅宗的味道,一切都好。
杨志军:因为是宿命,你必须认同宿命对你所有的安排。我觉得整个时代,它其实给予了我一种创作文学的可能。那时候改革开放,有那么多作家写作品,那么多作家每一部作品都畅销,当时我是一个小文学青年,这是很刺激我的。
俞敏洪:乔叶老师,你出生以后经历了完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时代,为什么你还会专门回去写农村的时代变革,而不是写城市的时代变革?
乔叶:我觉得“时代”这个词特别大,但体现在我们个人身上,小命运和大时代其实也是密切相关的。每个人都跟时代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以我个人的命运而言,我们都知道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有学校图书馆,有阅读的条件,我们知道什么是文学,对好的文字有感受。然后90年代初,我在乡下教书,看到《读者》杂志或者《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写?虽然我在河南省修武县某个乡某个村里教书,非常基层,但我能够看到这种文化信息。所以我开始投稿,然后就发表了,这极大地鼓励了我。《中国青年报》当时一年能给我发十几篇,还邀请我去采风。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觉得这是时代的福利。
俞敏洪:其实你写作是从散文开始的,然后因为受到了正向鼓励,就不断写下去了。
乔叶:对,写生活散文,最早的鸡汤文章,那时候可爱讲道理了。再后来就开了专栏,然后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我出了第一本书。
俞敏洪:那我就有点明白,为什么你的小说会带有非常舒服的散文色彩了,所以我把你的《宝水》称为“散文式小说”。
乔叶:我的确是因为文学改变命运。我先到县里工作,后来又被河南省文学院调去当专业作家,在郑州工作了二十年,然后又人才引进来到北京,其实都是因为写作。
俞敏洪:因为文学,所以改变命运。
乔叶:对,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给了各种机会,才有这种个人命运的变迁。这也是双向的,我虽然离老家越来越远,但我童年和青少年的乡村经验一直在我内心封存。后来我写《宝水》是因为,2014年我到河南南部的乡村去看,感觉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跟我过去的乡村很不一样,它能触动我。我对我过去的乡村其实特别不理解,虽然那时候在那儿生活,比如乡村的很多礼俗,“人死比天大”,两家有仇恨,但这家人有人去世了,那家磕一个头,立马就得化解仇恨来帮忙。
俞敏洪:因为乡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他不可能永远仇恨,否则就会变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仇恨,所以一定有各种方式化解。
乔叶:对,乡村的道德、宽容感,还有人情礼事中各种丰富的东西,都是我当时不理解的。但故乡是离开了才能拥有的地方,离开之后反而有回望的距离,也就慢慢有了理解的能力。我又看到了当下乡村的这种状况,所以我其实一直想写一个比较完整的链条。我内心有个过去的乡村,我不理解它,现在到一个新的乡村,一个他人的乡村,再去理解我的乡村。

俞敏洪:通过理解他人的乡村,来理解自己的故乡,《宝水》中明显体现了你的这种想法。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你觉得哪个十年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十年,或者对你来说最值得的十年?
乔叶:都很重要,你没有这个十年,就没有下一个十年,人生一定是这样递进式的成长,每一环都必不可缺。
俞敏洪:如果让我来拆分,我有两个十年最重要。第一个是1-10岁,在你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农村所有好的、坏的,都已经在你身上沉淀下来了。另外就是在北大的十年,也就是1980到1990年,那是我整个思想、价值观改变的十年。之后的一切都是这两个十年拼装起来往前走的。
则臣刚出生就进入了80年代了吧?因为我能在你的小说中看到时代对你的烙印,比如你写中关村、海淀,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时代烙印。
徐则臣:对,我1978年出生的。
俞敏洪:你觉得这个时代给你带来了什么?你人生中哪个阶段对你的写作或者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最大的影响?
徐则臣:如果我不是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时代,就是大家共同感受到的那个时代。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我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大时代,就是完全跟个体无关的宏大,它会按照自己的规律、逻辑去运行的大时代。同时还有一个个体的时代,我个人的个体时代,以及我触及到的每个人物的个体时代。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把人物的那个“小时代”搞清楚,同时让他的“小时代”跟“大时代”之间产生某种张力。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遵守的写作原则。
俞敏洪:《北上》一直从1901年跨到了2014年,跨了这么大一个时代,你怎样通过微观故事的串联把这些年代串起来?
徐则臣:比如写1901年那一段,1901年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王树增写过一本非常厚的书就叫《1901》。当时是晚清,我觉得这一年是中国近代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肯定是从大时代的角度来讲的,但在这个时候,一些小人物,他们感受到的日常生活跟这个是什么关系?小说中的小波罗,意大利人,他在1901年来到中国,沿着运河北上的过程中,他所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中国,那个时代东方的文明,跟整个世界或者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宏大叙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一定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一定可以形成张力,小的时代可以嵌入大的时代里面,然后一直延续下来。
俞敏洪:所以《北上》其实嵌入了好几个时代。
徐则臣:对,通过某一个信物,比如小波罗当年留下来的一些信物,这个信物不断地传承,把几个时代串了起来。信物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可以被忽略,但它带着一个小时代的细节,通过小时代的细节变迁,把整个宏大的时代给呈现出来了。
俞敏洪:我读《北上》时有一个感觉,五家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后因为某种宿命,比如因为运河,把他们连接在了一起。是不是在你个人价值观中,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冥冥之中其实会有某种命运的连接,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血缘关系?
徐则臣:我觉得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那样一个时代,整个运河是我们所有人可能建立联系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因为它当年是贯通南北的“高速公路”。
俞敏洪:如果没有运河,中国可能就没有这么完整了。
徐则臣:对,隋唐运河开凿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趋势,虽然中间也有反复,但总体上是大一统的。大一统靠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贯通,靠着一条河贯通,把一种皇权的威仪贯通下去,把一种民族的认同感贯通下去,把一种文化的认同感贯通下去。所以这条河对于连接所有人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奔波的人,你可能都会在某一个时间,在这一条河上,经过同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相遇是很有可能的。
俞敏洪:其实有这么一个说法,中国历朝历代,除了宋朝相对贯通性稍微差一些以外(因为辽金的存在),从隋唐以后到清朝结束,中国其实基本形成了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局面,而这跟这条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铁路和海运都是到了清朝末期才产生的,在那之前,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统一的命脉,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徐则臣:我同意,中国的河流在大运河南北贯通之前,五大水系全是东西方向,把中国切成了六瓣,当时也没有现在的架桥技术,比如建个长江大桥、一桥、二桥、三桥来做连接。三国时期东吴划江,只要划了那条线,这个国家就可以偏安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一条河完全隔绝了两个世界。但运河把这些河全部连通了,比如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
俞敏洪:把东西向的分割变成了南北的贯通。
徐则臣:贯通以后,所有的东西、物流、交通就各种融合。比如在欧洲发现的关于中国最早的一幅地图,那是马可波罗之后,整个欧洲对中国的想象,那个地图水系密布,他们想象从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上船,不下船就可以走遍整个中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条大运河,所以后来阿姆斯特丹、彼得堡的运河的设计,都取法于中国的大运河。
俞敏洪:所以中国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运河的一个示范和榜样。
杨志军:运河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它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命运,这个特别重要。
徐则臣:因为融合必须要建立关系,建立关系靠的是什么?靠的肯定不是隔绝,而是联系,把它贯通起来,连接起来。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说长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父亲河,但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这条运河南北贯通,其实对整个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包括对我们的文化。
俞敏洪:以吸引人的故事情节、跨越一百多年的时代,专门用小说的方式写运河的故事,好像仅你一人。
杨志军:运河也是母亲河,按照藏族的说法,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些是“阿尼”,是爷爷、祖宗的河,运河不就成了母亲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