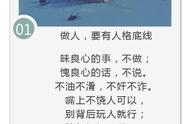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崔俊杰
日前,河南省招生办通报了2018级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全省违规考生处理情况。全省共发现违纪舞弊考生69人,其中由省招办通过网上巡查和评卷过程中发现并查实的违纪舞弊考生22人。河南对违纪舞弊考生作出取消其单科或全科的考试成绩,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的处理。通报称,希望各地引以为戒,在今后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的诚信教育,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考试管理,促进考风考纪进一步好转,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成绩可信可用。
强化诚信考试,拒绝考试作弊,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很多年前,一些高校就加重了对考试作弊的处罚力度,将考试作弊与学生的学籍学历学位挂钩,由此还引发了一系列广受关注的教育行政诉讼案例。惩治考试不端行为的目的在于维系社会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考试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建设向来离不开道德和法律。道德是内卷的,体现为人内心的确证;法律则是外化的,体现为具体化的、可预期的权利和义务。就治理考试作弊而言,法律层面的要求不可谓不重。比如,针对国家考试作弊的行为,我们甚至亮出了刑罚的利剑,规定在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将有可能构成重罪。至于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类规范性文件,更是与日俱增。在道德层面,我们也从来没有放弃教化之功,不管什么类型的学校,都已经把诚信考试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融入课堂教学、综合实践、主题活动、考前教育等日常性教育活动之中。
事实上,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治理一样,治理考试作弊等不端行为本质上还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执纪和守纪之间,并不能时刻保持平衡。比如,技术的进步使得考试不端行为变得越来越隐蔽。相应地,让这些劣迹曝光的成本也就变得越来越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某种程度上讲,要提升执纪的效益产出,自然需要不断加码违纪的成本,使之变成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从而自动产生震慑,形成阻滞效应。基于此,近年来,我们已尝试着将经济领域的征信溢出于社会建设的领域,通过打通信用信息的传输机制,触发黑名单管理、联合惩戒等措施,以达到扩大违法违纪后果的效应。前述河南省考试部门便是在取消违纪考生单科或全科的考试成绩的同时,将有关失信记录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信用工具是一种治理考试不端行为的巧办法、好办法、管用的办法,但也要看到,法学界对信用工具的性质、界限等关键性问题尚存争议。基于此,如何既对考试不端动真格,又始终不脱离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是诚信考试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一方面,加大对考试不端行为的惩罚力度,使考生不敢作弊,仍将是一种趋势。不过,当记入考生诚信档案等信用归集手段与未来对行为人主体实施差别化管理、启动联合惩戒相关联时,有关负担性义务的设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并赋予行为人必要的程序和实体权利。不仅如此,惩戒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为此,还应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为记入诚信档案设置必要的“洗白”期限。在这方面,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起到了示范作用,未来,应推进类似规定在其他考试领域制度化、规范化。
另一方面,记入考生诚信档案等信用治理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个人道德的某种外在评价机制,它使得更容易在熟人社会发挥作用的道德评价,通过征信的手段在陌生人社会得以外化,进而对行为人产生制约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讲,信用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红利。良好的信用累积对于考生而言,将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因此,考纪教育不应只是单方面的“苦口婆心”、道德教化,也应通过“告知承诺”,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后果可预期”的要求。“作弊风险高,后果须自负,承诺要兑现”,以此引导考生强化对自身主体责任的认知,诱发主动遵从,促使其不愿作弊,仍是实现治理的核心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