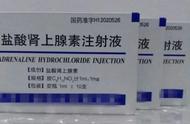“正史”以外,私家撰述中的碑(如墓表、墓志铭、神道碑等)、传(哀启、行状、家传、传略等),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国史学撰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集录碑、传为一书,始于宋代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明代以降,又有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徐纮、王元编《皇明名臣琬琰录》《续录》。清至近代,则有钱仪吉编《碑传集》、缪荃孙编《续碑传集》、闵尔昌编《碑传集补》、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金毓黻说:“裒录碑传以为一编,莫先于宋杜大珪之《名臣碑传琬琰集》。元人苏天爵继之以作《名臣事略》。明人焦竑之《献征录》,亦其伦类。清代则裒录亦多。嘉定钱氏经始于前,江阴缪氏嗣响于后,以成正、续《碑传集》。李氏《耆献类征》,亦用此体。近人闵尔昌又辑《碑传集补》。皆以清代为断。闻番禺汪兆镛亦续《碑传集》,未及付梓。闵氏辑《碑传征遗》,存稿待刊。又仪征阮氏曾纂《清碑版录》,未闻行世,殆见缪《集》而辍。若斯之类,盖更仆而难数也。”①事实上,宋明以来,集录碑传为专书者,概不止此。进入民国,国史馆有纂辑《民国碑传集》之举,惜未成书;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研究,曾辑《南明人碑传集》一卷,事属草创;滇人方树梅辑成《滇南碑传集》与《续滇南碑传集》两书,乃区域性碑传集。新中国时期,钱仲联辑成《广清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与《民国人物碑传集》。历经五百余年,集录碑传事业递相祖述,屡有纂辑,使得这类著述蔚然成一系列,成为我国史学园地中的一朵朵奇葩。
可以说,自宋明以来,集录碑传已成为我国史学的一种学术传统。已故中国史学史专家罗炳良教授云:“在中国史学史上,搜集碑传资料与利用碑版证史的传统由来已久。然而史家形成自觉的史学意识,使之成为连续不断的史学活动,则是从南宋史家杜大硅编纂《名臣碑传琬琰录》肇端。”②而白寿彝先生更早指出:“就过去某些史学著作跟原始史料的关系来说,他们有的是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作出了有系统有体系的历史著作……我们不应该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看作史料,而应该看作值得研究的观点或意见。”③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它们视为史料,更要从史学撰述的角度加以审视。同时,对这种史学现象或史学著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我们继承我国史学遗产,推进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方法。
一、集录碑传的条件
集录碑传是一件历时长久、十分艰辛的基础工作。一般来说,碑传集的搜集整理者,或是史官曾经参与史馆工作,或从事史学撰述的学者,抑或近现代的文史专家,本身大都“是有名的学者,交游很广,向人征求碑传,有靳而不予者”④;直至成书,历时较长,经常是“数十年如一日,惨淡经营,殊非易事”⑤,耗费了整理者的大量精力、智力、物力、财力等。如钱仪吉纂辑《碑传集》,从清道光三年(1823)开始,到光绪三十年(1850)过世之前,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功夫,才完成草稿;后经诸可宝校订,交由浙江布政使黄彭年刊刻行世。缪荃孙再辑《续碑传集》,则从光绪七年(1881)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完成,前后历时三十年最终成书。闵尔昌拾遗补缀,作《碑传集补》,编纂时间长达十年,“时作时辍,遂将十年”⑥,直至民国十二年(1923)刊印。还须家人、学生等作为助手,或提供佐助。钱仪吉外孙沈善登追述《碑传集》编纂过程,云:“方事之殷,四出借书,不得,则命驾厂肆,捆载满收,至无容膝地,则跨辕而归,众手分抄,伯舅助翻检,克日还之,易所未见,以为长。而先母所写最速且多,公赐诗有‘兼旬为写百篇书’,即此事也。”⑦卞孝萱、唐文权共同编辑《民国人物碑传集》,卞“妻段子宜女士、文权夫人洪宝珠女士以及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几位研究生用简化字抄写”⑧。
当然,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如前人所撰碑传已有一定量的积累;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学术传统的惯性;学者个体的较高认知和学术追求,即乐意从事这样的事业。
集录碑传首要的条件之一,就是须有大量的碑传存世。只有大量碑、传存在之前提,才有集录成书之可能。那么,碑、传何时出现呢?顾炎武说:“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又说:“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⑨也就是说,没有作史之职、作史之权的人,即不具备为人立传之资格,于是就变相采用写作碑、志、状等方式,以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章学诚对顾炎武的说法予以反驳,认为自古文无定体,经史不分,像《春秋》三传与大小戴《礼记》,或“依经起义”,或“附经而行”,“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又说:“夫后世文字,于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⑩
相关研究认为,传之产生先于碑,“碑传之始,匪特记人。专以记人,则传先于碑。《世本》中已有传。《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孝文传》。《史记·伯夷列传》引伯夷、叔齐古传,皆在司马迁七十列传之前。是传之作,起于先秦,碑则汉始有之。今汉碑传世尚多,蔡邕犹擅斯作,其《集》可征”(11)。四库馆臣则称:“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12)据清人赵翼爬梳,裴松之注《三国志》征引私传,若《曹瞒传》《郑玄别传》《荀或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虞别传》《任昭别传》《钟会母传》《虞翻列传》《赵云别传》《费祎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以及何劭作《王弼传》、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机作《陆逊铭》、《机云别传》等(13),不下三十种,可见其数量之巨大。
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六朝以后,碑传文大量产生,“沿及六朝,文体加缛,定谥有诔,表墓有志,策哀有词,起自朝廷,被于闾巷。唐有天下,昌黎韩愈,以文章雄视百代,鸿篇巨制,多出其手,碑传之作,于斯为盛。历宋元明清,其流愈衍,其制愈奓,私家而僭史官之权,及身而制薶幽之石,至于今日,几于人各一碑,家各一传”(14)。且隋唐以后,文人学士竞相替人撰写碑志、别传,相沿成为新的社会风尚。所以,当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碑传文献,集录碑传成为专书才有可能。
其次,集录碑传可能受到学术发展的影响,或受到史学活动的刺激。两宋之际,杜大硅辑成《名臣碑传琬琰集》,不是偶然的,可能受到了金石学研究的影响。“宋代以前的历代学者尽管也有人著录、记载和研究金石文字,但都是一鳞半爪,不成体系。两宋时期的学者不但广泛收集金石碑刻,而且撰写了不少专门研究著作,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创立了金石学。宋人开创了以金石与文献互证的考据方法,在中国历史考证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杜大硅才能把这些零散的撰述加以汇总,升华出自觉的历史编纂意识,汇集成《名臣碑传琬琰集》”(15)。
焦竑编纂《献征录》,正值晚明当代史撰述由勃兴到繁荣的过渡期。万历年间,焦竑充任本朝纪传体国史纂修官,利用修史余暇私纂《献征录》,“癸巳,开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条四议以进。史事中止,私成《献征录》百二十卷。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16)。似亦可理解为焦竑当时已有私修国史的准备,及修史中辍,辞官归里,“若而年不忘其初,凡所睹闻,佥命掌记,时为缵辑”(17),最终辑成《献征录》。
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续集》,则缘于他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氏早年撰著《晋宁乡土志》《晋宁州志》,编辑《滇文丛录》《滇诗丛录》《滇词丛录》;撰著《师荔扉年谱》《杨文襄年谱》《钱南园先生年谱》;选印《滇南书画录》,并撰小传;与云南当地文化名人赵藩、陈荣昌、秦光玉、袁嘉谷、赵式铭等编纂《云南丛书》《云南通志》。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他见钱、缪、闵三家碑传集“于滇南人物,所收寥寥”,“欲思博访吾滇碑传,都为一集”;为此“出游南北十余省,搜访文献,关于滇南碑传所获尤夥”(18)。最终将汉至元滇南人物编为《古滇人物考》,明清两代人物编为《滇南碑传集》、民国至解放初人物编为《续集》。
二、集录碑传的史学旨趣
学者著述或辑成专书者,率多受到时势激发而有为之作。也就是说,这类著作的编纂,大都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宋明以来,碑传集类著述的编纂者,同样具有强烈的经世目的。正所谓“古之良史,多资故典。会粹成书,未有无因而作者”(19)。只不过我们以往考察这类著述的成书过程,不甚关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这类著述进行综合考察和纵向比较,即可注意贯穿于其中的治学旨趣。
集录碑传主要出于征文考献的根本目的,即为了实际利用而辑成专书。杜大珪“顾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20),于是辑为《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分作三集,上集27卷(神道碑),中集55卷(志铭、行状),下集25卷(别传,采自宋人文集,间采于实录、国史),起于北宋太祖建隆、乾德年间,止于南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
《献征录》之辑,四库馆臣据书“前有自序,谓明代诸帝有《实录》,而诸臣之事不详,因撰此书”。又说:“盖宋人《实录》之体,凡书诸臣之卒,必附列本传,以纪其始末。而明代《实录》则废此例。故竑补修之。”(21)焦竑友人顾起元说,焦氏处境正像唐刘知幾当年一样的境遇,“身为史官,以作非一人,诒书僚长,徒抱汗青无日之叹”,退出史局以后,“犹思储一代之史材,以信今传后”。(22)这一说法似更符合事实。考焦竑特别关注本朝纪传体国史,屡称“古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时事”,认为当代史编纂的意义,正在于“作者代兴,胜劣互异,然莫不钩深故府,囊括辞林,一代兴衰,赖以考见。傥谓迁、固亡而无史学,不亦谬乎!”(23)故《献征录》120卷,涉及800余人,考“献征”之义,就是“征文考献”,全书时间上跨越元末明初至万历末年(24),采集传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铭等。且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堪称明代历史文献编纂的大成。四库馆臣称许道:“自洪武迄于嘉靖,蒐采极博”,“自王侯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缁黄、僮仆、妾伎,无不备载,人各为传。”(25)
至于五部清人碑传之集,亦无不立足于征文考献之目的。钱仪吉鉴于清朝自天命以来的历史人物载诸本朝纪传体国史,藏于金匮石室,外人没由得见,他虽然参与《清会典》的修纂,“幸获展观,亦不敢私有写录”,于是“采集诸先正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得若干篇”(26),辑成《碑传集》一书,收集清初至嘉庆年间2000余人的碑传。缪荃孙鉴于“至嘉庆朝为止,迄今又九十年,中兴伟绩,贤才荟萃,长篇短牍,记载较多”(27),继起辑为《续碑传集》,收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1100余人物的碑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则补录钱、缪二书所无的810余人的碑传,以清代人物为主,兼收民国人物,作为二书的补充。汪兆镛《碑传集三编》试图在缪书之外,另起炉灶,别为“钱、缪两书之续”,搜集清末400余人的碑传。通计以上四书,共收录4000余人的碑传,且取材广泛,有行述、行状、墓志铭、墓志、墓表等多种材料,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大型文献汇编。
然而以上四种碑传集之编者,受其时代之局限或阶级之偏见,难免存在有意排斥或各种失收漏收的现象:
重要人物如名儒黄宗炎、顾祖禹、颜元、毛奇龄,史学家全祖望,古文家鲁九皋,诗人屈大均、谢启昆、丘逢甲,书法家王文治、邓石如,画家陈洪绶,俱未收入。已收入人物之重要或最重要传记往往失收,如于钱谦益,未收顾苓所撰《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朱彝尊,未收其孙桂孙、稻孙合撰之《祖考竹垞府君行述》,而二文皆详确之长篇。至于清初大量遗民碑传,失收者更为指不胜屈。四种碑传集之编者俱为封建时代之士大夫,观点陈旧,已收之忠节、列女各类中,多不必收或不应收者,而有关于说部、戏曲、艺人等传记,则未网罗在内。且有为清廷所黜,或视为叛逆而不收者,如年羹尧、刘鹗、周榖;罹文字狱而不收者,如戴名世、查嗣庭等。清初江南、两浙之抗清志士,所收亦失之于稀少,全祖望《鲒埼亭集》于此类碑传收集甚夥,而几全被疏漏。至于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天国领袖,台湾农民军首领林爽文,均遭排斥在外。(28)
故钱仲联编辑《广清碑传集》,重点在“广”字上下功夫,试图突破前四书的收录局限,如“清初明遗民,钱、缪诸人往往未见后来发现之珍贵材料,因而收辑不广。本书于此突出重点,研究清初史料或图编纂完善之明遗民录,不难取资于此。近代文集,于余私人收藏者外,复加勤搜,所得颇多难见之作,因而亦是本书之重点。其他宗教、艺术、百工等碑传,凡四种碑传集所疏略者,本书亦提供一定之篇章”。“总之,必须有征文考献价值者始行入集”。(29)该书收录人物1100余人,碑传1200余篇,基本弥补了前四书的缺漏和不足。
他如方树梅编《滇南碑传集》《续集》,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基本相似。就此而论,集录碑传为专书者,其根本旨趣在于“征文考献”,也就是曾国藩所谓的“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30)。
当然,我们审视集录碑传的旨趣,不能仅停留在“征文考献”这一层面,还应向前推进一步,即关注士大夫著述强调经世致用的旨趣。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出于其阶级属性和立场,尤其是宋明以后史学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特别强调维护纲常名教,维持和反映当代统治秩序,注重发挥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
焦竑治学强调经世,说:“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于雕虫篆刻之间,而所当留意者,或束阁而不观,亦不善读书之过矣。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31)所以,他在参修本朝国史无成的情况下,转而辑成《献征录》,以期历考本朝历史得失,为本朝政治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属于“考古以合变”的经世作为。故其友称《献征录》,“所谓国体民瘼、世务材品,犁然而具,明主所与、文武将吏行事之实,庶几无缺,后王法之,群工尊之,则太平之略也”(32),“至于折衷是非,综校名实,阙疑而传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先生于此实有独鉴,异乎徒事网罗,靡所澄汰,爱奇好异,或滥情实者矣”。(33)如设置类目,将孝子、义人等置前,将胜国群雄殿后。所以,有人说焦竑“试图通过在《献征录》中对本朝人物事迹的翔实记载和描述,宣扬封建纲常中忠君、仁义、孝悌等价值观念……以达警世、昭世和醒世的目的”(34)。
钱仪吉认为阅读《碑传集》者,“果能口诵而心识焉,可以考德行,可以习掌故”,且通过对比其中篇章,“考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体,主乎乐道人善,以为贤士大夫畜德之助”。(35)恽毓鼎称缪氏“新编《续碑传集》十二册,征文考献,近四朝人物略见于兹,丰功长德,足备师资,不第诵文辞、识掌故也”(36)。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期于光、宣以来数十年政治之迁流,人才、学术之隆替,可以考镜”(37)。均重视发挥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最终达到维护纲常名教的根本目的。
至于区域性碑传集,更多的是出于保存地方文献、复兴地方文化的责任和担当。方树梅早年受到当地学者赵藩、陈荣昌、袁嘉榖等人大力提倡“滇学”,传播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响,立志以平生精力“弘扬吾滇文献”,而后数十年之间惨淡经营,坚持不懈,“他对书不视为‘珍玩’,而是主张发挥致用”,“和他的研究工作,结合甚为紧密”,(38)纂辑《滇南碑传集》“以为征文考献之资”,且“言坊行表,滇之人踵武而发扬光大之,是余至所仰望也夫”。(39)《续滇南碑传集》之编辑,则是出于“辛亥改革迄解放初期已故之人物,于国家社会有关者……然皆生清末叶,至改革后,各占数十年,于先后所值政治、军事、教育、文化、风俗等之变革,为前史所未有。或隆或污,或升或降,内讧外祸,国事日蹙,民生日困,皆有莫大之关系。知其人、论其世,贻后贤以评骘,作信史之参稽,此《滇南碑传集》之不得不续也”。(41)
三、编纂体例上的继承与创新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作为草创时期的碑传集类著述,主要以裒辑文献资料为着眼点,“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于时代体制。要其梗概,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为多”(41)。而且,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与两宋流行的名臣言行录存在某种关系,或者说该书脱胎于言行录,又在体例上另辟蹊径,以有别于言行录。按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体例,“先列某人之生平小传,后编列节录行状、墓志、笔记、野史等的史料,以示其言行节谊。但《琬琰集》的体例却与之不同。《琬琰集序》称其书‘集神道志铭、家传之著者为一编’,即汇集整篇之文成一编,而非节录文字。由此在后世形成两种不同的著述体例。……朱熹《言行录》载录史料的体例是‘采掇’,而杜氏《琬琰集》是‘尽录全篇’”。(42)
焦竑《献征录》在杜书基础上,体例有较大调整或创新。按照四库馆臣的说法,《献征录》按照有官与无官两个系统来编排,“其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其无官者则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载之”(43)。实际上,这种调整或创新,至少受到了两种影响:一是有官一系的编排,与《大明会典》这部法典的体例相对应,设置了宗室、戚畹、勋爵(公侯伯)、内阁、六卿以下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官僚机构相对应的类目。充分反映了明代的政治体制。二是无官一系的编排,受到了正史“类传”体例的影响,主要设置《孝子》《义人》《儒林》《艺苑》《寺人》《隐佚》《释道》《胜国群雄》《四夷》等类目。不仅突破了“名臣”的藩篱,而且凸显出宋明理学之下史学强调维护纲常名教的突出特色。至于辑录文献,突破了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分段辑录的体例,改为摘录整篇文献的形式,又回到杜书体例上,同时局部保留《元朝名臣事略》辑录专门段落的体例。因此,《献征录》体例上的创新,对此后的多种碑传集著述影响深远。
至钱、缪、闵、汪四家清人碑传之集,基本延续《献征录》有官和无官两条线索,有官者“以其时,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厌之”(44),即以官秩为经,以时间为纬,按照传主的官爵、事迹和时代分类。在类目设置上,除钱书立《宗室》《功臣》外(45),四家均设有《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监司》《守令》《教官》《杂职》《武臣》《外藩》;且《宰辅》《部院大臣》《督抚》《监司》之下,因其内容繁多,又区分朝代编制。同时采纳正史类传体例,别出《忠节》《儒学》《文苑》《孝友》《义行》《艺术》《列女》等,共计二十二类。
钱书以后,缪、闵、汪三家一仍其例,几无出其范围,但均能根据历史时代的变化及其内容,进行体例上的调整或创新。缪书“续集分卷,比诸原书,微有增损”(46)。如改《藩臣》为《外藩》,后添《客将》一目。“分《经学》《理学》而二,仍是《道学》、《儒林》之习,今悉改为《儒学》”,故将《经学》《理学》合并为《儒学》。缪氏自称“《列女》所收较严”,细化为贤明、孝淑、辨通、节操、贞洁、义行七小类,其中“辨通”一目为新增。(47)
闵书在钱、缪之后,体例或仍遵钱书,《理学》《经学》仍分为二;或新增类目,增《使臣》,“纪晚近始设之官也”;增《畴人》,“用阮文达、罗茗香例也”;增《党人》,“志革命所由起也”;增《释道》,因钱书附存释道人物传记,且《魏书》立《释老志》,《元史》设有《释老列传》,属于“前史例也”。《列女》中,删《辩通》,增《母仪》,“依刘子政例也”。(48)
汪兆镛对闵书深为不满,直欲上接钱、缪二书,故名曰《碑传集三编》。体例也有所调整或变化:“惟《督抚》之次,增《河臣》《使臣》;《守令》之次,增加《校官》。钱、缪二书,《经学》《儒学》《文学》之名,似未允洽。兹将《经学》《理学》统入《儒林》,文章、辞赋诸家统入《文苑》。《文苑》之次,增入《算学》,此本于阮文达公《畴人传》之意也。”汪氏作为清末遗民,特别强调:“东汉崇尚风节,蔚宗创立《独行传》。辛亥后,松柏岁寒之时,其有瑰节绝俗者,增立《独行》一门,以表幽贞。”(49)反映出汪氏作为清末遗民的社会心态和著述追求。
近代以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传入我国,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碑传集的续补工作出现新的变化。钱仲联《广清碑传集》突破四家碑传集的束缚,编纂体例与范围都发生了变化,收录人物“为在各个领域有一定成就,有一定代表性者。有的人物入收,含有阐幽表微之意。重点有三:一是清初明遗民。二是近代人物。三是其他宗教、艺术、百工等碑传。至收录范围,上起清顺治初,下迄宣统三年,但“凡明臣仕于南明王朝殉难者不列入,明臣仕清及遗民死于顺治三四年以后者列入”;清末人物“必须在此年以前已有显著活动者,包括政治、学术、艺术、文学等方面,或生存至新中国建立后任新职者,皆不属于清代范围,一律不阑入。正反面人物俱收,但反面人物慎收。太平天国人物,录入上层有代表性者十人左右”。具体编纂上,“按人物生卒年排列;生卒年无可考者,则按其人活动时期、交游、科名之先后,相应插入”;选文上,取舍颇严,“文章从总(集)、别集、方志及其他各方面(包括丛编、期刊等)搜集。短文在数十字以内者不录,方志慎收近年所新编者,语体文之传记不收,个人传记已刊为专书大专如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者不收,年谱不收。在广泛收录中,有尚未刊刻之稿本、拓片,如沈曾植《海日楼文集》、王蘧常《明两庐文集》、《淞社名人小传》等,又有未刊布之单篇钞稿”(50)。为便于使用,末附传主姓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方树梅辑《滇南碑传集》,“仿钱、诸家体例,参酌损益,循名核实而分编之”(51),按明、清分置,“分内官、外官诸类”(52),不过,明代部分设置隐逸、遗民类目,主要是出于明清易代历史实际的考虑。至编纂《续集》,充分考虑到时代的演进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因而一变前集之体例,“兹则清祚已斩,制度皆变,前例不合沿袭,分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卓行诸目”,至于所收碑传人物,因大多数系编者相接、相见、相闻或志同道合者,但取舍上较严格,“要皆洽于舆情,而非阿其所好”,“一以其人之于国家、社会,有无关系以为去取焉”。尤其是以云南重九光复、护国起义、抗日战争中的著名人物为主,旁及教育、文化、科学等。其中凡德行可以为法,功绩不可埋没者,亦尽量收入,“若夫金碧英灵:辛亥起义、护国出师、抗日御侮三大役,或树有奇勋,或见危授命者,得鸿儒椽笔,有光卷帙,是余之所最欣慕者矣”。(53)
尽管碑传集类著述收录的碑传之文,多谀墓溢美之词,“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54),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碑传,可以考见宋明以来各断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风俗等社会历史的多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尽可能保存大量的原始文献。这是该类著述的主要价值之一。反映在具体录文上,基本保持一人一通碑传,甚至达一卷之多。以钱仪吉《碑传集》为例。因清世宗有“本朝大臣,以功则李之芳,以德则汤斌为首”之谕,“故用李文襄冠功臣之首,汤文正领大臣之前,而以陆清献、张清恪继之,遵圣训,重从祀也”。(55)故《碑传集》“康熙朝大臣”卷汤斌之下,辑入耿介《传》、方苞《逸事》、徐乾学《神道碑》、彭绍升《行状》、冯景《杂记》、杨椿《传》、汪士鋐《墓表》以及潘耒《送汤公潜菴巡抚江南序》等八篇碑传;(56)张伯行之下,则收录朱轼《神道碑》、张廷玉《墓志铭》、沈近思《墓表》、费元衡《行状》、蓝鼎元《传》、贺代伯《传》、杭世骏《传》、华希闵《传》、沈彤《述先师仪封张公训》、任兰枝《张清恪公年谱序》等十篇。(57)而且,该书“附录”体例,亦重在多保存原始文献。“或一人杂见他书者,同时之迹及其子孙言行有可称者,间为附录,殿于本篇。或论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过当,或沿习忘反者,往往有之”(58)。少者一二则,多者达二十条以上。如“宰辅卷”范文程下,除李果《传》、李霨《墓志铭》外,又附录十三则,取自《盛京通志》《贤良小传》《八旗通志》等。(59)再如“翰詹卷”施闰章下,除毛奇龄《墓表》一通外,附录二十则,主要出自汤斌《墓志铭》、高咏《行状》、彭绍升《良吏述》、《施氏家风续编》、全祖望《施愚山年谱序》、梅文鼎《述》、王士禛《池北偶谈》以及施闰章《学余堂文集》等。(60)因此,“于碑传全篇外,节取他说,考异刊同,各为附录,颇见用心”(61)。充分体现编纂者试图尽可能保存更多原始文献的良苦用心。
第二,有利于修史者所采择。如上所述,碑传集的编纂多与史学家或学者们的史学活动有关。如焦竑在参修本朝纪传体国史的过程中,开始纂辑《献征录》;钱仪吉在会典馆任职时,有见于内府所藏国史不为外人所易见而纂辑之;缪荃孙纂辑《续碑传集》,正是他在史馆任职期间。因此,此类著述一旦流布,即为修史者所采摭,有利于官私史书的编纂。万斯同指出:“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62)经今人对勘,清朝官修《明史》充分利用了焦竑《献征录》(63)。再如清末遗老修纂《清史稿》,率多依据钱、缪二家,“宣统辛亥后,《清史稿》告成,大抵采用官书外,依据钱、缪两编为多”(64)。
第三,成为考证史实的重要依据。这类著述收录的碑传,记载具体、详细,对于查考其人其事,如生卒年月、迁转次序、拜罢时日、言论举事并其家世等等,远较正史为详,其所收监司守令以下,亦多为正史不及,为治断代史者必备之参考书。所以往往为考史者所利用。“其议论之同异,迁转之次序,拜罢之岁月,则较史家为得真”,“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65)。如杜大珪《名臣琬琰碑传集》,两宋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篇》、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较多采用之。到现代,该书亦为学者所倚仗。汤志钧当年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的“《宋史》标校,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以至宋人文集中的碑传,订正了《宋史》的失误”(66)。
至于焦竑《献征录》,记载明人事迹,“书郭子兴诸子之死,书靖难诸臣之事,皆略无忌讳;又如纪明初有通晓四书等科,皆《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所未载;韩文劾刘瑾事,有太监徐智等数人为之内应,亦史传所未详,颇足以资考证”(67)。钱仪吉曾指出《碑传集》的价值,不仅“可以考德行,可以习掌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更强调其“有裨于实用”,曾在《后序》专门举例,说:嘉庆二十一年(1816)漕粮奏销册中列有里民津贴银米一项,户部莫知所由,疑为外吏私征,几予驳诘。嗣后从《朗文勤公墓志》及《八旗通志》中的《范承勋传》《郎廷极传》,得知江右多山溪,道险,漕粮盘运艰难,于是有里民津贴夫船之费,载于《赋役全书》,其事乃得明白。(68)此类足资考证之例,多不胜举,不再赘述。
第四,编者按语的多重价值。明代以后的碑传集,编者受历史考证学的影响,率多使用按语的形式考证史实。如钱仪吉《碑传集》,遇有事实不甚合符处,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则加有按语考释。“仪吉案”涉诸多方面,或条列异说,或补充说明相关人物行迹、典章制度、所任官职,或补充说明碑传相关文字,或指出后人记载之误。再如缪氏《续碑传集》,“事有误者,间作夹注而已”(69)。“所撰按语多为考证事实,使得该集较之一般的史料汇编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70)。故有学者称:“这是缪氏编纂《续集》的方法,比前人仔细,且用夹注说明考证的结果,是历时较久的原因之一。删节远不如保存原文,这是正确的处理。”(71)
不惟上述,该类著述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广清碑传集》《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续滇南碑传集》,所辑多是明末清初人物,或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人物,“‘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恰恰是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灾难深重的沧桑易代之际,仁人志士辈出,事迹可讽可咏,最能体现我们华夏民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传统,因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以降,国是多故,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联军、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一一通过当事人的碑传在本书中作为详赡实录,每有正史所不能及者。而碑传撰者也多曾亲历其境,笔端风云往往与血泪俱下。切肤之痛,终天之恨,至今读来仍具有震慑人心的感染力,不啻为进行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72)。
五、余论:集录碑传在当代史学中的延续
宋明以来,不少史家或学者将目光投向碑传类文献,集录成专门的文献资料集,尤以五部清人碑传之集为最(73)。而民国碑传之整理,则有国史馆之编辑试图,又有卞孝萱、唐文权编辑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和《辛亥人物碑传集》。可以说,宋明以后,各断代碑传集的编纂,踵武赓续,成为中国史学上一个突出的学术现象,彰显了优良的史学传统。
而且,碑传集的编纂一直持续至今,影响到今天的史学研究。至少出现了两条发展线索:一是将考古考察的古代碑刻汇录起来,成为历代碑刻集,如《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上海碑刻资料选集》《四川历代碑刻》《温州历代碑刻集》《广东碑刻集》《嘉兴历代碑刻集》《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
一是各地为挖掘和弘扬地方文化,古为今用,出现了大量以当地人物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或专门性的碑传集。如《江宁碑传初辑》(卢前编,江宁县文献委员会,1948年印行);《中国历代明医碑传集》(方春阳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碑传》(韦宾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荥阳清人碑传集初编》(陈万卿编,广陵书社2015年版);《南浔近代人物碑传集录》(陆剑、王巍立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吴中名医碑传》(葛惠男、欧阳八四主编,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吴江学者碑传集》(杨阳主编,广陵书社2017年版);《介休碑传集》(侯清柏、许中编著,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余杭历代人物碑传集》(王国平总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这些碑刻集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墓志铭。
此外,我们仍需正视碑传的某些不足和局限,要爱而知其丑,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碑传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关于碑传研究的深化问题,章开沅这样呼吁:“如果进一步考察探讨碑传的文体、内容、作者、形制、礼仪、风俗等方面,则将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碑传学。”(74)对于新时期集录碑传工作的开展和延续,需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力争在批判继承中继续发展。
注释:
①金毓黻:《民国碑传集序例》,《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期(1948年4月),第140页。
②罗炳良:《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33页。
③白寿彝:《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2页。
④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1页。
⑤章开沅:《序言》,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⑥闵尔昌:《碑传集补自序》,《碑传集补》卷首,《清代碑传全集》第5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1页。
⑦钱仪吉:《碑传集》卷首附《沈吉士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页。
⑧卞孝萱:《后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819页。
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古人不为人立传”条,《顾炎武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6-757页。
⑩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仓修良编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11)朱希祖:《滇南碑传集叙》,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0-411页。又,方树梅纂辑,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滇南碑传集》卷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琬琰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0页。
(13)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页。
(14)赵式铭:《滇南碑传集序》,方树梅纂辑,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滇南碑传集》卷首,第1页。
(15)罗炳良:《杜大硅〈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36页。
(16)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五《泰州学案四·文端焦澹园先生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28-829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献征录提要》亦称:“考竑在万历中,尝应陈于陛聘,同修国史,既而罢去。此书殆即当时所辑录欤?”
(17)黄汝亨:《献征录序》,焦竑:《国朝献征录》卷首,扬州:广陵书社,2013年,第6-7页。
(18)方树梅纂辑,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卷六《文学》引李生葂《方树梅传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71页。按:该传载方氏1934年受云南通志馆委派,出游访求滇南文献,所得甚夥,“抄得未刻***省长蒙自杨增新神道碑、墓志铭稿,以备《通志长编·人物》资料”。
(19)焦竑:《澹园集》卷五《修史条陈四事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31页。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琬琰集提要”,第520页。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献征录提要”,第558-559页。
(22)顾起元:《献征录序》,焦竑:《国朝献征录》卷首,第1-4页。
(23)焦竑:《澹园集》卷二三《经籍志论·史部·正史》,第304页。
(24)参见展龙:《〈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作提要补正两则》,《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1期,第89-90页。
(2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第559页。
(26)钱仪吉:《碑传集》卷首《碑传集序》,第1页。
(27)缪荃孙:《续碑传集》卷首《序例》,第1页。
(28)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前言》,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29)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前言》,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首,第2-3页。
(30)曾国藩:《国朝先正事略序》,《国朝先正事略》卷首,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页。
(31)焦竑:《澹园集》卷一四《荆川先生右编序》,第141-142页。
(32)黄汝亭:《献征录序》,焦竑:《国朝献征录》卷首,第7页。
(33)顾起元:《献征录序》,焦竑:《国朝献征录》卷首,第2页。
(34)姚家全:《焦竑的编纂活动考略》,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1页。
(35)钱仪吉:《碑传集》卷首《碑传集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页。
(36)钱伯城、郭群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恽毓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3页。
(37)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二《碑传集三编自叙》,邓骏捷、刘心明编校:《汪兆镛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9-260页。又,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首《自序》,《清代碑传全集》第6册,第75页。
(38)方树梅辑纂,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卷六《文学》引李硕撰《方树梅传略》,第478-483页。
(39)方树梅:《滇南碑传集自序》,方树梅纂辑,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滇南碑传集》卷首,第19页。
(40)方树梅:《续滇南碑传集自序》,方树梅辑纂,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卷首,第1页。
(4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琬琰集提要”,第520页。
(42)顾宏义、吕晓闽:《宋杜大硅〈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录〉为伪书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第97页。
(4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第559页。按:常见说法认为,《献征录》在拟订类目上,注重分类,主要以官爵为主,以身份(特征性身份)为辅。不仅要突出这些“有名公卿”,还有其他特殊身份的下层人士,如孝子、儒林、义人、艺苑、寺人、隐佚、释道。
(44)钱仪吉:《碑传集》卷首《碑传集序》,第1页。
(45)按:钱仪吉《碑传集》设立名目,“功臣”又析分为“沈阳功臣”“国初功臣”,且“宰辅”区分为“开国宰辅”“明臣宰辅”。这既充分考虑到清朝入关前后的历史实际,也可能受到乾隆时期官方史学的影响。
(46)闵尔昌:《碑传集补自序》,《碑传集补》卷首,《清代碑传全集》第5册,第1页。
(47)参见缪荃孙:《续碑传集》卷首《序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48)闵尔昌:《碑传集补自序》,《碑传集补》卷首,《清代碑传全集》第5册,第1页。
(49)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二《碑传集三编自叙》,第259-260页。
(50)钱仲联:《广清碑传集前言》,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首,第2-3页。
(51)方树梅:《自序》,方树梅纂辑,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滇南碑传集》卷首,第19页。
(52)方树梅:《续滇南碑传集自序》,方树梅辑纂,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卷首,第1页。
(53)方树梅:《续滇南碑传集自序》,方树梅辑纂,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卷首,第1页。
(54)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55)诸可宝:《校刊记》,钱仪吉:《碑传集》卷首,第5页。
(56)钱仪吉:《碑传集》卷一六《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上,第447-475页。
(57)钱仪吉:《碑传集》卷一七《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中,第497-551页。
(58)钱仪吉:《碑传集》卷首《碑传集序》,第1页。
(59)参见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国朝宰辅》,第70-75页。
(60)参见钱仪吉:《碑传集》卷四三《翰詹》上之上,第1182-1187页。
(61)诸可宝:《沈吉士书题识》,钱仪吉:《碑传集》卷首《沈吉士书》附,第10页。
(62)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寄范笔山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510页。
(63)参见侯君明:《〈明史〉与〈献征录〉相关人物传记考订》,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8页。
(64)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二《碑传集三编自叙》,第259页。
(6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琬琰集提要”,第520页。
(66)汤志钧:《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6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第559页。
(68)参见钱仪吉:《碑传集》卷首《后序》,第2页。又,该书点校说明揭橥其旨。
(69)缪荃孙:《续碑传集》卷首《序例》,第2页。
(70)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说明》,缪荃孙:《续碑传集》卷首,第1页。
(71)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第301页。
(72)苏州大学出版社:《后记》,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末,第1432页。
(73)按:清末民初,整理清人碑传者尚有刘承斡。刘氏《椶窗杂记跋》称:“余最近录近人传状志铭之属,思赓续钱氏、缪氏《碑传集》之后。先生亦致力于此,尝写全目寄余,互校两异同,谓‘去取当慎,不宜滥采掇,媚浊世’,并欲举赠全稿,俾参合授梓。”文末署曰“癸未嘉平月吴兴后学刘承斡敬跋”,癸未为公元1943年(《椶窗杂记》卷末,《汪兆镛文集》,第471页)。
(74)章开沅:《序言》,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卷首,第3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ZS009);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引进与培育计划项目(gxyqZD2019032)
来源: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