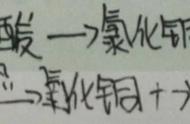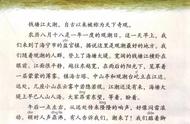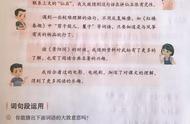2020年,我们被“内卷”的“打工人”包围。但“u1s1,姐学、糊弄学、凡尔赛学”也在今年的流行词中占有一席之地。
每一年,语言总会涌现出新的流行趋势。但流行语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还是千篇一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020年见证了一个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流行语数量的井喷式增长和种类的频繁迭代——就在我们讨论“打工人”时,“打工人”就已经开始被新的流行词“干饭人”取代。如今不断井喷的流行语仿佛成为一条高速运转的流水线,新的词汇如走马灯一般闪现,在我们尚未深入品味与体察一个词汇折射的复杂现实时,它就倏忽而逝,令人目不暇接。
海德格尔曾将语言比作“存在的家”,如果说在变动与不安中度过的2020,改变了人类存在境况,那么语言生态的变动,自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中国的流行语历史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变迁?怎样的流行语更有生命力?当下的流行语是否不再成为对存在经验的诉说,而更多成为供人狂欢的素材?在应接不暇的流行语中,个人如何保持反思性?在2020年的年末,在这条“语言流水线”轰鸣了一整年后,我们希望通过这场对谈中的冷思考,追问2020年的语言,也追问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2020年12月,新京报书评周刊活动品牌文化客厅,联合SKP RENDEZ-VOUS推出年度文化议题盘点系列直播“追问2020”。今日(12月14日)19:00,“追问2020”系列第二场,我们将与你一同探讨如何突破系统围城,欢迎关注!
撰文|刘亚光
12月初,有“语文啄木鸟”美誉的《咬文嚼字》编辑部照例公布了今年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分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后浪”、“直播带货”、“飒”、“神兽”、“双循环”、“打工人”、“凡尔赛文学”和“内卷”。8日,头条搜索也公布了今年十大流行语,“逆行者”、“集美”、“后浪”位列榜单前三,“网抑云”、“尾款人”等榜上有名。
无独有偶,近日,许多国外机构也都相继公布了自己的年度词汇,如“Lockdown(封锁)”(柯林斯词典)、“pandemic(大流行)”(美国韦氏词典)等,《牛津词典》更是表示“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一年”,首次没有选出任何代表词汇。此外,日本的“新词流行语大奖”也于12月1日揭晓,新冠疫情防范标语“3密(密闭、密集、密切接触)”一词获最优秀奖。德国的德语语言协会评委近期也评出了2020年的十大年度词汇,其中8个与新冠疫情相关。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更是将一个怪异的“iso”评为年度词汇,它可以被理解为“isolated”(隔离,隔绝)的缩写词,可以用来和各种名词搭配,比如“iso 发型”,“iso 烧烤”,用以形容各种隔离期间的生活状态。
纵观中外的各类流行语榜单,不难发现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词汇成为了榜单的绝对主角。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言:“一切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一个时代的流行语如同一个胶囊,浓缩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心态与集体记忆。在2020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这些流行语如一个个石碑,为我们记录下了今年人类经历的那些刻骨铭心的苦难与感动。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突发的公共事件常常成为流行语扩散的“引爆器”,除了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件,热点公共政治事件也制造了“躲猫猫”、“我爸是李刚”、“帝吧出征”等令人记忆深刻的流行语。不过,流行语的广泛传播,不仅可以被热点事件引爆,也可以伴随着社会情绪的积累自然地流露出来。比如,今年9月末,B站突然出现了多条以“早安,打工人!”为主题的短视频。“打工人”瞬间成为年度最热的自嘲用语,在各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仿佛一时之间,各行各业的上班族都通过“打工人”建立起了身份认同。许多媒体也对“打工人”的走红背后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打工人”引发公众共鸣的背后,是通过工作实现阶层晋升机会的收窄带来的普遍焦虑,和因专业化分工的不断细化而被消磨的工作热情。

“追问2020:语言流水线”,图为周玄毅、邵燕君、维舟在活动现场。
书评人、专栏作家维舟对公共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有着长期的关注,他同样认为,流行语的变迁很好地反映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他看来,网络流行语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2005年以前、2005-2013、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互联网在中国刚开始流行,彼时的网络流行语大多是些非常简易的表情符或者是“喜大普奔”等缩写词。2005年,博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WEB2.0时代,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出现为网络流行语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支持。这一时期,网络流行语快速增长和迭代,但总体上,依旧带有明显的青少年亚文化特征。而到了2013年,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网络流行语开始由青年亚文化向全社会扩散开,逐步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用语之中。
从小众的亚文化逐步走入公众的视野,并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这种语言的“破壁”现象其实发生在很多流行词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专注于研究网络文学,在一次课后被年轻学生们的各式“网络黑话”隔绝于交流之外的经历后,她萌生了撰写一本网络流行语的“词典”的想法。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语言现象的涌现空前繁盛的时代,在她和学生们一起编著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的前言中,她写道:“麦克卢汉曾预言,进入电子时代的人们将重新部落化,如今,在网络空间以‘趣缘’而聚合的各种圈子,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生产着新话语”。而这些新的语言,正在不断渗透进我们已有的语言中。《破壁书》收录了大量在不同时段出现的网络流行语,其中例如“卖萌”、“屌丝”、“钓鱼”等等,都已经成功完成了“破壁”,成为我们日常交流中时不时蹦出的词汇。

周玄毅在现场展示今年双十一期间的网络流行语。
而在今年年末,流行语的一种新的“破壁”:学术词汇的“出圈”,意外地制造了可能是今年最火的一个流行词——“内卷”。这个词原本由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以形容小农经济领域某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而如今,它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形容“竞争激烈”、“高度内耗”的场合。不过,流行语在快速打破壁垒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壁垒。流行语越来越快的迭代更新速度,使得语言成为了年轻人和父母辈之间的另一种“数字鸿沟”。
一面打破壁垒,一面制造壁垒,只是流行语自身蕴含的矛盾之一。这种矛盾性,由流行语的“新”所决定——这注定了它将与社会既有的语言体系正面相遇,并接受后者的审视与评判。而一直以来,盘旋在中国流行词上空的最重要的争论可概括为一种“雅俗之争”。脱胎于网络亚文化的流行语千奇百怪、不循常规的造词方式,戏谑搞怪的草根风格,常常被视为与“正经”的主流语言体系格格不入,被打上粗鄙庸俗的烙印。而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语言,他们可能赞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的一句挖苦:“很明显,那些上了岁数的人对语言革新都很排斥,他们很难接受青少年创新的语言,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新语言,转瞬即逝。”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可以引发争论的事物,往往也就意味着商机所在。因此我们也看到,在“公共事件引爆”、“社会情绪的流露”之外,资本、平台的助推成为流行词走红的另一个关键的路径,比如今年年初一度引发热议的“后浪”即是一例。在流行语的每一次狂欢背后,似乎都有一些隐藏在背后的“推手”,在左右着语言的风潮。不过,在这股被引导的潮流之中,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语言“弄潮儿”,不盲目跟风,试图用自己的创意和批判性思考,玩出有别于潮流的新花样。武汉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知名辩手周玄毅正是这样一位微博“大V”,他一面紧跟各种流行语的热点,一面在自己的微博tag“瞎扎尔辞典”中,发表对流行词的个性化解读。这些解读有的诙谐,有的引人深思,还有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没有什么特定的意思,只是为了不盲目跟随大家对流行语千篇一律的解读”。
那么,什么样的流行语才具有生命力?对于2020年的流行词,周玄毅、邵燕君、维舟又有着怎样的剖析?
01 窗户:
流行语是一个时代表达自身的方式
“凡尔赛学”是2020年的另一个热度极高的词汇,在活动的开场,维舟便阐述了他对这一词汇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凡尔赛学这个词的有趣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直接指涉的“低调而不经意间地炫富”这类现象,而是这个词自身内在的“反讽性”和“解构性”。“美国的学者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将世界上的文化划分成了高语境和低语境,在高语境社会,比如中国,人与人的交往常常是要听‘弦外之音’,‘凡尔赛学’这个词汇的有趣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弦外之音,当我们用凡尔赛形容一个人的时候,是在用一个表面上‘高大上’的词汇,去形容一个很可笑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反讽。可以说,这个词的使用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文化特征。”
这种流行语的“反讽”特征,同样体现在其他的许多词汇上。邵燕君认为,虽然“内卷”、“PUA”这些词汇指涉的现象十分负面,但是这些负面的现象能够以流行词的方式被“指认”和“名状”出来,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可喜的现象。“当我说出PUA这些词的时候,其实这意味着我已经把这些负面的现象对象化、问题化了。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把这些现象说出来,这说明我们还对社会存在哪些问题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