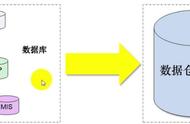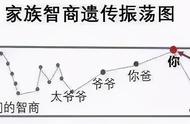▲ 使用隐语是小圈子防备外人的一种沟通方式。 © 电影《智取威虎山》
时下00后社交圈的建立,不仅仅是基于以前的血缘、地缘和业缘,更是建构于互联网之上的趣味圈子。比如追星、玩cosplay的、玩嘻哈的,都有自己的圈子。圈子不仅是兴趣俱乐部,也是一种情感联结和归宿;一套大家都懂得的圈内用语,是判断“是否是自己人”最直接最简便的手段。如果大家都喜欢同一个明星,其他粉丝熟稔地使用yyds、ssmy等来夸奖自己的爱豆,唯独你既不会使用、也看不懂,那你可能就很难融入这个圈子。不知道别人说什么,也感受不到圈子化的乐趣。同时,饭圈内部使用缩写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仅限于在圈子里褒贬,不会将影响溢出圈子外,缩写也有助于规避检索和掐架,从而实现圈地自萌。
▌沟通效率的提升与语言贫乏之忧
有人将当下的时代定义为“刷时代”,刷微博、刷微信、刷淘宝、刷新闻、刷热点……人们从刷APP中开始一天,又在刷APP中结束这一天。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述的屏读(Screening)日渐成为一种现实。阅读行为虽然存在,但是这种阅读更多指向了碎片化的泛阅读,停留在一种阅读的姿态上,就像用眼睛“刷”一下屏幕,手指轻轻划过页面。

▲ 阅读行为虽然存在,但是这种阅读更多指向了碎片化的泛阅读,停留在一种阅读的姿态上,就像用眼睛“刷”一下屏幕,手指轻轻划过页面。 © Pixabay
媒介改变了我们对信息的接受方式和习惯,反过来,我们对信息的接受习惯也在影响着信息的形式。慢慢地,网络语言就成为一种被“刷”的语言,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效率、速度感和爽感。
“字母缩写”正好能契合这样的需求,它把复杂的语言进行量化、简化,形式简单、输入便捷、能言简意赅地传递情绪,践行着语言经济学“最省力原则”的要义。
因此,无论人们是否乐于接受黑话化的流行语,都应该正视,在网络交流中,年轻人自然会追求语言的效用最大化。能够更快、更简单、更即时传递情感和信息的语言,就更受欢迎。可以预见,这类缩写的网络流行语以后还会有更多。
从乐观的角度看,作为流行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这一代年轻人从中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个性和创造性,他们在互联网上构建起了独属于他们的表达、社交审美乃至于价值体系,并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认同方式。
一方面沟通的效率得到了提高,但另一方面,很多人担忧,网络流行语的泛滥会导致年轻一代语言贫乏。年轻人天天浸染在网络语言里,无论是发弹幕还是网上交流,都是不假思索地使用“短平快”的网络语言。如果网络语言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表达反应,会不会由此影响年轻人对规范语的运用,以及复杂修辞的训练?比如互联网博主“王左中右”就在微博上痛批这一现象:“越多地运用这些网红词,人只会越来越匮乏。你看到好看的,你想不起来‘明眸善睐’、‘媚眼如丝’,你只会:‘绝绝子’。你内心翻涌不想说话,你不会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你只会:‘无语子’。你难过得不行,你也压根不会想起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你只会说:AWSL……”
语言贫乏的确是时代症候。此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做过一个调查,76.5%的人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受访者认为最明显的表现是基本不会说诗句(61.9%)和基本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网络语言更注重小圈子里的交流效率,它虽便捷却轻浅,虽可即时性反映情绪,却也千篇一律。这种批评不是要扼*年轻人使用网络语言的权利,而是呼吁:在学校内外必须着力培育年轻人的语言美感和人文素养,让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始终有人文支撑。

▲ 传统文字之美往往是网络语言所不能表达的。 © 丰子恺
但不必对网络语言“污染”汉语抱有太大的戒心。语言学者王弘治认为,“语言的进步与繁荣,其中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一个民族书面文献的丰富程度——书面语最容易被拿来衡量一种语言的进步与否”。语言是在不断进化的,只要有使用语言的人,它就会不断被丰富。各种各样的流行语的确会挑战书面语的权威,但坚守语文课的阵地,坚守传统文学的阵地,书面语便不惧挑战。
▌“反新话”与“新话化”
前段时间针对“黑话”的批评声音很多。不仅仅是前文说的网络黑话,有人批评文科“黑话”,有人批评互联网行业的“黑话”,比如动不动就“深度串联”、“势能积累”、“高频触达”、“快速响应”、“耦合性”、“颗粒感”等。在批评者看来,这些“黑话”不仅仅是一堆看上去高大上的空话套话废话,它更代表了一种行业的权力控制。“知著网”在一篇文章中将之与《1984》里的“新话”相类比,指出,“互联网黑话的频繁应用也逐渐改变着员工们的思想与表述习惯,使其成为权力体系中的一员”,“让员工们失去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
这并非危言耸听。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语言背后是思想,是认知。在《1984》小说构筑的世界里,塑造“新话”可以消灭旧语言,继而缩小人们的思考范围,因为到时候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表达相关的思想。

▲ 塑造“新话”可以消灭旧语言,继而缩小人们的思考范围,因为到时候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表达相关的思想。 © 《一九八四》英国首版封面
在粉丝饭圈等狂热化的圈子里,网络黑话也能起到相似的作用。比如“白嫖”这个词在饭圈流行,指的是粉丝喜欢爱豆,却不为他花钱,不买周边不买代言产品不看演唱会。这个负面色彩的词汇型塑了一种饭圈思维:喜欢爱豆,一定要不遗余力为他花钱,并通过同伴压力给粉丝制造焦虑。例如此前某爱豆发行了一张数字专辑,饭圈里动员粉丝大量购买,话术如下:“量力而行≠买个十张八张意思意思……能买100张就咬咬牙买300张”,“买一张的真不是东西,不用来反驳,在我眼里连黑子都不如”,“买这么少好意思说爱他吗,你有脸爱他吗,好意思白嫖吗”……这里,“白嫖”这个“新话”的词语,就起到了消灭理性、助长粉丝畸形打投的作用。
但在某些情境下,我们恰恰发现,网络黑话也能够起到一个反对“新话”,争取生存空间的功能。如同在古代社会,黑话是三教九流的边缘人群挑战主流社会的形式,网络黑话也是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符号化的内容对传统和主导文化形成某种侵蚀和疏离。
虽然互联网的开放和包容让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但不必讳言,依然存在着一些禁区,使某些词语或观点不能直接被叙述出来。
这时,网络黑话就具备了几年前表情包刚火时的功能,它是“一种公共修辞策略,其实就是对言说分寸、传播潜力、语义结构、话语安全与修辞智慧的不断拿捏和试探”。网络黑话很难为外界直接理解,文字背后包涵的戏谑、调侃和嘲讽意味,也可以表达出年轻人对某些事件的态度。网络黑话成为另一种圈子化的“社会方言”、一种曲隐的参与方式,它可能保障了某种言说的自由,潜藏着某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