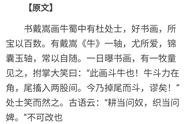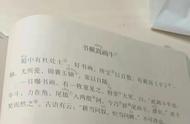唐代画家戴嵩善画牛,和善画马的韩幹齐名,人称“戴牛韩马”。
戴嵩牛画,后世一画难求。小学课本里有苏轼《书戴嵩画牛》一文,说蜀地有杜处士,收藏了一幅戴嵩牛画,随身带着,四处显摆。一牧童见了,拊掌而笑:“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
苏轼由此感慨,“耕当问奴,织当问婢”,牧童最懂牛尾巴。
戴嵩画错了,还是杜处士买了赝作?刘埙是宋末元初人士,他说“戴牛品入神妙,然世远难得真”,假画的可能性更大。还有个例证,南宋《清波杂志》载,宋代米芾之子米元晖“尤工临写”,有人向他兜售戴嵩牛图,米元晖借留数日,临了一幅把画掉了包。卖画人后来找上门来打假,米元晖问他怎么看出来的,回说:“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
先谴责下米远晖的人品。接下来说,此事有疑点,画牛眼只需一点墨,如何能看到人影?故宫藏有戴嵩《斗牛图》,此画自然也难逃乾隆题跋。据乾隆判断,“似指牛目中画童子形,童子目中画牛形。”戴嵩神技,画出了牛眼中的牧童。

戴嵩《斗牛图》
宋代院画极重格物写真,从皇上到画师都是细节控。宋徽宗说“孔雀登墩,必先举左腿”,就是画坛佳话。这故事传了上千年,没见人质疑过,果真如此?古画里登高的孔雀举哪条腿的都有,如今见不到孔雀登墩,但孔雀栖于高枝,迈腿是上不去的,大约还是要靠飞。至于斗牛的尾巴摇不摇?找了不少图片看,斗牛不是都夹着尾巴的。华尔街那头愤怒的铜牛,尾巴也一直翘着。
黄宾虹评说宋画风尚,“一人、二婴、三山、四花、五兽、六神佛”。宋人爱画婴戏图,儿童不好画,在唐宋之前,画中的儿童多是画成了“小大人”。东晋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小孩都是一身成年打扮。《宣和画谱》说唐代张萱“善画人物……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因为“盖婴儿形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髻稚气。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人”。周作人曾批判不能把儿童“看作不完全的小人”或“缩小的成人”,画儿童亦如此。
宋人为什么喜欢婴戏图?因为婴戏图的一大功用,是为了香火。两宋时,尤其是南宋遭遇严重的“不举子”问题,就是说宋人不爱养孩子。宋代战乱频仍,赋税沉重,尤其是按人口征收的丁赋,使得宋代人口问题极其严峻。南宋开设了有史以来第一家国家设立的幼儿慈善组织,慈幼局每年收养弃婴竟达两万余。再加上宋代婴儿的夭折率相当高,宋代皇帝共有子女182人,其中夭亡者82人,将近一半。
古时最初“女称婴,男为孩”。要为宋人点赞的是,婴戏图中很注意画女孩。比如现存最早的一幅宋代团扇上的《百子图》,一百个孩子里有20个女孩,后世《百子图》很难找到女孩。直到今天,这样的性别差异在儿童绘本中仍然存在,去年有篇论文《畅销儿童绘本中的性别图景与性别权力研究》中,对近年来国内畅销的儿童绘本做了数据统计,其中男孩的形象仍然超过女孩1.75倍。
说到民俗艺术,大致可分两种:一是有香火气的,一是有烟火气的。
婴戏图从宋代宫廷中渐入民俗。学者扬之水说:“明清时代的婴戏图不仅多半程式化而且成人化,再少见宋金时代作者笔下的童心童趣。”若是不谀宋的说,宋代的婴戏图都是香火气,好不到哪儿去,那种“大头儿子”式的夸张,开了一个挺不好的头。
明清时代虽然循规蹈矩,但却有不一样“气味”的,比如扬州八怪之一的华喦。今年是虎年,华喦的《蜂虎图》很出圈,因为那只老虎歪嘴眯眼弓身子,全无虎威。华喦晚年画山画水,还画过一组《婴戏图》,闲笔所至,那画上的儿童没有宋画的浮华与富贵,却多了巷井生气。都说丰子恺先生的画风学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其实在华喦的画中就可寻到。

(清)华喦《婴戏图册》
毕加索有句名言:“我十四岁就能画的像拉斐尔一样的好,之后我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艺术和人生的境界是相通的。周作人说“发现童年”,老了老了,不妨去做老顽童。
老子早就讲过“圣人皆孩之”,这句话很容易读作“圣人接孩子”。即便是圣人,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难免的吧。婴戏图里是没有牧童的,牧童都在山水画里。看山水画中的牧童与牛,总觉得牛是画家的自画像,正可谓牛眼中有童子影。
周作人写过《儿童杂事诗》,一共72首,其中《带得茶壶》这一首写得很有“尿性”:“带得茶壶上学堂,生书未熟水精光。后园往复无停趾,底事今朝小便长。”
丰子恺先生给诗作配画,不遮不掩画了小同学们墙根下的这一幕,却不让人觉得有冒犯,这就是烟火气,你在《百子图》上画个试试?
韩愈推敲了一辈子的诗,《诗学纂闻》却说“昌黎之佳作,莫若‘老翁真个似童儿’”,话不中听,但很中肯。
杨万里老了老了,和孩子一起去看鸦,给乌鸦数胡子:“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复小卢胡。一鸦飞立钩栏角,子细看来还有须。”他写了一辈子山水,一首《桂浦铺》写至化境:“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门。”在他笔下,山水都打闹起来,返老还童了。
“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莺雏金镟系,猫子彩丝牵。”晚唐诗人路德延一生“放恣”,写了《孩儿诗》五十韵,诸般童戏尽入诗中,“曲尽儿嬉之状”。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却觉得这首诗在讽刺他,不由分说把路德延扔进了黄河里。
千古奇冤,童心还能伤到人?(责编:沈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