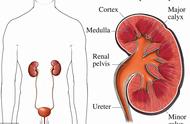他们这一代与西方的坚船利炮最早接触的大臣为西方的先进技术震慑的同时,又希望拿来的仅仅还是来自西方坚船利炮。多数人心目中的“西学”只是为了“长技”而已,也只有个别人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这一时期,我们只是拿来了技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
而从60年代中叶初期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大臣创造江南制造总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为了抗衡西方的军事压力,中国开始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

但同时,为了学习技术不得不翻译。也正是因为军事衍生出来的翻译之学,中国的近现代教育出现。一批学习英语的西式教育学校相继建立,所翻译之书也大多与军械制造、机器制造有关,数学、声光电等学问也渐渐传入中国。
科学事业与教育事业相辅相成,这个过程又成为格致之学“用器以显”的时期。

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薛福成的《机器殖财说》,郑观应的“商战”,以为“十万之富豪,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这种呼声,也唤来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的官办民族企业。
他们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开始把声光电视为西学的精华。

于是历史又进行到下一阶段,由科学技术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
还在70年代,若干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出,洋人“学校建而志士多,议院立而下情达,其制造、军旅、水师等都是议院政治的成果”。经过80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90年代,散见的点滴言论与人们私下之间关于政治的议论渐渐成为那个时候先进中国人的公开秘密。
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中国之患,在政事之不立,而不在格致西洋之器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