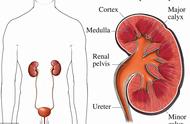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主张被提出,是认识西学的一个突破点。尽管此时满清高层并未修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宗旨,多半也只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会对君权加以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中体”中的“君臣之义”。多年来是否赞成议院这一条也是作为改良派和洋务派的界限。
比政治和教育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
虽然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中国知识界所挖掘和传介,但在西学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初已经有人开始在窥探西方哲学的彼岸了。严复申论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就是典型的代表,并提出了天地万物有万物形成之理,人言有辩证之理的学说,这就从认识的根本上冲击了儒家一言堂的哲学观。

这种对于西学的探索由格致而进入哲理的趋向,代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会有的终极阶段。
这五个阶段由表及里、有具体到抽象的汲取西学的过程,虽然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开展的,但是它本身又徐徐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因为西学是新学,中体是旧学,中体和西用是不可能不互不侵犯的。
“用”在“体”中发酵,势必会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人们虽然想把他限制在既定的范围之内,实际却是无法控制,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最终把中国专制主义封建政体淘汰,这一点是发动这场洋务运动的满清高层所始料不及的。

思想是人类的武器,所以我们现在总是在思想的框架下抓教育,而后才是追求器物上的硬件优越,殊不知,这一认识是建立在我们中华民族充满血与泪的历史之上,通过一辈辈人的人生积累所换来的。

人不能没有武器,但更不能没有思想,因为,思想就是人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