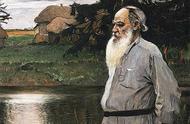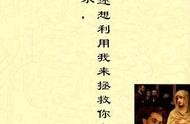然而,文章的短,就意味着表达空间的狭窄。
为了简单而明快地表达思想,只能把问题简单化,甚至,干脆变成对立的“黑白或正邪”,让作者写起来更加义愤填膺,读者读起来更激情澎湃,审美快感油然而生。
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就这样巧合地取悦了国内文人偏激的激情,从而,出现了陈独秀赞誉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赞誉托尔斯泰“敢于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等言论,甚至,连鲁迅先生都称其“高歌猛进、将旧秩序一扫而空”。一时间,国内文坛就这样把“二十世纪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战袍,披在了列夫·托尔斯泰身上。
国人看西方文学还仅仅停留在皮毛,往往只读了只言片语,就将心中的某个愤恨不平的想法寄托于其中。貌似我们是在学习先进的思想,实则却是一个可笑的撒娇举动,无非是为自己被现实压制的理想,找到一个所谓的权威的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老先生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国外好的东西,一经传入中国,没有一个不走样,就连列夫·托尔斯泰,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而这样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转,就在1928年列夫·托尔斯泰一百周年的诞辰之际,这位文人再度被国人热炒。与此同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即:他真正的代表作,才开始真正被翻译成中文,进入到中国文人的视线。

此时,中国的那些具有革命色彩的文人,在阅读后惊奇地发现:这位俄罗斯作家,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具有“战斗性”,他的笔风温柔,描述细腻,让人回味无穷。可是,这样的风格,却无辜地在中国遭到了强烈的讽刺。之前,列宁曾露骨地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可怜虫。”自此,列夫·托尔斯泰在国人的心中,开始走下神坛。
但不幸的是,之后,很多中国文人开始对列夫·托尔斯泰做出荒唐的评价,称其为“卑污的说教人”。这其中,也有一些文学大家,比如:周立波、鲁迅等人,开始“客观”地看待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与为人,一方面承认他的才华,另一方面批评他的“不抵抗主义”。就这样,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文人中,被撕扯成了惨不忍睹的两面。
可是,被文人们看重的“写作才华”,却也包括了一个巨大的文学误解。国内文人天真地以为:小说可以拆解分为“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两者可以互不干扰。尤其是“技术”层面,又可以无限地拆解为描写、组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文学创作基本功”。但是,最为可怕的却是这样无限拆解的结果,这其实就是一个扼*小说的过程。

看似专业的“技术”,实则,只是一套“精致的谄媚”手段。
对此,很多作家娴熟地运用着这个技术,他们高尚地打着“观察生活、反应生活”的种种旗号,却做着“故事工人”的工作。其实,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创造力就是在这样的感受中被“无痛、合法”地“阉割”掉了。之后,当国内读者渐渐觉醒,当我们更多的人可以理性地认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而对于他最中肯的定位,则是一位优美的“小说家”。
此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一个思想剑走偏锋的人,为何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何会走向不朽?
由此,中国文人从盲目追风托尔斯泰,又转向所谓的研究托尔斯泰的文学风格,妄图在其中找到这位文坛圣者不朽的理由。通过对托尔斯泰文本的分析,中国学者得出了一套令常人晦涩难懂的理论,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
其实,托尔斯泰走向世界文学神坛的理由非常简单:在世界文坛上,本来就存在着完美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的更接近这个模板,谁就能更接近不朽。
而在实际的写作技巧方面,这样的“不朽”技巧,无非就是: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有更多的剧情人物,更多的故事情节,更加细腻的细节描绘,不断变换的场景描述,主题与时代完美相结合等等。当很多作家明白这个“不朽”的真理之后,其创作空间就会被压缩到极致。

中国小说家们仿造托尔斯泰,的确也写出了很多“伪托尔斯泰”,可是,谁也没能被不朽垂青,连杨沫都因受到“中国的托尔斯泰”的称号而自持不住。这也难怪,在托尔斯泰不朽传奇的后门上,文人们个个都撞的头破血流。
上个世纪60年代,列夫·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被禁止出版,只有他晚年的一些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得以传播。在那样的中国历史氛围中,托尔斯泰却被再度推向了“思想家”和“良心”并存的神坛!
直到“文革”结束,中国读者们归于理性,才慢慢的发现: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其实,充满着厚重的对于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也有来自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深沉的内省,仔细读来,所有人第能感受到他心中这份厚重的隐忍和令人感动的力量!
当我们真的从群体中剥离出来,真的用自己的智慧来观摩这个世界,从自己的思想中去探索自由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写作已经成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灯塔,那灯塔照亮着每一个不愿向命运屈服又无奈在路上艰难跋涉的人们。
所以说,是托尔斯泰让我们知晓:我们应该配得上那曾经承受过的所有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