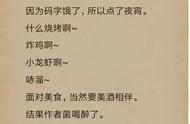《天问》的来历,按王逸《楚辞章句》,是由于屈原“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意即在宗庙祠堂中见到壁画而生思。作为中国早期的神话史诗,《天问》的内容截止春秋末年。其中的一百七十八个问题涉及天地开辟、洪水传说、夏商周古史等等。

在这部史诗中,有意思的是对大禹治水之事的疑问:
鸱龟曳衔,鮌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这里面涉及到:
为什么鸱龟都会听从鮌的吩咐;为什么帝不计鮌的功劳,要对他施刑?为什么囚禁在羽山三年还不放?鲧是怎么从腹中生出禹的?为什么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谋略?天下土地贫瘠不同,是怎么划分的?应龙是怎么画地疏通的,河海是怎么流通顺利的?鲧怎么就迷惑了,而禹怎么就成功了?
这其实也是很多年来,中国一代代学者的困惑。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换种思维,尝试着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首先,我们要谈一下——
(一)大禹是什么人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图腾视角下的二里头时期夏商文化转换》中已经谈到当年“疑古派”顾颉刚的说法:“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是一条虫”。这还引起了鲁迅在小说《理水》中的嘲讽,以“鸟头先生”影射顾颉刚。但顾颉刚的学术观点是有一定价值的,并非空穴来风。他曾经与人合写《鲧禹的传说》,系统论述了鲧禹传说的来源和演变,指出禹与夏的联系最初出现在战国以后的文献里。早期的《诗经》等典籍中,禹的主要贡献在于治理山川。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这里面的禹可以视为上古时代的一位卓越的部落领袖,形象近乎于神。
后来,顾颉刚放弃了“禹为虫”的假设,但在《古史辨》第七册中仍然认为禹是“主领名山川的社神”,是神而非人。丁山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顾颉刚的观点,他在《禹平水土本事考》中说,“禹之为禹,得名于雨,雨神为其最初神格,继因祷雨山川而演为山川之神。因农业发达,社稷之祀尊于一切,禹之神格,再变而为后土,为稷神。”(转引自詹子庆:《回顾“大禹治水”问题的讨论》)。

画像砖上的大禹
大禹神话毕竟已经是三四千年前的事情,由于夏朝及以前的资料缺乏,想要系统而完整地考证出是否真有大禹其人毕竟困难。大禹的有无问题,就连两千年前的司马迁都已经感到棘手,所以才会在《史记》中出现禹的身份失统问题:在《夏本纪》中,司马迁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五帝本纪》中则说:“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那么舜是颛顼的六世孙。这样看来,禹与敬康是一辈的,当舜出生时,说不定禹都不存于人世了,又如何能舜命禹治水、还接受舜的禅让?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或许曾经存在一位部落首领,他对于部族有大功,因此形成了一系列以他为中心的神话,并将其虚构为大神禹。当夏代建立之后,为了渲染自己血统的神圣性,夏王朝即利用了已经存在的禹的传说,编造出夏族的世系。历史上真正存在的首领是大禹神话的底本,人们在此基础上添枝加叶,终于形成了治水、铸九鼎、生出夏国开国君主启的完整的大禹神话。
因此,当本文提到禹时,指的是在历史中可能存在的那个“禹”的真实原型。

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清乾隆年间,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二)大禹是否治过水大禹有没有治水,这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如果他治水了,是如何治水,治水范围有多大,是否真的遍及“九州”?这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天问》还是在现代,都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大禹治水似乎有多方面的证据。从气象学和地质学来看,在4200—4000年前可能存在全球性的气候异常,由于灾害性降雨、第四纪冰川溶化等原因,中原地区确实曾洪水滔天。
2016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聘用人员吴庆龙带领的团队通过调查研究青海省循化县黄河上游的堰塞湖和洪水沉积物,认为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由于堰塞湖溃坝,导致黄河流域发生过一次超级大洪水,影响到了下游2000公里以外的中原地区,进而为大禹治水提供证据。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刊物《Science》。不过由于在年代判断上与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国内夏商研究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