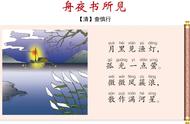公园成了城市建设的新指标,新的公园设计需要更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修建大面积精致的景观,却与居住者不发生关系。
记者 | 任思远
编辑 | 张云亭
“公园城市”成了中国城市建设的新热词。大到对山川河流的生态治理,小到居民社区里的“口袋公园”,设计不同类型的城市公园成了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的新趋势。
各地城市规划中不断增长的数字可以作证。截至2020年年底,上海已有406座公园,并计划在2025年增加到1000座;截至2021年10月,被划归为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成都建成绿道4700余公里,规划建设了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以及1.69万公里的天府绿道。
对公园类型的精准划分随之而来。除了大型公园,成都同时强调要建设“公园社区”。杭州则在2022年制定了《加快公园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的“四级公园体系”。
公园成了城市建设的新指标,城市管理者寄希望于它能解决过去城市快速扩展中的环境污染、人地矛盾等诸多问题。这意味着新的公园设计需要更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修建大面积精致的景观,却与居住者不发生关系。
公园的设计和运营也不再遵循传统的模式,而是探索城市未来经济发展、社区自主参与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新旧城市发展模式的迭代过程。
在临近山川河流的新城区开发中,生态公园的设计成为这股趋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趋势兴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土地增量有限,城市边界比如滨海区域反而成为发展的重点。
这要求城市规划师对于自然地理环境有更多的了解,以新的模式代替过去城市建设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改造,扭转“人造”美感转而尝试探索能与自然共存的城市。“环境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共存’不是应该这样,而是必须。”荷兰的建筑与规划事务所KCAP的副合伙人陈亚馨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我们的认知之所以还有这个矛盾在,是因为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我们逐渐丧失了与自然共生的能力。”
常见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案正在发生改变。KCAP在深圳就经手过这样的案例,他们负责的光明湖碧道项目原本规划了一条马拉松道,但在生态调查中发现附近有野猪栖息地。为了避免对周围生态的破坏进而造成对野猪生存环境的影响,KCAP主张将这里的跑道取消、换到生态敏感度更低的区域,并最终得到了委托方的支持。
“国内过去的大部分规划都是以发展为核心,”陈亚馨说,“当我们提出‘通过发展来保护’,或者‘通过保护来发展’,相当于提出了新的概念”。
同时,过去城市发展对生态的破坏已是既定事实,部分生态公园面临修复问题。在江西南昌,美国景观设计公司SWA设计了赣江“S湾”活水岸公园,它位于江西省赣江新区的核心起步区,SWA设计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分析河流形态的演变历史。他们发现在近30年人工干预的影响下,河岸不断被侵蚀,原本稳定的S形凸岸逐渐瓦解。因此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减缓侵蚀过程,并尝试恢复S形河流地貌。
城市公园趋势的另一重点则与当下的“城市更新”“老城改造”联系紧密。在这种语境中,密布在居民生活空间中的“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的设计成为城市公园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有不少小公园被用来解决城市废弃“盲区”的遗留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深圳梅丰社区公园就是典型案例,它位于福田区北部,周围城中村、老旧住宅和工业区混杂,而公园所占的4000多平方米地块已经因为周围小区业主和开发商矛盾被闲置20年。2019年,梅林街道发起了设计竞赛,让街道、社区规划服务机构、设计师、居民和第三方顾问合作设计。原本的围墙被拆除,与周围小区打通,改建成了社区的公共空间。

深圳设计团队自组空间设计的梅丰社区公园,利用碎裂的混凝土块进行微地形塑造成为裂缝花园。(图片:梁瑞华、叶 颖)
与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一样,社区花园同样面临着革新。疫情过后,曾经整齐的、充满“奇珍异草”但并不利于本土动植物生存的公园遭到质疑。尝试改变现状的人和组织开始出现,并实践探索城市“野生公园”的可能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悦来2014年就和伙伴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四叶草堂”,希望通过居民共创,在城市社区里营造出更自然、更有野趣的花园。受景观设计师俞孔坚的影响,他赞同应使用“乡土物种”而非“异域或园艺场的奇花异木”。并且从早年经历中他发现,“园艺化”的、“高级且贵”的公园往往并不利于人在其中自如活动。
刘悦来和四叶草堂尝试指导居民利用小区附近的闲置地块种乡土植物农作物、做菜园和花园,这些植物作为“景观”的同时,还能让社区的居民参与种植和采摘,因此被称为“共治的景观”。除此以外,他们尝试通过改变植物、土壤,修建辅助通道的方式,探索给青蛙、刺猬、蝴蝶等昆虫和小动物留出栖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