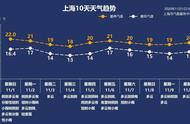上次写《淘麦》,给老伴把面捎去了,这次还正应了老伴的话:“麦虽然没淘,但打的面还比淘过麦的还白,吃起来劲道,蒸的馍也白,到底是磨面设备先进了。”文/闰土

啥叫馍,是把面发好后从锅里蒸出来的叫馍,城市人把这叫馒头。
上次写《淘麦》,给老伴把面捎去了,这次还正应了老伴的话:“麦虽然没淘,但打的面还比淘过麦的还白,吃起来劲道,蒸的馍也白,到底是磨面设备先进了。”这次我留了几十斤面,也刚好上次蒸的馍吃完了,我想马上也快过年了,不如发些酵子,起上些面,把过年馍一蒸,到年跟前也就不乱套了。
我小时候上学时,家里吃的短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肚子饿得像猫抓一样。一次,我放学后剜了一笼野菜,晚上让母亲给我蒸菜疙瘩,我把菜择净后,不停催着,母亲亲昵地说:“你急什么,像喉咙眼手上来了。”等了不大一会儿,母亲把锅盖一揭,我从锅里一手拿一个菜疙瘩,大口大口地吃着,菜疙瘩把我噎得直打嗝。母亲看到后笑着又说:“看我娃像饿狼城里放出来一样,甭急,菜疙瘩有的是,你慢慢吃。”那晚就不大的菜疙瘩,我一气吃了五个,母亲吓得再不敢让我吃了。
那时不知我是长身体还是饭菜没油水,经常一顿饭赶不上一顿,每次学校回来,就在厨房翻箱倒柜找吃的。奶奶笑着说道:“看我憋蛋娃像饿死鬼掏肠子呢?”然后奶奶又从她房子拿些好吃的偷偷给我。
记得在七十年代未,我曾招录在一个乡镇企业上班,都在灶上吃饭,后来我又在外面给厂子跑采购、搞推销,再后来又当上了销售厂长,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因为多在外,少在家,生活上常常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母亲常常数落我,“把我惯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连吃饭调和都不会调。”
以后娶了媳妇,我更是大男子主义严重,往往从厂子回到家里,妻子第一句话就问:“你吃啥呀?”
我不加思索地说道:“吃面。”妻子把面做好,给我端来,又亲切地问我:“调和尝着吗?”那时我能吃饱饭已经很知足了。
这样我常常回来不几天,就走了,即使农村割麦、种麦也停不了多长时间,家里有父母亲,加及我妻子,他们也不在乎我在不在家收种。
那时,有母亲的呵护,家里就是油瓮倒了我都不管不发慌,更别说吃喝了。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由昔日的年轻小伙一晃到了花甲之年,我当年的妻子也熬成了老太婆,儿女成家立业,都过上了他们的好日子。
老伴去西安管护孙子了,我由于不习惯西安生活,加之又种了十多亩麦子,还有这文学爱好,喜欢写些小豆腐块,还要参加县上的许多活动。所以,儿子多次叫我,我去两三天后,就偷偷溜走了,无怪乎儿子对别人说:“我爸来我这里,好像他当年出差似的,停不了几天就走了。”
我常常看到西安哪里有咱农村好,现在就是不要啥,把我户口迁到西安,我都不去。
不去西安,生活就成了大问题,虽然我常对朋友吹牛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但酸辣苦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有时还真像没王的蜂,到处胡飞着。
忙天农活开了,既要干地里的,又要回家做饭,往往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不做饭吗?肚子饥,做下又吃不完,有时就放坏了。买的馍,吃腻了,我下定决心要自己学着蒸馍。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蒸馍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记得我第一次学着蒸馍,在电话里把老伴一一请教了,从烫面到发酵子,再到起面。
第一次我把面起得软了,又和了些干面,这不由得我想起了儿时奶奶给我讲的一个有趣故事。“那时有一个叫张三的人,他做饭常常把握不住,不管是擀面、蒸馍,把水倒多了,就加些面,面多了,又加些水。”以后人们就不自觉把这形成了一个口头禅。“张三做饭,干了加水,稀了添面。”
又一次,由于没有掌握住时间,起的面时间大了,蒸出来的馍酸了,我告诉老伴后,老伴把我数说了一顿,说我笨,面起上后要掌握时间,不停看着。那酸馍放到冰箱,我断断续续吃了几十天,剩下几个馍,实在吃不完了,最后我用油炸了一下,才勉强吃了。
第三次蒸馍,可笑的是我又忘了看时间,一直烧着锅,估计馍快熟了,打开锅盖,一看大吃一惊,馍都烤黄了,锅底都烧红了。我吓了一大跳,咋弄下这嘛哒,幸好荆笆是铝合金的,要不也会烧着了。
这次我没敢给老伴说把锅烧红了。
吃一堑,长一智。几次蒸馍的磕磕绊绊,使我大长了记性,蒸馍水平不断提高,比如冬季,我把面一烫,晾冷放上酵子,放在热炕上一天一夜,等酵子发旺后,再起上面,比如晚上把面起上,放在热炕上,第二早上面就起旺了。然后把面倒在案上晾凉,再放盆内把适量碱水均匀地调进,放在案板上使劲地揉面,等面揉匀后放在案上停半小时再蒸。
我常在县上待着,周六、周日才回家,蒸馍时我怕麻烦,一次蒸两锅馍放在冰箱,一般吃一月到四十天左右。前年老伴知道我一次蒸两锅馍放到冰箱,说我是懒得很,幸亏冰箱小,如果冰箱大,她看我一次能蒸半年的馍。
人常说:“什么事都是逼出来的。”这话一点不假,这蒸馍实实在在是逼出来的。
我蒸馍有一个大特点,每次蒸的馍小小的,看起来小巧玲珑,一次我可以吃二到三个。我最不爱吃大馍了,那大馍蒸的时间也长,我又怕把锅烧红了。
说句大实话,这四五年了,我蒸馍水平也越来越高,每次蒸馍都掌握时间,由过去的蒸馍、圆头馍、花卷、到现在的包子,样样打不住手,并且蒸的馍咧的十字花型,看起来分外诱人。我包的大肉包子,用料大葱、生姜、五香调料、包子调料等,一出锅,满院都有了香味,那是我最爱吃的、最拿手的。
这次快过年了,前一天下午我就发面,第二天早上我就蒸了两锅馍,这是年馍,馍咧的十字道花,好看极了,有些像梅花。
这次我突然又多了个心眼,把蒸的两锅馍,拍了照片给老伴发去。没想到老伴一次给我拃了五个大拇指,还打字说道:“红萝卜调辣子,吃出没看出,现在你本事大得都能上天了。”
作者简介

闰土,原名杨润杰,农民,陕西扶风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宝鸡职工作家协会会员、宝鸡杂文散文学会会员、西府文学社会会员、扶风县作家协会会员、扶风诗词楹联学会会员。在各种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上百件,并多次获奖。
曾出版散文集《一把苜蓿菜》《天渡》,曾参加省文学院举办的《关中片区》作家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