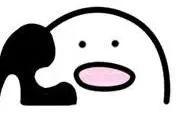秋分无生田。“青黄不接”是在晚春。而到了秋分的时候,只有黄的没有青的了,庄稼都可以“毕业” 了,希望不要“肄业”。
在江南:白露见稻花,秋分见稻谷。此时,天地之间有两种令人陶醉的颜色:金色和白色。正所谓: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
一个“好”字,似乎有两层含义,一是长得好,二是长好了。
秋分时节,正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时候。鸟飞欲尽暮烟横,一笛西风万里晴。
一笛西风,天气很美,诗人的解读更美!
以前读“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总觉得说说总可以吧。岁月静好的时代,不能总是“N 丈豪情”。秋风起时,能够想起美食,本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何况现在“吃货”也已经不再是贬义词了。记得医生曾经对我说,换季的时候,可以适当懒一懒、烦一烦、馋一馋。
过了十一黄金周,天儿就冷了,但还不算太冷。到霜降的时候,那就真冷了!北方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气温下降速度最快?就是霜降到立冬的时候。
但是,也不能小觑寒露,要是没有寒意,人家凭啥叫作寒露呢?霜降的冷,有差不多一半儿是人家寒露给攒下来的,霜降彰显的是累积效应而已。

深秋时节,有一种灾害,叫作寒露风。
农谚说:
棉怕八月连阴雨,稻怕寒露一朝霜。
寒露风原指华南寒露时节危害幼年晚稻成长的低温现象,或凄风(干冷型)或苦雨(湿冷型)。而当双季稻北扩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晚稻的这种“小儿科”疾病开始在秋分前后流行。所以广义的寒露风,未必仅是风,也未必仅发生于寒露,而是危害晚稻的低温综合征。
无霜期,是草木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光
登高望远时,恰是秋高气爽天气。但很多人依然无暇陶醉于金秋之美, 因为“九月九重阳,收秋种麦两头忙”。
九月田垌金黄黄,十月田垌白茫茫。
仅仅一个月之后,大地便卸了妆,重新以素颜示人。从前是以田垌白茫茫形容霜雪,但是现在,偶尔有白茫茫的雪,经常是灰蒙蒙的雾。
有诗云:
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
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宋]杨万里)
霜降时节,气渐寒,霜如雪,而且雾气加重,清晨时常处于低能见度的状态。搁在现在,可能是只凭 GPS(全球定位系统)认前村。
在俄罗斯,霜冻的辈分很高,它是一位爷,霜冻爷爷(Дед Моро́з)。霜冻爷爷的职责和圣诞老人差不多。但之所以叫作霜冻爷爷,或许是因为那里,霜冻“当家”管事儿的时间很长,人们在他面前都很卑微。在俄罗斯情景喜剧《爸爸的女儿们》中,就有这么一个桥段,6 岁的小女儿“小扣子”为了促使父母早点和好,便在风雪天离家出走,满大街去找霜冻爷爷,向他求助。可见在孩子们心目中,霜冻爷爷是有多管事儿啊!
为什么会专门有“无霜期”这个概念,而没有无雷期、无雪期的说法呢?因为霜冻执掌着作物的生*予夺。无霜期,是草木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光。
全国平均而言,“以风鸣冬”的立冬时节是一年之中气温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段。天气越来越冷,到小雪的时候开始下雪了。

但对南方而言,“(农历)八月暖,九月温,十月还有小阳春”。暖气团撤退之前,还可能会恋恋不舍地营造一番和暖的小阳春,一番感人的作别。这时的江南,“禾稼已登”,小阳春正好晒谷,大家心情好爽。有诗云: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节气中有三组大小节气
节气中,有三组大小节气: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于是经常有人探讨:小暑大暑谁更热?小寒大寒谁更寒?总的来说,小暑大暑经常“没大没小”,伯仲之间;小寒大寒,倒是小寒略胜一筹。
那么,小雪大雪是如何区分大小的呢?所谓的大与小,并非只是降水量的大与小,而是积雪的多与少。小雪时节,一天当中的温度还在 0℃上下晃悠,所以雪可能是下了就化,化了又冻,冻了又消融。而大雪时节的降雪,飘落之后就有可能“坐住了”。地上白茫茫的积雪,给了人们特别好的“印象分”。
在华北,冬小麦的冬灌,讲究的是:
不冻不消,冬灌嫌早;
一冻不消,冬灌嫌晚;
又冻又消,冬灌最好。
说的是如果还没有上冻,就太早了;如果冻得结结实实,就太迟了;只有“又冻又消”,就是白天消融、夜晚冰冻,才是冬灌最适宜的时节。这便是在小雪时节。
谚语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大地开始封冻了,然后水面也开始结冰了,船都可以休息了。“三月初一试船雨”,待到阳春三月,它们又可以愉快地上岗了。
小时候 12 月就可以穿上冰鞋或者坐上冰车,高高兴兴地滑冰了。不像华北地区,三九四九才能冰上走。

但是,随着气候变暖,“冰上走”可得留神,危险莫过于“如履薄冰”。
2018 年立春,我才想起去颐和园滑冰,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不停地巡查冰层融化的情况了。这里的滑冰季是 1 月 6 日至 2 月 4 日,只有小寒大寒两个节气,而且还是在大寒极寒的背景下。
冬至,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大” 节气,因为它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阳光最疏远我们的时节。“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这是古人心目中阴气始衰、阳气始生的节气, 阴阳流转令人充满期待。所以到了冬至,人们会相互道贺,文雅的贺词便是:迎福践长。
人们在最黑暗的时令看到希望,日子会一天一天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