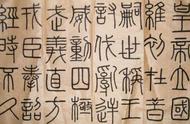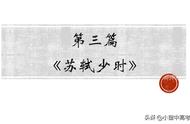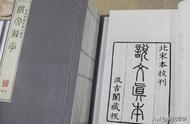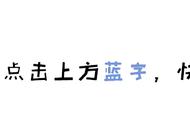中国古人在春播时过清明节,奉爱祭春;在秋收时过中元节,慎终追远。其实就是在用生命的方式联络死亡
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木本”汲“水源”,以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等理念传承孝道,以视死如生、视亡如存等理念阅读生命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欣 实习生 韩雅宁

人数超2.9亿——这是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1.1%。
“老”的人群在扩大,“老”的速度在变快。不仅如此,“老”还为慢病叠加、重病多发所扰,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面临挑战。
与“老”仅隔一箭之地,死亡终将到来。怎样优雅地迈向生命的终点?近年来,各地推动的安宁疗护,尝试提供一种让“生死两相安”的范式,回应中国人对善终的朴素愿望。
在实务层面,安宁疗护从业者们面对着一系列直击人心的人文之问: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对死亡有禁忌,对优逝有期待,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纠葛如何化解?如何以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涵养生命教育的土壤?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邀请业内专家学者一起寻找答案。
“死不是我的”
《瞭望》:在安宁病房里采访,听到一句话,“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以“收口”比喻生命最后一程。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结束?
路桂军:《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终命,也就是善终。我国传统文化里,对善终的期望是,当生命走向终结,没有遭遇横祸,能预先知道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疼痛,心中了无挂碍地安详离世。
胡宜安: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中说过:“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千年农耕文明里,家是寿终正寝之地。濒死之际,躺在家乡祖屋的老床上,身边环绕着子孙亲朋,交代后事、安详离去。浓郁的伦理亲情氛围可以给当事人极大的心理安慰,即自己的生命不会因死而终灭,反而会在子孙的生命中得到延续。
宁晓红:有一位93岁的老人,肺部和膀胱有肿瘤占位。因为尿频尿痛,最多时一天要换76片尿布,老人无法安眠,*不断。入住安宁病房后,老人排出脓尿并接受抗感染治疗。她对女儿说:“哪儿都不疼了,就像是待嫁的新娘,每天高高兴兴等着。”这是关于优逝的浪漫表达,我的理解是,少痛苦、有尊严,善终复善别,生死两相安。
《瞭望》:古人追求的善终,听上去很“奢侈”。进入现代社会,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从“出生”到“入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很多临终的场景谈不上逝者安详,生者安宁,也离家很远。如何看待这背后的原因?
路桂军:确实如此。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我的人生像一本书,有很好的开篇,很好的高潮,但到尾声阶段,行文却特别仓促,几乎是凌乱的。身体的疼痛,导致我寝食难安,我根本无法把思绪整理清楚,整个人简直成了断壁残垣。实现圆满完结仿佛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
胡宜安:现代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能源于“死不是我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把死亡变成一种“他控”的生理过程,临终不再是有本人及家人共同参与的生命旅程,而是交由专业人士和精密仪器掌握的死亡之旅。某种程度上,面对死亡,很多人只是旁观者。当属于“我”的那一刻迫近,大多数人毫无准备,恐惧焦虑由此而生。
宁晓红:现代医疗中针对病人的治疗,过度之处需要纠正,不足之处正在补充。有一位肺癌晚期的老人,全身多发转移,浑身疼痛,严重厌食,家属坚持使用靶向药物十多天,老人越发羸弱。我们为他开了一些缓解疼痛和不适的药,老人状态好转。他说:“你给我开的,才是真正‘靶向’的药。”
医学的本质是帮助。近年来,缓和医疗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入,说明越来越多医疗从业者意识到,应把单纯对病情的关注,转变为帮助病人舒缓痛苦、抚慰精神、安顿心灵、肯定生命价值等的“全人”照护。
为了更好的生
《瞭望》:人一定会死,但在多数人的思想意识里,却没有死亡的一席之地,或者说,回避给它一席之地。这是为什么?
胡宜安:一些人忌讳谈死。很多时候,我们在屏蔽死亡,我们打开电视会发现有关死亡的话题被压缩到医院、火葬场和墓地等少数场景,似乎死亡意味着“战败”。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体两面,这一点,我们的先人早已想通。农耕文明里,春播粟,秋收籽。中国古人在春播时过清明节,奉爱祭春;在秋收时过中元节,慎终追远,其实就是在用生命的方式联络死亡。孩子们的科普读物里也有“一鲸落,万物生”的说法,死完成生,死又孕育生,生生不息。树立乐生顺死的生死信念,有助于超越死亡焦虑。
路桂军:直面生死,是善终、善别、善生的必要条件。我们常常讨论“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却很少谈及生命如何结束。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父亲因肝脏肿瘤去世时,他才6岁。看到父亲因腹水过多而高高隆起的肚子,他问:“爸爸怎么了?”妈妈解释说,爸爸吃了一颗坏种子,种子在他的身体里不断长大。自那以后,年轻人再也不敢吃任何种子。
论及“他死”,尚且笨拙,遑论以“你”“我”来探讨生死。但这是必须要实现的进阶,只有以第一、二人称谈生论死,“我”才能设身处地思考“你”困扰什么、焦虑什么、恐惧什么,针对性地给予帮助;“我”也能通过“遗愿清单”明确诉求,要什么、不要什么,“你”照章处理就好。
宁晓红:对于死亡话题,应该积极讨论。否则,当那一刻真正来临,会手足无措,这很残忍。曾有一位生存时间以“周”计的老人问女儿:“我今年什么时候死啊?”他女儿说:“我哪知道啊,你5月份的时候差点就不行了,后来又缓过来了,说明你有福,得多活一阵儿。”老人说:“你把我小时候喜欢吃的,北京所有小吃都给我买来尝一遍。”在这里,积极的、没有忌讳的讨论,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意味着握有选择权的自主决策,意味着不留遗憾,意味着好好活,直到最后。
《瞭望》:除了讨论,我们还可以了解哪些与死亡相关的知识?
宁晓红:知晓生命的轨迹。如果罹患肿瘤,生命将如何结束?如果是心肺功能衰竭,轨迹又有何不同?个体的离世,各不相同。一位84岁的老人接受肺癌治疗三年多,没有多少痛苦症状,每次到我门诊,似乎就是“聊天儿”,聊她想要换一家做饭更好吃的养老院,聊她对死亡不恐惧,也不要插管。她是在临终前一周,才出现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最后在急诊离世,没做插管。疾病发展各有规律,以充分了解为前提,为死亡做些准备,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路桂军:了解死亡的过程。死亡有着一般规律:首先味觉丧失,其次四肢湿冷,然后昏沉嗜睡……我们应该了解并尊重这个过程。我曾跟一位患者聊天,开玩笑地问“最不想见的人是谁?”他竟然指向日夜守护的妹妹。问起原因,他说,妹妹遍寻各种美食“投喂”,认为“吃两口,吐一口,还是赚的”。但她并不知道,那种吃了吐、吐了吃的感觉,实在太痛苦了。顺势而为,理性照护,才能促成生命尽头的安详。
《瞭望》:高密度处理生死事件,给您的生死观带来哪些改变?
路桂军:有助于我们自身理解死亡。我有一位患者家境优渥,从小到大,只喝冰水,后来食道癌剥夺了她的“口福”。临终前,她对我说:“我从未感恩过任何一口滋润过我咽喉的水。”这对我就是个宝贵的提示,令我更加珍视当下拥有的,对生命更存敬畏,在事业上更高效,情感表达更充分。
探“木本”汲“水源”
《瞭望》:社会对安宁疗护的误读仍存。有人觉得安宁疗护意味着治疗降级,或者放弃治疗。如何为提高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质量,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胡宜安:我们不能将一座高楼大厦建立在一片沙滩上,对生死话题的讨论应该从娃娃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进行的生死启蒙早已有之。古代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有一节名为“疾病死丧”,开篇第一句是:“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这句话点明了幸福、长寿、健康、安宁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正视了疾病的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的极端确定性。
小草为何枯萎?花朵为何凋谢?小狗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生病?爷爷奶奶会死吗?伴随年龄增长,生死问题由远及近,最后抵达自己的死亡:我死后将归于何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对这“十万个为什么”的思考和求解过程,也是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我在大学开设《生死学》选修课已经24年了,希望带领同学们以死观生,引导学生在优化自我生命的同时,学会更加重孝守礼、慎终追远。
路桂军:其实我们天天在谈生死,只是没意识到而已。有次开会,上台时我摔了一跤。主持人担忧地说:“摔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顺势开启了科普:何谓三长两短?棺椁承载尸身前,是左右及底三块长,前后两块短。一旦盖棺就是四长两短。对于死亡话题,多喊狼来了!喊得足够多,有助于降低死亡恐惧,当那一刻来临,可以少一份无措,多一份从容。
宁晓红:医学对象应被理解为完整的、有喜怒哀乐的、有温情的人,而不仅仅是疾病的载体。2014年,在协和医院教育处的支持下,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启《舒缓医学》研究生选修课,首次开课时仅有7名学生报名,其中还有一半儿是护理专业的。如今,《舒缓医学》已经成为协和医院“4 4”(本科教育4年 医学院教育4年)试点班学生、博士后学生和临床专科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并已融入本科八年制学生课程内容。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让医学生和医护人员了解如何面对和帮助接近生命终点的人。让大家清醒意识到,这是所有医务工作者绕不过且必须做好的一件事。
路桂军:生死事大。生死不仅是关乎个体生命的“大事”,更是国家治理的“大事”。我们应该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木本”汲“水源”,以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等理念传承孝道,以视死如生、视亡如存等理念阅读生命,满足中国人对安宁的追求,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符合时代需要的善终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