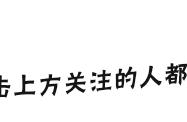扣肉是一道遍布大江南北的菜肴,大概养猪的地方,就会有这道菜,只不过叫法略有不同。有些地方叫千层肉,有些地方叫烧白,福建同安叫封肉,都很形象。两广叫扣肉,“扣”字意指将制成后倒盖于碗盘中使其翻面的过程,见过的人会觉得此名更加形象。
在我的饮食生涯中,扣肉这道名菜,有如一些男人的择偶标准——首先要上得厅堂,扣肉起码是华南各地宴席必不可少的硬菜,说它上得厅堂完全可以;其次,要闹得闺房,尽显本色,而不像在厅堂上克己复礼,装得雍容华贵,摆臭架子。对这一点,我有很多个人心得。对扣肉这种近乎背道而驰的要求,我称之为“红黑两道”,红道就是老老实实在宴席上当硬菜,备受尊崇;黑道就是由主人率性胡来,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我知道并且铭记在心的第一道硬菜,就是扣肉。扣肉地位最高的地方,就是两广。两广有俗话,无鸡不成宴。其实,没有扣肉更不成宴会。哪怕今天有人忌恨脂肪,不再视扣肉为美味,但红白喜宴上,还是少不了扣肉。不管在家里做,还是上馆子办,没有扣肉会让人笑话。我小时候,大人喝喜酒会打包,哪天午饭看到家长拿出一大脸盆杂烩加热,那就是他们头天喝喜酒去了。现在我还想不清楚,喝顿喜酒,怎么还能打包那么大一脸盆菜?这盆杂烩里,什么都有,也不全是肉类,还杂着大量木耳、粉丝、豆腐、黄花菜、土豆之类素菜,估计是配肉菜的。鸡鸭鱼猪牛之类荤菜也占一半,或大块或小块,或三块或两块,加起来也占一半以上。当然,肯定会有几块滴着肥油的扣肉。

扣肉胚子
老实说,这种整脸盆盛回来的杂烩,味道真是奇美,只能用“异香”来形容,后来我再也找不到这种香味。大概各种菜混到一起,诸味自动调和,生出新的味道来了。整个味道,甜甜的,是菜肴的那种甜,不是糖的甜。一股暗香不断涌出,既沉抑又张扬,无论夹什么食材,都是一种新合成的味道,很难尝出本味。这个味道,就叫香。我小时候吃不得肥肉,不是娇生惯养,而是生理性的条件反射,一沾肥肉,哪怕不让我知道,我也会当场吐得死去活来。但我老娘经常拿此说事,遇上吃喜酒打包回来的扣肉,我是可以连肥带瘦吃一块的。
我父亲却爱吃肥肉,光是瘦肉他吃不下。他很小就招工进厂,辛勤地做了一辈子农场工人,什么个人爱好都没有,连最简单的棋牌都不会,连普通话都讲不了,晚年后只能坐在沙发上,不断地摁遥控器。偶尔有讲家乡客家话的客人来,他总要抓住机会和人家交流一下,但颠来倒去只是反复问,是否相信他的两大杰作。一是后生时一顿吃过两斤半米煮的饭;二是后生时一口气吃过两斤扣肉。这种艰难时世打赌吃东西的段子,到处都有一些。我相信他有过一口气吃下两斤扣肉的壮举,这老头一辈子老实,连吹牛材料都没攒下什么,确实被狠狠饿过,所以话头不虚。这类段子说明,有过一个时期,人们长期忍受饥饿,不然不会动辄拿能吃多少来打赌;打赌的标的物,一般被视为美味,但打赌的量远超正常的食量,但架不住经常有人超常发挥。所以,这类段子开了个头,没有人能猜到最后的输赢结果。扣肉人人爱吃,但是几乎没有机会痛痛快快吃一顿。成为赌注,每个人都在惦量自己的赌本,但凡有点希望,就想博他一博,好生吃顿扣肉。赌博的诱惑正在于此,能让人在*的权衡中坠入地狱。

吃之前,要将扣肉胚子先行下水锅煮软
如果放到今天来打赌,一口气吃两斤扣肉,不太有人敢接招了。一般宴会上的扣肉,一份不过一斤多肉。扣肉只是饥饿年代的集体向往,有屡屡成为赌注的潜质。在人们不再受困于油水缺失、饮食品类极大丰富的今天,越来越多人忌讳脂肪、肥肉,扣肉不再是高大上的代称。所以,两广人才说“无鸡不成宴”,而不说“无扣肉不成宴”,虽然宴席上扣肉必不可少。其实,扣肉已经以随风潜入夜的姿态,默默地融会在两广人的日常饮食中。很多馆子能点到扣肉,且不必说。宴席上有份扣肉,总会有人夹去吃,最后也也是盘子精光。吃一两块,不至于当场毙命。两广人每日早餐一碗米粉,其中一种候选的热门菜,就是扣肉。对胆固醇的疑惧,挡不住下水杂碎的热销;同样,对脂肪的担忧,也不必着眼于吃了一两块扣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