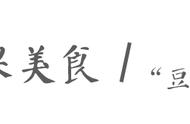此件回忆,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我想说的,是我从没在家里吃过这道菜,黄泥螺。不知是台湾的泥螺不合用,抑是我妈哪怕在故乡,亦不见得是吃黄泥螺那一挂的?总之,我也没问过。最大的可能,是我妈到了台湾后,凡吃食已逐渐一点一滴地进入自然的“现代”矣。当然,这也是我自己中年后猜想的。
我妈也偶尔包水饺。这是她惟一做的北方食物(包子、馒头从没做过)。她的馅是小白菜猪肉馅,皮是切面店买来的皮。小白菜先用滚水稍煮一下,捞起略放,俟凉,再放进纱布里,把菜汁拧干,取出,剁碎,再放进绞好的猪肉里拌。拌时,加盐,及麻油。也加很少的酱油。我没看过她加胡椒粉,也没加姜末。显然,和有些省份的调味法,或店里的调味法,不同。为什么是小白菜?我没问过。这小白菜剁碎了,包在饺子皮里,下好,捞起在盘子里,皮内透出绿色,哇,我还记得!

当然,我妈也炒年糕。炒法十分简单,就是肉丝蔬菜炒宁波年糕。有时是白菜肉丝,有时是青江菜肉丝,有时是雪菜笋丝;很偶尔呢也会用草头炒年糕,非常翠绿的外观,也非常翠绿耐嚼的美味。年糕片必须炒得片片分开,也必须和肉丝蔬菜炒得很融合有滋味。这赖于炒的人要细心、手要勤于拨动。我妈炒得固然好,但即使是她,有的年糕片也会两三片黏在一坨里,我们小孩一吃,眉头就皱起来了。当然,做成汤年糕,也很多。
这年糕,我妈未必到菜场常态地去买,倒是有挑担子的年糕贩子,到了我家门前,用家乡话叫卖,于是我妈买上一叠。所谓一叠,是三或四条年糕排成一层,七八层用绳子扎起,上铺一张印着品牌的红纸,是为一叠。这挑担子用宁波话叫卖年糕的场景,是五六十年代的好风景。他在巷子里叫卖,但到了他知道的宁波人家门前,会多停一两分钟,想,这同乡今天会否开门买他一叠!
我妈也包粽子,宁波人嘛。包的就是坊间会卖的湖州粽子,口味也是就猪肉和豆沙两种。记忆中,邻居都赞不绝口,说她的粽子真好吃!她也包汤圆。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芝麻汤圆。自己炒馅、调糖,但糯米粉好像是买来的,并没见她自己捣米什么的。酒酿也是自己做的,却未必是为了配成“酒酿汤圆”。这几样手艺,很偶尔会在她心中生出想改善拮据环境的念头,差一点要开一爿小小的卖浙宁点心的铺子呢(就像人家在南门外开“蔡万兴”之例)。
我家也偶吃面食。但做法是南方人版。像葱油饼,我家是将面糊(里头拌了葱花)用汤杓舀进有些许油的炒菜锅里,如此煎成的,宁波话称“油抹黄”。我十岁时也会做。这事看一次就会。十岁的我,在巷口玩累了玩饿了,会回家煎几片油抹黄,或是烧一碗“雪菜肉丝面”。其法是先切肉丝,再切咸菜(将一小把咸菜切成细段),在炒菜锅里搁花生油,油热了,先投肉丝,炒几下,投咸菜,炒上一阵子,加入白开水,盖锅盖。等水滚了,投细面(切面店买来的、用小段杂纸圈在晒干细面腰上的),再盖锅。又快滚时,掀锅盖,审看一下,再盖,再掀,差不多好了,便是一碗咸菜肉丝汤面。
写着写着,突然惊觉这是六十年前我的“作品”。十六七岁后我再也没做过这种先炒料码、再加水、再投面的煮面法。也再也没在煤球炉前先移开进气铁片(如此静置的煤球因空气灌入可致火烧大),再将炒锅置上等那些属于老年代的动作矣。唉!
以上说了不少童年的事。那么聊些别的吧。
假如某天你经过一个小镇,见一小馆子,只卖几样你熟悉的家乡菜,那会是多么的教人感动啊!比方说,你进了一乡间小馆,他只卖几样东西,像呛蟹,像拖黄鱼,像红烧墨鱼,像夜开花炒鳝糊,像白菜肉丝馅的春卷,再有一锅菜饭,哇,如果他敢卖这几样东西,那一定是武林高手,而隐居在某个荒村小店!
如果我坐下一尝,哇,做得还真不错,那这时我会怎么想?老实说,我可能心中有淡淡的哀愁,一来我会担忧他开不久,二来,他应该有另外一种埋藏在心底的重要念头。
也就是,这样的馆子,有一点像掌柜开这家店,是为了圆一个心愿,是为了等一个远方的长辈。那长辈已太老太老,常年住在纽约的长岛,或许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会来到这个小镇,若这长辈吃过了这一顿最精采的饭,不久后离开人世才会毫不遗憾。
这种菜肴是他的心愿。当这个心愿圆了,他第二天把店一收,就可以云游去了。
【俯拾皆是风景】是舒国治在笔会的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