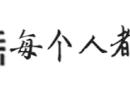作者简介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边疆与国家建构问题。著有《六朝士风研究》,译著有《哈佛中国史·分裂的帝国》。

摘 要: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关键词:后秦;姚兴;中华认同;汉化;官僚君主制;宗室出镇
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是中国史叙事的重要内容。学界一直围绕着“汉化”是否真实发生、“汉化”是否为少数民族政权的主要面向等问题展开富有争议性的研究。少数民族立国主要集中在十六国北朝与辽金元清两个时段,二者所处时代不同,“汉化”的内涵与表现也不同,实难以脱离时空关系作抽象论述。在十六国北朝史的通行叙事模式中,胡汉关系是主要矛盾,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成败取决于对这一关系的把握,“汉化”与“胡化”则是两种处理胡汉关系的方案,代表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在唯物史观的叙事中,“汉化”是指以汉文化为观念主导,包含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具有社会发展的意义。在这一基础上,近年来的研究更进一步阐发少数民族政权中华认同的观念,并尝试将胡汉对立思维中的“民族”叙事置换为多元一体思维中的“天下”叙事。本文拟在这一研究视域下,以十六国时期“汉化”程度很高的后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所具中华认同的意涵,并从制度认同的角度考察后秦推行官僚君主制、宗室出镇制的政治考量与历史后果,以此揭示后秦之中华认同所具的时代普遍意义,由此为“汉化”暨中华认同命题提供一个可资讨论的阐释路径。
一、中华认同:后秦的国是
后秦在姚兴统治前期达到鼎盛,唐代修《晋书》的史臣赞誉姚兴:
子略克摧勍敌,荷成先构,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弟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取汾绛,陷许洛,款僭燕而藩伪蜀,夷陇右而静河西,俗阜年丰,远安迩辑,虽楚庄、秦穆何以加焉!
《晋书》史臣认为姚兴超越了春秋时期的楚庄王、秦穆公,建立了卓越的功业。《晋书》所述史实如下:皇初三年(396年)逼降西燕署河东太守柳恭,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镇蒲坂,控制了关中进出河东的通道;皇初五年(398年)遣镇东将军杨佛嵩攻陷洛阳,东晋“自淮汉已北诸城,多请降送任”;弘始二年(400年)灭亡陇右乞伏氏的西秦;弘始五年(403年)逼降河西的后凉;弘始九年(407年)以外交手段使南燕称藩;弘始十年(408年)蜀地谯纵遣使称藩。虽然后秦直接统治的疆域最盛之时是在弘始七年(405年),此后由盛转衰,但不可否认,姚兴一度成为淝水战后最有可能再造统一的君主,南燕、谯纵的称藩在一定程度上便是缘于姚兴的声威。即便在后秦陷入内忧外患之后,最主要的敌人赫连勃勃也不得不承认“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采用“游食”战法经略岭北、河东。
《晋书》史臣认为姚兴的成功是基于任贤(“虚襟访道,侧席求贤”)、睦亲(“敦友弟以睦其亲”)、明赏罚(“明赏罚以临其下”)等举措。《晋书》曾以“变夷从夏”来概括苻坚的政治路线,上述对姚兴的政策分析其实也是将其放在华夏政治传统中予以解读。无论是北魏崔鸿所修《十六国春秋·后秦录》、东魏魏收所修《魏书·羌姚苌传》,还是唐人编修《晋书·姚兴载记》,均没有对姚兴“夷”的身份进行描述,仅仅交待祖父姚弋仲为南安赤亭羌人。正如先行研究所揭示的,姚兴已是滠头集团的第三代。滠头是后赵将姚弋仲所部迁徙至关东的安置地点,属冀州勃海郡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姚兴之父姚苌即出生于此。姚弋仲所部在迁徙过程中及居住滠头期间,已经与其他部族和汉人豪门相混融,形成了具有内部凝聚力的集团。可以说,不能将滠头集团与羌人族群完全等同起来。在与建立前秦的枋头集团进行权力竞争时,滠头集团也并不将氐、羌的族群身份视作划分政治立场的标准。至姚兴之世,滠头集团的文化面貌已经实现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在文化修养上已与汉人士大夫无异。
姚兴在前秦时的官职是太子舍人。太子舍人为东宫近侍,掌管东宫文书,对任职者的文学才华、言谈举止、德性操行均有非常高的要求。如西晋时选补太子舍人的夏侯湛,便是“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并称“连璧”,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当与夏侯湛相去不远。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对姚兴的叙述是:
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勗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
赵翼的叙述皆取材于《晋书·姚兴载记》,但《晋书》对姚兴崇文好学事迹的记载远远不止于上引两条。与同时代的少数民族君主相比,姚兴在成为君主之前已经与汉人士大夫声息相通了。按《十六国春秋·后秦录》所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可见不止于姚兴,整个南安姚氏皆秉持对华夏的身份认同意识,认为家族血缘源自虞舜、“世为羌长”的权力身份缘于夏禹的册封。南安姚氏的这种身份认同亦为周边族群所认可。如沮渠蒙逊听闻刘裕攻灭后秦,对左右说:“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今镇星在轩辕,而裕灭之,亦不能久守关中。”在北凉君主沮渠蒙逊眼中,姚氏不仅为虞舜之后,而且是轩辕氏的苗裔,代表了中华正朔,所以他近乎诅咒地预言刘裕难以长久占据关中。可见由南安姚氏所统治的后秦,在当时已被周边政权视作华夏政权。《魏书·贺狄干传》记载:
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之。弟归,亦刚直方雅。与狄干俱死。
贺狄干为鲜卑人,任职北魏北部大人,因秦魏交恶而被姚兴扣留在长安。在长安期间学习了书史、经典,具有了儒者的举止风流。待贺狄干返回北魏之后,北魏道武帝看到他的言语衣服带些后秦羌人色彩,而不看他其实也是饱读诗书的儒者,将他与弟弟贺归一同*掉。
再如,姚兴派遣尚书郎韦宗出使秃发氏,韦宗与秃发傉檀谈论后感概:“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韦宗的这番言论是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下自居为华夏,言语虽是称赞秃发傉檀,却将之视作夷狄。当姚兴决定放弃对凉州的直接统治而转以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之时,凉州申屠英等二百余人遣主簿胡威赴长安劝姚兴收回成命,所列理由是“今陛下方布政玉门,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玁狁,忠诚华族弃之虐虏”,指责姚兴“忽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凉州士族以后秦为“华”,以秃发氏为“玁狁”。
由此可见,姚兴按照华夏政治传统推行任贤、睦亲、明赏罚等举措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群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华认同是后秦的国是。
正因后秦以华夏正朔自居,所以姚兴的政治理想是再造大一统。姚兴即位后,于皇初元年(394年)便攻灭了与姚苌缠斗十年的苻登,随后主要的战略方向转为关东,取得了控制蒲坂、占据洛阳的功绩。其实当时无论是河东的西燕残余势力,还是洛阳的东晋势力,皆无意也无力对后秦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后秦的西境却是强敌环伺。陇西的西秦是苻登盟友,长期支持苻登对抗后秦,且乞伏乾归一直觊觎关中:“若枭翦姚兴,关中之地尽吾有也。”河西的后凉也正处于鼎盛期,吕光曾下书“朕方东清秦赵,勒铭会稽”,言明要将后秦视作征战的对象。姚兴之所以暂弃西境强敌而主攻东方,主要是想夺取与长安同具神京地位的洛阳。赫连勃勃御史中丞乌洛孤曾结盟于沮渠蒙逊并在誓言中说:“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乌洛孤称长安、洛阳为“二都神京”,将“神京”的荒废视作西晋灭亡后“祸缠九服”的象征。乌洛孤为少数民族,可见在当时“九服”之中,无论夷夏皆将“神京”当作正统性的标志。正是在这一政治语境中,姚兴才以兴复洛阳为重要战略目标。
占领洛阳后,姚兴便开始措意经略东晋。当时桓玄势力开始崛起,东晋辅国将军袁虔之等投奔姚兴。《晋书·姚兴载记》记述了姚兴在东堂引见袁虔之等人的情形:
(姚兴)曰:“桓玄虽名晋臣,其实晋贼,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办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兴大悦,以虔之为大司农,余皆有拜授。
姚兴之所以大悦并拜授袁虔之等等官职,乃在于袁虔之所言契合了他“廓清吴楚”的政治理想。与袁虔之的情况相反,东晋河南太守辛恭靖被俘至长安,姚兴称“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辛恭靖却答以“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惹怒姚兴而被幽禁。
正是在“廓清吴楚”之政治理想的驱动之下,姚兴积极经略东南。弘始七年(405年)东晋平西参军谯纵割据蜀地,姚兴予以了积极支持,派遣平西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支援谯纵与东晋作战。弘始十二年(410年)谯纵策划再度用兵东晋,姚兴先派曾任东晋尚书左仆射的桓谦南下,发挥桓氏“部曲遍于荆楚”的政治影响力,又派遣前将军苟林率骑兵与之会师。姚兴虽囿于国力,未能如苻坚那样发动统一南北的战争,但是他对东晋的经略,则与苻坚的政策一脉相承。
二、官僚君主制:以扬弃政治习俗为指向的后秦国制
因后秦统治集团早就在精神层面自居为华夏,如果说在建立政权之后存在“汉化”问题的话,那么主要是指在国制上采用汉魏晋王朝的官僚君主制。姚苌建立后秦,先于白雀元年(384年)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其中大单于号源自匈奴。两年后(建初元年,386年)姚苌即皇帝位,不再以单于号自称,实际上放弃了以胡族名号构建政权的政治路线。姚苌定国号为大秦,定都长安(改称常安),立妻虵氏为皇后,立长子姚兴为皇太子,置百官,在制度层面将后秦改造为汉魏晋王朝的样式。同时采纳五德始终说,“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将后秦政权置于华夏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
皇帝制度是官僚君主制的核心,姚苌、姚兴均按汉制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姚兴、姚泓均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立储本是为了巩固皇权,明确官僚阶层的政治预期,然而后秦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却与南安姚氏、滠头集团推选领袖的政治传统相互冲突。皇帝制度及嫡长子立储制度断绝了有才能的宗室成员晋升为君主的合法可能性,将皇帝与太子推向了南安姚氏乃至整个滠头集团的对立面。尚未接受汉式制度规训的宗室成员转以夺嫡甚至夺皇位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导致姚兴统治后期宗室斗争层出不穷,《晋书》将之称为“萧墙屡发”“人有危心”。
弘始八年(406年)秃发傉檀占据姑臧,次年(407年)赫连勃勃叛秦,后秦由战略扩张转为战略防御。《晋书》以“边城继陷”“战无宁岁”“伪境日侵”来描述这一阶段后秦的处境,外部危机成为后秦宗室夺位的契机。弘始十一年(409年)姚兴派遣幼弟平北将军姚冲与征虏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姚冲率军抵达岭北后,谋划回师袭取长安。这一计划遭到狄伯支的反对,姚冲为此鸩*了狄伯支。狄伯支为后秦宿臣,姚苌起事以之为从事中郎,姚苌临终前又委以顾命大臣辅佐姚兴。姚兴之世,常派遣狄伯支与诸皇弟共同领兵,如在秦魏柴壁之战中随同姚平领兵。狄伯支在军中的角色如同姚兴的监军。姚冲谋*狄伯支使得宗室间的矛盾无法再被掩盖。《晋书》载:
兴自平凉如朝那,闻冲谋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绝人,犹欲隐忍容之。敛成泣谓兴曰:“冲凶险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寝不安席,愿早为之所。”兴曰:“冲何能为也!但害名将,吾欲明其罪于四海。”乃下书赐冲死,葬以庶人之礼。
面对姚冲谋反,姚兴“犹欲隐忍容之”,但在后军将军姚敛成的泣谏之下不得不予以处置。姚敛成在此前一年(408年)曾随姚兴子姚弼攻伐秃发傉檀而丧师七千余人,时任卫大将军的姚显(姚兴弟)将战败责任“委罪”于姚敛成而非主帅姚弼,姚敛成成为宗室政治的牺牲品。弘始十六年(414年),姚敛成讨伐叛羌战败后选择投奔后秦的死敌赫连勃勃,可见他并非如其所言那般忠心,劝谏姚兴诛*其弟姚冲当是出于宗室的内争。姚冲事件不仅将皇亲间的皇位争夺公之于众,而且也将南安姚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暴露出来。
事实上,姚兴对皇权所面临的威胁并非没有警觉,弘始四年(402年)立姚泓为太子便是应对这种威胁的策略之一。当年二月北魏侵后秦,长安大震,姚兴决意亲征北魏,时任司隶校尉的姚显进言:“陛下天下之镇,不宜亲行,可使诸将分讨,授以庙胜之策。”姚兴在柴壁之战前立太子,正是为了使太子代天子坐镇长安,由姚显及尚书令姚晃辅助太子入直西宫。柴壁之战以后秦的失败宣告结束,姚兴声望受损,本该罪己,但姚兴反而立昭仪张氏为皇后,册封皇子懿、弼、洸、宣、谌、愔、璞、质、逵、裕、国儿等为公。这一有违常规的举措反映了姚兴急于将皇子们扶植为政治势力用以拱卫皇权的用心。
姚兴立太子是为了应对危机,故对太子有才能方面的要求。然而,长子姚泓“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兴将以为嗣而疑焉”。是坚持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还是选择有经世之用的储君,姚兴是处于矛盾困境中的。在犹疑之后仍选择立长子为太子,表明姚兴将维系君主制的恒定性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同时,姚兴又推出了一个替补方案,培养有经世之用的皇子,他选择的是姚弼。此时姚兴的构想是将自己的核心家庭成员视作一个整体来拱卫皇权,排斥诸弟及其他宗室成员对最高权势的觊觎。
弘始十年(408年),姚弼被委以征伐秃发傉檀的军事指挥权,这场战争关系到后秦在河西、陇右的统治成败,足见姚兴对姚弼的信任。姚弼败绩后,姚兴又任命他为雍州刺史,镇守安定。安定是岭北的核心区,岭北是后秦最重要的军事防卫区,是其军事力量之所出。从上述姚弼履历可见,姚兴最初计划将姚弼培养成军事将领。随着姚弼权势的增加,他开始有了夺嫡的谋划。姚弼夺嫡使姚兴核心家庭出现分裂,原本用以拱卫皇权的势力转而成为皇权的内耗因素。《晋书》载:
初,天水人姜纪,吕氏之叛臣,阿谄奸诈,好间人之亲戚。兴子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时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至是,兴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矣。
按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姚弼以大将军兼尚书令、侍中的时间是弘始十二年(410年),此前弘始九年(406年)六月姚泓曾被委以录尚书事。经过姜纪的运作,弘始十二年(410年)时姚弼完成了由边将向宰相的身份转变,而且在职权上不低于太子姚泓。《晋书》认为姚弼权势的形成与卫大将军姚显的支持有关。如前所述,在弘始十年(408年)与秃发傉檀的战事中,姚显维护姚弼而委罪于姚敛成,双方结党已见端倪,但姚弼入辅的关键原因是姚兴的政治需要。陇东太守郭播曾建言:“广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镇督一方,愿陛下远鉴前车,近悟后辙。”姚兴以沉默的态度婉拒让姚弼“镇督一方”的建议,坚持将其留在中枢。后来姚弼在姚兴病中“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被甲伏于其第”,姚兴知道后“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姚兴将皇权与宗室间的矛盾视作主要矛盾,而将核心家庭的分裂视作皇权的内部矛盾,故他明知姚弼势力成长会危及其储君之位,却仍然将姚弼留在中枢,试图依仗姚弼“才兼文武”的才能为其所用。
姚弼势力的结成,终使后秦朝廷形成了党争之势。《晋书》载:
弼宠爱方隆,所欲施行,无不信纳。乃以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其党人,渐欲广树爪牙,弥缝其阙。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父子之际,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犹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并后匹嫡,未始不倾国乱家。广平公弼奸凶无状,潜有陵夺之志,陛下宠之不道,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徒,莫不鳞凑其侧。市巷讽议,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诚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兴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无废立之事,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去其左右,减其威权。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庙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兴默然。
姚弼权势的强盛引发“市巷讽议”,认为姚兴“欲有废立之志”,将以姚弼取代姚泓的太子之位。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要求姚兴对姚弼“去其左右”“减其威权”。梁喜在姚兴为太子时便是东宫中舍人,与姚兴“讲论经籍”,关系极为亲密。任谦是造秦功臣,在姚苌起事时为从事中郎,姚兴时既任侍中,又掌管部分宿卫禁兵。尹昭由吏部尚书转任京兆尹,与任谦等同掌宿卫禁兵。梁喜等人是参预决策的姚兴近臣,他们之所以针对姚弼发难,乃在于姚弼通过其党人参预了机要(“左右机要,皆其党人”),影响了后秦最高决策权的行使。然而面对梁喜等人的抗议,姚兴依然以沉默来回应。当姚兴临终前决定铲除姚弼势力时,“收其党殿中侍御史唐盛、孙玄等之”,可见姚兴很清楚姚弼党人在其身边左右机要,之所以容忍,或许是出于牵制身边近臣之意。姚弼的权势正是姚兴实现皇权独尊的工具。
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对后秦史的编撰主要依据姚和都《秦纪》。《隋书·经籍志二》记《秦纪》十卷,“魏左民尚书姚和都撰”。唐人编修《晋书》后秦史事时当参考过姚著。姚和都曾任姚泓太子右卫率,在姚兴临终前的权力空窗期,姚和都率领东宫兵参与镇压姚愔的政变。姚和都撰述后秦史事倾向于姚泓东宫一方当无太大疑问。《晋书》所载姚弼事件多叙述姚弼对太子的威胁,或是受到姚和都立场影响的缘故。
事实上,姚兴从未打算废易太子。当姚兴听闻梁喜等所言“欲有废立之志”时,他感到错愕。姚兴在扶植姚弼的同时,也在增强东宫的势力。“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树党东宫。弼恶之,每规陷害周。周抗志确然,不为之屈。兴嘉其守正,以周为中书监”。自晋武帝重构东宫建制后,太子詹事职如尚书令,并统辖东宫门下、中书、秘书诸机构。故姚泓东宫以太子詹事王周为党争的核心。在姚弼与东宫的争斗中,姚兴并未偏袒姚弼,反而擢升王周为中书监,将东宫的势力延伸到最高决策层,这正出于姚兴对东宫的保护。此外,姚兴为东宫配属了相当数量的禁兵,姚泓曾派遣东宫禁兵镇压冯翊人刘厥等数千人规模的叛乱。虽然自西晋开始太子卫率已是军事编制,但将东宫兵用于*并不多见。姚泓东宫的军事力量已经超出常规,这不能不说是姚兴有意为之。姚兴临终前命姚泓录尚书事,又遣敛曼嵬没收姚弼府第中的甲杖,这些举措确保了姚泓的顺利继位。
姚兴将姚泓、姚弼势力均视作皇权的延伸,这一权谋既旨在排斥宗室对皇权的觊觎,同时又牵制跻身决策层的异姓权臣。尽管姚兴将姚弼势力视作东宫能力不足时的补充,却在事实上造成了“二宫争构”的格局,从实践层面动摇了其所维护的嫡长子继承制乃至皇帝制度的根基。不仅如此,从后秦社稷角度来看,姚弼与东宫间的党争带来了朝廷的大分裂,已经危及到后秦政权的存亡。
在朝廷重臣方面,卫大将军姚显是姚弼的重要支持者。在决策机构中,侍中任谦、中书监王周、黄门郎段章支持东宫,姚弼兼任侍中,其党羽给事黄门侍郎尹冲、殿中侍御史唐盛与孙玄、侍御史廉桃生等“左右机要”。在尚书省中,太子姚泓录尚书事,姚弼为尚书令,右仆射梁喜、尚书王尚、尚书郎富允文支持太子,尚书姚沙弥为姚弼党羽。在宿卫将领中,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倾向于东宫,抚军将军姚绍则“每为弼羽翼”。在九卿之中,大司农窦温党附姚弼。在公府、幕府掾属中,司徒左长史王弼劝姚兴行太子废立之事,抚军东曹属姜虬则劝姚兴压制姚弼之党。在军事系统中,左将军姚文宗、镇军将军彭白狼为东宫支持者,姚弼则亲自担任过雍州、秦州等强藩主将,握强兵于外。东宫之党还有胡义周、夏侯稚、博士淳于岐等文士学者。东宫与姚弼之间的党争遍及从决策层到行政层的各个层级,从禁中到外朝的各个机构,从朝廷中枢到地方军镇的诸多场域。
从弘始十二年(410年)姚弼入朝为大将军兼尚书令、侍中,到弘始十八年(416年)姚兴驾崩,党争延续六年之久,这一时段也是后秦国力迅速衰弱的时期。政治生态的恶化是重要内因,造成这一结果的是姚兴维护君主制的方式出现了偏差。为了防范皇权觊觎者及牵制参预决策的异姓臣僚,姚兴采用培养东宫与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的独尊地位。但是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策略却降低了东宫的地位,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这便削弱了官僚君主制的制度权威,从而使姚兴所极力维护的君主制走向了崩溃。
三、滠头集团政治传统影响下宗室出镇制的制度运行
姚兴扶植姚弼的直接后果是开启了诸皇子间的夺嫡斗争。在姚兴第一次病危期间,除了姚弼招集数千人“潜谋为乱”之外,皇子姚裕遣使“密信诸藩,论弼逆状”,诸皇子纷纷响应。姚懿起兵于蒲坂,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阳,平西将军姚谌起兵于雍,后秦陷入了全面内战的危险之中。虽然姚懿等人起兵的理由是“广平公弼拥兵私第,不以忠于储宫”,打着维护储宫的旗号,但主要动机是不愿姚弼继位。在政治身份上,姚懿等皇子与姚弼同为公爵,自不甘心让姚弼夺嫡。在姚弼被免除尚书令,以将军、广平公归府第之后,姚懿、姚恢、姚谌等仍上表请求治罪姚弼,姚懿、姚洸、姚宣、姚谌又借来朝之际向姚兴当面提出将姚弼“委之有司,肃明刑宪”的要求。姚兴诸子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境地。
在姚兴第二次病危时,率先发动政变的是南阳公姚愔。其支持者是姚兴少子姚国儿、大将军尹元以及降秦的后凉皇帝吕隆,姚弼亲信尹冲也参预其间。因姚兴死讯传出,这场政变旨在阻止太子姚泓继位,故而姚愔、姚国儿转而与姚弼合作,可见姚兴诸子并没有遵奉东宫的意识。姚泓曾对姚兴言明他在诸子间的处境:“臣诚不肖,不能训谐于弟,致弼构造是非,仰惭天日。陛下若以臣为社稷之忧,除臣而国宁,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听臣守藩。”可以说,“不能训谐于弟”是姚泓的真实感受。
诸皇子相争在姚兴之世已是尽人皆知之事。《魏书》载:“兴还长安。有雀数万头,斗于兴庙,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余乃止。识者曰:‘今雀斗庙上,子孙当有争乱者乎?’”识者其实是通过附会长安宗庙的异象来讲述姚兴诸子夺嫡这一政治禁忌。姚泓继位后,赫连勃勃判断“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认为姚泓难以守住后秦的基业。首先发难的是姚泓之弟姚宣,占据“总三方之要”的邢望,准备自建“霸王之业”;其次是姚懿“举兵僭号,传檄州郡”;最后是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以车为方阵,自北雍州趣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姚泓继位后,既要应对赫连勃勃与东晋的进攻,又要应对诸弟、从弟的叛乱,《晋书》描述他的处境是“属倾扰之余,内难方殷,外御斯辍”;姚泓自己也说:“元子不能崇明德义,导率群下,致祸起萧墙,变自同气,既上负祖宗,亦无颜见诸父。懿始构逆灭亡,恢复拥众内叛,将若之何?”姚兴诸子相争是后秦衰亡的最主要原因。
姚兴诸子之所以不顾东宫储君之位而参与夺嫡斗争,有观念、制度层面的多重原因。在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中,领袖是以自下而上选贤任能的方式推选出来的。如姚苌建立后秦便是为“西州豪族”推选出来做盟主的,《晋书》记载当时的情形是:
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苌将距之,天水尹纬说苌曰:“今百六之数既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观沉溺而不拯救之。”
尹纬劝姚苌担任盟主有两个理由,一是姚苌具有“匡济时艰”的能力;二是豪杰进行了群议,推选姚苌具有程序合法性,姚苌不应推辞。在这一传统中,宗室中有才能者皆有成为君主的可能性,这是姚兴扶植皇子防范觊觎者的原因。当姚兴诸子成长起来后,他们也在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中找到了打破嫡长子继承制的依据。易言之,姚兴一直试图以君主制打破滠头集团的盟主推选制,但是政治习俗的影响是长远的,它一直影响着后秦的君主制运行。当姚兴以人治的手段扶植姚弼以增强皇权时,君主制的稳定性便被动摇了。嫡长子继承制既然面临失效的风险,传统政治习俗将再次发挥作用。参军韦宗动员姚宣自立的说辞便是“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强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难未可弭也。殿下居维城之任,宜深虑之。邢望地形险固,总三方之要,若能据之,虚心抚御,非但克固维城,亦霸王之业”,即认为姚泓不具备领导后秦度过“本朝之难”的能力,“居维城之任”的姚宣当建立“霸王之业”。韦宗的说理正与尹纬劝说姚苌的逻辑相同。
后秦是南安姚氏与滠头集团、西州豪族建立的联合政权,南安姚氏以第一家族的身份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为了维护家族利益,采用的是西晋以宗室出镇的制度。早在姚苌时期,便以皇弟姚硕德、姚绪、姚靖领兵出镇。在姚兴统治前期,曾以皇弟姚平为主将发动柴壁之战,以姚显为诸军节度征伐秃发傉檀,以姚绍统洛东之兵,以姚嵩镇秦州;后期则改以子侄出镇,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姚泓时期。姚兴子姚懿为征东将军、并州牧,镇于蒲坂;姚洸为征南将军、豫州牧,镇于洛阳;姚谌为平西将军,镇于雍城;姚宣、姚逵先后镇于杏城;姚璞为镇东将军;姚裕为车骑将军,镇于池阳;姚兴侄姚恢为征北将军,镇于安定。
应该说,宗室出镇制度对于后秦政权的巩固具有积极意义。赫连勃勃曾说:“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直至后秦灭亡,赫连勃勃尚未完全攻陷军镇密集的岭北地区。然而以宗室出镇拱卫皇权的要害在于朝廷必须强盛,一旦朝廷虚弱或君主权威被削弱,宗室出镇制度将会引发全局性的混乱,西晋八王之乱如此,侯景之乱后萧梁诸王混战如此,姚泓时期的诸弟之乱亦是如此。推究其因,这与宗室的双重性有关,他们既是皇权的拱卫者,同时也是皇权的竞争者。
更为重要的是,因南安姚氏凌驾于滠头集团、西州豪族以及其他家族之上,当宗室出镇时,这些异姓家族子弟常出任幕府掾属,左右军镇的决策。易言之,出镇宗室往往代言某些异姓家族的政治诉求,他们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异姓家族之间的竞争。如姚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姚兴“责丕以无匡辅之益”,可见权丕对姚宣负有“匡辅”之责。权丕出于滠头集团的核心家族略阳权氏;姚愔身边则有天水尹氏及后凉皇族吕氏;煽动姚宣自立的参军韦宗,或出自京兆韦氏。影响姚洸决策的主簿阎恢,或出自天水阎氏;煽动姚懿“僭号”的是司马孙畅;响应姚恢的是天水姜纪。可见宗室诸镇纷纭复杂的政治表现,实是诸多异姓家族的参政反映。可以说,因异姓家族参预幕府决策而导致出镇宗室间的利益分化,使得原本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反而培育出朝廷潜在的分离势力。姚兴在世尚可调动诸镇势力以应对外部危机,至姚泓时只能依靠中央禁兵。统辖禁兵的姚绍、姚赞既要应对刘裕的北伐,又要应对接连发生的姚宣、姚懿、姚恢的叛乱,最后使姚绍忿恚发病,呕血而死。缺乏军事领袖的后秦再难抵抗刘裕的北伐,姚泓、姚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投降东晋。姚泓继位不到两年,后秦便灭亡了。
四、结论
与一般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建政前后才开始“汉化”不同,后秦统治集团(滠头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因此皇室南安姚氏并不存在“汉化”的问题,他们的中华认同是原生形态的。南安姚氏认为家族血缘源自虞舜,“世为羌长”的权力身份缘于夏禹的册封,南安姚氏的这种身份认同亦为周边族群及政权所认可。姚兴按照华夏政治传统推行任贤、睦亲、明赏罚等举措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华认同成为后秦的国是。正因后秦以华夏正朔自居,所以姚兴的政治理想是再造大一统。
在建政后,后秦的“汉化”主要指在国家制度上采用汉魏晋王朝的官僚君主制。如所周知,秦汉以来的官僚君主制以中央集权为制度精神,旨在建立并维护皇权的一元化权威,由此一来,姚苌、姚兴推行的官僚君主制便与滠头集团共享统治权的政治传统发生冲突。姚兴采用培养东宫与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的独尊地位,但是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策略却降低了东宫的地位,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这便削弱了官僚君主制的制度权威,反而使之走向崩溃。
后秦是南安姚氏与滠头集团、西州豪族建立的联合政权,南安姚氏以第一家族的身份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后秦采用源自西晋的宗室出镇制度。由于宗室具有皇权的拱卫者与竞争者的双重性质,一旦朝廷虚弱或君主权威被削弱,宗室出镇制度将会引发全局的混乱。加以统治阶层中的异姓家族参预幕府决策,进一步加剧出镇宗室间的利益分化。由此一来,宗室出镇制度培育出朝廷潜在的分离势力。姚兴为独尊皇权而施行扶植姚弼的权谋,客观上造成了姚泓弱势君主的地位,宗室出镇制度的负面作用在其继位后加剧显现,最终导致后秦从内部瓦解。
如果从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角度来看,后秦的衰亡缘于官僚君主制、嫡长子继承制、宗室出镇制与统治集团固有的政治习俗之间的冲突。然而南安姚氏在建政之前便已与汉人士族的文化面貌无异,统治集团中的羌人部族也已经与其他部族及汉人豪门完成了政治上的混融,因而虽承认但亦不能过度夸大统治集团政治习俗与官僚君主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南安姚氏为第一家族,联合滠头集团、西州豪族建立政权的形式,同司马氏与门阀士族建立联合统治的两晋王朝模式相同。若以两晋王朝为参照,后秦的制度选择与其政治结构具有匹配性。与其说后秦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所致,不如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性所致。无论是嫡长子继承制还是宗室出镇制,都不能完全有效解决第一家族内部、第一家族与参政家族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西晋晋惠帝的皇权衰弱导致八王之乱,侯景之乱中萧梁政治中枢的瓦解而导致宗王混战,莫不根源于官僚君主制与门阀政治之间的矛盾。姚兴统治后期的政治危机与姚泓时期的宗室之乱亦属同类性质。
后秦的盛衰表明,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未必全然缘于族群政治,更有可能是缘于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性的问题。
【注】文章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责编:李静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头条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