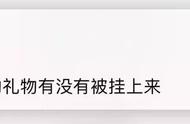之后我们不再提“小梅”的话题,他们开始讲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有的让人羡慕,比如春立这几年开半挂车,发了财见了世面。又或者,涛子这几年路不顺,干什么赔什么,最后媳妇也跟别人跑了。等等等。我也把我的遭遇说了,我这几年不上班后,就开始鬻文为生,不料写了几部颇受欢迎的小说,竟一炮而红,名利双收。大家都对我称赞,说我是文化人。其实我则很羡慕他们走南闯北,不羁的生活。
晚上七点,我们各自回家,同时约好了明天再聚。我在村里面的街道上独自行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在我背后喊我“叔叔好”,我回头看,居然是小梅的女儿。我内心一热,竟不自由主地从兜子里掏出了一百块钱给她当压岁钱。但她不要。她对我笑着摆摆手,说:
“叔叔,我妈妈说了,不能要别人的钱。”
说罢,她欢快地跑开了,留我在原地,五味杂陈。
说实话,我很想问问她,*妈好不好?可是我明知道自己办不到,这就像我明知道自己写的破烂文章没有一点“意义”一样。我看着那女孩离去,就像看着最后一丝希望破灭,我明明能够挽回,却无能为力。

我回到家后,把沮丧的心情隐藏,毕竟跨年之夜,合家欢乐,才是最重要的。
但我细心的妻子还是发现了我的异常,她抽空问我:
“老公,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我笑说“没有”,对她解释喝了点,有点头晕。
“那就不要喝酒了。”我妻子关心地对我说。
但晚上九点,春立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让我去他家喝茶,我说有点累了,不想去了,春立就说:
“峰哥,你一定要来,来了给你个惊喜,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问他什么事,他只是笑,随后挂断了电话。
我不相信有什么“惊喜”会让我“后悔”,但还是感觉到这个“惊喜”也许和“小梅”有关。如果果真是她在的话,我没有去,岂不真的“后悔终生”?

但我又感觉她在,似乎不太可能。我们一伙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虽说已过了“避嫌”的年龄,但我们还不至于在“辞岁夜”,把多年不见的女同学请来一起辞岁。
可是我的内心又很渴望我的猜测是错的,我虽然明白我即使见到小梅,也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这就像我见到卖给别人的汽车,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油然而生罢了。——也许这比喻不恰当,不过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了。
我还是给父母、媳妇说了一声,去了春立家。
在春立家,我并没有见到小梅——就连她女儿也没有见到——我想一定是春立怕我不来,故意“骗”我的。但当时人很多,我又不便当面问他,也就和他们有说有笑,抽烟喝茶聊天。
大概晚上十点左右,我借口回家,春立居然没有挽留我。他送我到门口,说了句“明天有空歇着”,就分别了。我在春立家门口还没有走出五百米,就遇到了小梅的女儿。
她扎着一条小辫,穿着过节的新衣服:粉色的羽绒服,黑色的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她显然是在墙角等着我。我就笑着问她:
“小美女,你找我有事吗?”

她没有笑。她告诉我她叫“齐蕾”,我又说:
“齐蕾,你找我有事吗?”
这时她才笑了,但她的笑容很浅,就像涟漪即将消失的水纹。
“我想让你带我去唱歌。”她说。
我愣住了。她让我带她去“唱歌”,我想,我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去唱歌,这合适吗?
再说,我和她不熟,她放心我吗?另外,在这辞旧迎新之夜,合家团聚,附近还有营业的歌厅吗?
齐蕾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说:
“叔叔,马路上有营业的歌厅。”
这么一来,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了。但我还是说:
“*妈让你去那种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