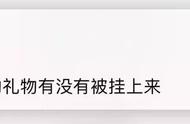但我没有那么做,我只是对她说:
“小梅,你能再给我唱一首《呢喃》吗?”
小梅双眼噙着泪,带着哭腔的给我唱完了那首歌曲。从那夜之后,我们再没有见面。我不知道小梅是不是因为赌气不见我,反正我是为了她好,而不去找她。
接下来没多久,小梅就和隔壁村姓王的一个青年结了婚。婚后,他们一起去了S市,在当时很出名的一家叫“往事”的歌厅打工。
我当时很难受,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于是我也去了S市打工。我当时想,我虽然见不到小梅了,但我就在她的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她也一定会感觉到我的存在。
也许小梅是在结婚的第二年有了齐蕾,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能确定的是,小梅自来到歌厅上班后,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她总是对别人谦虚的说:
“不好意思,我不会唱歌。”

我知道,她不过是把最好的歌声留给了我。
小梅在结婚后的三五年(最多不超过六年),也许是快乐的。她老公爱她——她毕竟长得很漂亮——但是等她老公有了钱,他摸透了歌厅的门道,自己开了歌厅后,他就变了。他开始对小梅不理不睬,很快发展到恶语相向。等到她老公有了个南方相好(听说那女人大他七八岁),他就彻底对小梅不理不睬了。
两夫妻天天吵架,也许还能凑合着过。但要两口子不闻不问了,这婚姻就彻底完了。他们离婚了。
孩子归小梅,这一年她三十一岁。而我于这一年当了爸爸,事业蒸蒸日上。我听说这个消息后,曾设法找过她,但结果都是枉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故意不见我,还是我找的时机、地方不对,总之这一遗憾一直蹉跎了下去。她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闪即逝。
而今我见到了她女儿,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缘分到了,她要和我见面呢?为此我辗转反侧,一宿无眠,直到凌晨,该起床给长辈们拜年了,我才略有睡意。但还是起床,穿戴一新,和妻子走出了家门。
现在的新年,除了拜年一项没有丢失(起码我们这里没有),其余的大部分都失去了。这也许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我们左右不了。但空发几句唠叨,我们是可以做主的。

上午八点,春立又来找我了。新年的第一天总是高兴的,人高兴似乎就该有酒,春立让我去他家喝酒。我说不如在我家。就把剩下的两箱酒搬来,酒菜都现成,我们开始新年的第一次聚餐。
酒意阑珊,春立突然小声问我:
“峰哥,昨夜的歌唱的可好?”
我一怔,无话可说。我想,他怎么知道的?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但我没有说出心里话,只是对他笑了笑。等到下午大部分人都去牌桌上玩牌了,我才把春立叫到一边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春立深吸了一口烟,轻笑一声,说:
“这都是小梅安排的。”
我说:“那她为什么不去?”
春立低下头,右脚在地上来回踩动,欲言又止,最后他说:
“我也不知道,她也许有自己的苦衷吧!”

顿了一下,他又说: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你也不是不知道她家在哪。”
是啊,我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
十五年前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作为一个朋友(或者同学)去看她,又有何妨呢?
此时我就下定了去小梅家看看她的想法。但我并没有对春立说出我的想法,我拉他坐回牌桌,重新欢笑。直到人群散去,天也蒙蒙黑了,我随便吃了口饭,对家人支应了一声,就信步走出了家门。
我依着记忆,穿街走巷,十五分钟后就来到了小梅的家门前。
她家门开着,能够看到门内微弱的红烛光。但我并没有直走进去,我在门口占了有五分钟左右,才壮起胆子往里走。
小梅的家和十五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触目而及,难免让我生出一股对往事的惆怅。等我走进了堂屋内,却没有见到她,单是见到了她女儿,齐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