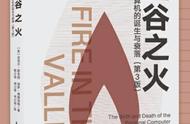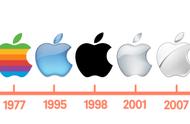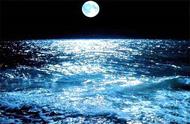有苹果员工称,苹果的设计团队正在遭遇“人才流失”的困扰,从Apple Watch发布之后,艾维的小团队已经有至少15名成员离开,很多曾在艾维手下工作的资深设计师都去了他的新公司LoveFrom。
这样的人员流动是很少见的,艾维离职前曾说过,在过去的15年里,只有两名设计团队成员离开了苹果,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因为健康原因才离职的。
艾维的继任者汉基负责监督苹果的工业设计团队,但实际上,她仅仅在这一职位上任职了三年。
目前在苹果工业设计团队中,仅存的两位老将,一位是在苹果工作了26年的理查德·豪沃思(Richard Howarth),另一位是在苹果工作了30多年的巴特·安德烈(Bart Andre),但这两位都没有接替汉基的意愿。
虽然苹果曾考虑任命软件设计主管戴伊(Dye)负责硬件设计,但老员工们认为,这一举动将“激怒”硬件设计师们。
有苹果内部老员工告诉媒体,他们认为从别的公司引进人才是“团队的死亡(death of the team)”,苹果现在需要在内部找人,但苹果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接班人培养计划”,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艾维曾经透露,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关注的重心是运营而不是设计。
可以说,苹果的“灵魂”设计部门的元老级人物陆续散场,或许只是一个表象,在业绩增长遇到瓶颈、产品创新乏力之际,苹果源自内部的深层次调整或许已成必然。
但无论如何,对于苹果来说,创新离不开人才,而不论是面对MR头显所指向的元宇宙,还是面对电动汽车的新方向,人才难寻的问题将始终是苹果当下面临的突出挑战。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46岁,已经超越了绝大部分科技巨头的“年龄”,苹果这些征战了二十年、三十年的员工,最终交棒给“新鲜血液”,或许对于苹果来说也是一次由内而外的革新。
或许想成为一家“百年老店”,这是苹果必须要经历的。
正如微软、英特尔这样的科技巨头,也在近几年迎来了CEO级别的人事更迭,而如今新的业务在这些公司中都在旺盛生长着,带来了新的变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苹果能否积极面对变化,找到解法,至关重要。
四、供应链结构性调整之忧:“铁打的果链”神话能否延续?
接下来,我想谈的苹果中年之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苹果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
在科技行业中,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流水的厂商,铁打的果链”。诚然,在苹果“日不落”供应链帝国依旧稳固的今天,这句话并没有问题。
但在庞大帝国之下,危机与变革也在悄然酝酿着。
苹果对于中国大陆供应商的依赖问题,如今正成为外媒讨论热度最高的“苹果话题”之一。
虽然近年来,苹果不断把产品的最终组装环节转移至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但实际上苹果在制造业方面依然极其依赖中国大陆。
苹果iPhone、Mac电脑、AirPods、Apple Watch、iPad等绝大多数产品的“FATP(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都要在中国大陆进行,另外郭明錤也提到,苹果的新产品导入(NPI)流程也几乎都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
可以说,虽然富士康是一家中国台湾公司,但它的主要生产工厂都位于中国大陆,比如郑州的富士康工厂。

富士康郑州厂区一角
苹果为什么离不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制造业员工的平均工资远超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劳动力成本并不是主要优势,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实际上,像富士康这样规模庞大的代工厂,其核心优势在于灵活性。富士康郑州厂区的人数曾一度超过30万人,相当于一座小城市。工人都工作、生活在园区内部,园区里各类设施一应俱全。
这样就使得组装生产的队伍可以24小时待命,随时被灵活调拨。比如初代iPhone在上市前几周,乔布斯突然决定将塑料屏幕换成玻璃屏幕,因为他发现塑料屏幕在裤兜里会被钥匙刮花。几周后,8000多名工人在产线上轮班工作,几天之内,让改版后的iPhone出货订单超过了1万部。
这样的大规模、集中、灵活的生产能力,目前其他国家还很难具备。
站在中国大陆制造业发展的角度,苹果是功不可没的,其带动的就业、其对于生产技术提升的促进效应,都是有目共睹的,立讯精密、歌尔股份、京东方、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供应链企业,都在加入果链后实现了更快速的成长。
而站在苹果的角度,对于中国大陆的过度依赖,在近年来显露出了一些弊端,最明显的莫过于新冠疫情和大国政治博弈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
疫情造成的停工、贸易战造成的物流运输成本飙升,都成为苹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时期,贸易紧张局势导致苹果的产品也被纳入额外征收关税之列;疫情爆发初期,苹果的iPhone SE和iPhone 12都因为工厂停工、产能不足而延迟发布。
2021年的缺芯潮虽然没有影响苹果iPhone 13系列的发布,在苹果年末财季的财报电话会上,CFO马埃斯特里称,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可能会给苹果造成40到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6到532亿元)的损失。
他还特别提到了当时上海疫情给附近工厂带来的影响。
近期郑州疫情对于富士康工厂生产的影响,已经波及到1500万到2000万部iPhone 14 Pro的生产,订单削减幅度在20%左右。
苹果供应链布局的分散,已经成为必然,并在加速推进中。
苹果持续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大陆,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甚至连中国台湾地区,苹果都认为“不够放心”。
最明显的莫过于台积电的动作,台积电近年来不停地在海外扩张建厂,其中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被议论的程度最高,主要因为它可能会率先投产台积电更先进的芯片工艺制程,比如3nm。
苹果也公布了后续将从“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在建工厂开始为其设备采购芯片”的消息,显然,这说的就是台积电。
此外台积电还在美国东岸的维吉尼亚州建立第三座位于美国本土的芯片工厂,在欧洲,台积电正在与德国政府讨论建厂的问题。
当然,芯片生产的转移绝非一日之功,一座芯片工厂从规划、建厂、投产,到最终产品通过量产测试、真正大规模生产落地,都是以年为单位计算时间的。
这其中的变数也将成为苹果和台积电要共同面临的挑战。建厂的资金问题、美国的补贴政策能否及时落实到位、人才团队的建设培养、供应链链条的打通、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甚至台积电自己能否解决现在工艺研发中遇到的种种技术难题,都会成为挑战。
此外,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相比高技术壁垒环节,看起来似乎要容易一些,但事实却也是困难重重。
比如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基础方面十分薄弱,产业链实则极为“畸形”,在重化工业方面都较为缺乏,而重化工业又是制造业的基石。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印度、越南真的是承担了最“纯粹”的组装工作,他们需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自身只承担加工组装任务,产品出口到美国。
正如前文所说,苹果核心产品的大规模量产关键环节仍然离不开中国大陆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