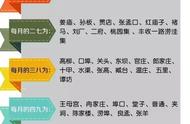到早上8点钟,当都市白领起床准备上班时,寿光的蔬菜交易已在短短四五个小时内交易近万吨,也就是说,这样载重25吨的大货车装满了400车!成交的蔬菜品种达200多种。

卖菜其实是一门看天吃饭的生意,每天的菜价也不一样,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交易过程中不允许现金交易,都是通过刷卡实现结算。刷卡完成后,工作人员会给一张交易单,上面有品名、净重、单价等信息,这样一笔交易就完成了。
当蔬菜交易都完成后,到大约9点钟,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就会公布一个蔬菜价格指数,这是从园区200多个蔬菜品种中采集成交价格、交易量、交易额等数据计算出来的,反映的是蔬菜价格变化趋势。
就像股市的大盘指数一样,寿光蔬菜指数不光能让菜农、批发商看到每天的菜价和季度、年度走势,甚至为国家发布有关蔬菜建设政策的相关信息提供着参考依据。因此,寿光蔬菜交易号称“全国生产,寿光定价”,这里每年的交易量达到400万吨,销往北京、上海等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全国蔬菜市场就有了定价权。

就这样,寿光把农业这张牌打出了高水平!
2
百菜之王
寿光蔬菜种植变得如此“硬核”,并不是偶然。
1997年10月17日,最后一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副食品——大白菜,供销正式全面放开。这个长期实行特殊供应方式的“百菜之王”,结束了它几十年来对北方人冬季餐桌的“统治”,开始了与其他红、白、绿、黄、紫等蔬菜一同“竞争上岗”的日子。

图为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排队买冬储大白菜
百姓餐桌上的这一悄然变化,除了因交通日益便利得以“南菜北运”外,还与位于山东中北部,莱州湾畔一个小县城密不可分,这个小县城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颗“大白菜”而改变。
时光回溯20年,回到决定中国国运的1978年。
在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年代,距离小岗村600多公里外的寿光三元朱村,15名党员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推举王乐义担任村党支部*。其实,这个选择有些许无奈。因为37岁的王乐义刚罹患癌症动完手术,家人极力反对他担任村支书,但三元朱村的村民似乎没有更好地选择。
那时的三元朱村被三个光秃秃的埠子岭环绕,土差水少,粮食不收,蔬菜不长,过怕了苦日子的乡亲们期盼着这位“能人”带领全村吃饱饭。
当上村支书的王乐义,拖着病躯四处奔走、外出考察,确定了“东岭苹果西岭桃,南岭山楂带葡萄”的规划,他带领干部群众苦战10个严寒酷暑,将埠子岭变成了“花果山”。
1986年,全村年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几十元增长到1200元,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王乐义在村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然而,这离着他心目中的目标还差得远,但怎么突破还一时找不到门路。
改革开放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当初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推广,除了18位农民的敢为人先,也离不开省委*万里的推动以及中央的认可。显然,对于王乐义和三元朱村来说,要想更上一层楼,除了他有能力、有想法,乡亲们吃苦能干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推手。很快,决定着三元朱村乃至寿光未来命运的机缘出现了。
这一年,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
自古以来,寿光南部的农民就有种植蔬菜的传统,除了地肥水沃的自然条件外,也有历史基因的传承——世界第一部农学巨著《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诞生于此,他遗留的文化遗产滋养了这片土地千百年。
然而,长期以来寿光蔬菜种植品种都比较单一。就在王伯祥担任副*的1983年,寿光南部农民种植的近2500万公斤的大白菜卖不出去,而寿光就紧邻30万人的胜利油田,这是一个庞大而高端的消费人群,由于产销体制限制,只能眼看着白菜烂在地里。
于是,农民把菜摆到公路边卖给过路的石油工人,一个蔬菜市场自发形成了,但由于秩序换乱、干扰交通,周围的老百姓颇有微词。第二年,在王伯祥推动下,一个占地20亩的九巷村蔬菜批发市场建设完成,菜农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将蔬菜卖往附近最大的消费市场——胜利油田。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因势利导建立起来的菜市场,居然成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轫地。正是这个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撬开的缺口,源源不断地迸发出助推寿光蔬菜产业向前发展的市场动力。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各项改革依次展开,国家先后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实施“菜篮子”工程并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政策,市场经济的洪流已不可阻挡。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88年春节。
常年在外做蔬菜生意的堂弟回来给王乐义带了两斤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多年摸爬滚打练就的敏锐嗅觉让他意识到,期盼了许久的突破点找到了。
后来的故事耳熟能详,在王伯祥支持下,王乐义带头顶着政治风险砍掉玉米,17个党员带头建起大棚。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第二年,全村大棚发展到144个,再后来遍布整个寿光。
2018年,寿光蔬菜大棚面积发展到60多万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27元,高出全国平均6010元,而40年前,这个数字低于全国平均数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