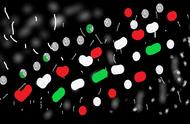《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大哥你写小说,写它有啥用?”
关注市井生活以外,谈波的小说还常出现情色与暴力元素,“这些东西吸引人,能让读者参与进来,毕竟人愿意看一些有意思的事。但一个作家,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些元素中陷入重复,实际上,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没太多新意了,只不过变了个概念、换了套词汇。
我觉得好小说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即使把那些新词扒去,当你看完,还是有种被激活的感觉”。但有段时间,谈波的这种感觉消逝了。那是他父母亲离世的时候,面对生死,文学似乎没有任何效用,“他们病危时,原本在背后支撑自己的那些文字,变得不可靠了,很无力”。

《长假漫漫》剧照。
过去,文学像他的堡垒,“别人打麻将我也打,你们能输,我更能输,别人做生意我也做,做不成我还能退回来。我有旁人不具备的东西——文学”。谈波寻思,这辈子就喜欢这么个玩意儿,按理说,平日对它那么好、付出那么多,作为最好的朋友,在最紧要的关头,它该站出来,结果它现在跑哪去了呢?还不顶心灵鸡汤好使。
摇滚歌手梁龙那句致命的“魔力一问”会时不时浮现在脑海,谈波把“玩摇滚”换成了“写小说”:“大哥你写小说,写它有啥用?”艺术是不是真的只是“游戏说”,在吃饱喝足、无忧无虑的状态下才能有?如果它不能帮助你解决生死,那还有什么值得你投入一生去玩呢?任凭怎么想,谈波都无法说服自己,他怎么回答都不对,都不完善。
随着时间推移,悲伤减退,谈波的“逃兵伙伴”回来了。谈波冷不丁惊出一身冷汗,“玩了几十年的朋友,差点儿给忘干净了”。那段时间谈波心生怀疑:文学和自己究竟是什么关系?后来他很快释然,是自己强人所难了,想把宗教、哲学、医学都整不明白的问题让文学解决。
文学可能只是你的一个好哥们儿,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他的解释是:“好比我跟他上街,我跟人拼起命来了,回头一看,他跑了,他没帮我,但过两天,他又折回来,一块吃吃烧烤,一块玩玩,安慰安慰我。好像也挺好。文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当不成生死朋友,酒肉朋友还是够格的。”

《山村犹有读书声》剧照。
在这点上,曹寇评价谈波:“文学于他,完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等同于呼吸空气,但也到此为止,而绝非获取名利的器具。这几乎是一种修行。”谈波常扪心自问,究竟在为什么而写。
他说:“梁龙那个致命一问太有魔力了,无论怎么回答都不对,都会遭到这个问题本身以及你给出的答案本身的反诘。即使这样,还得不断追问下去,问题生问题,永无穷尽,永无答案,但这个自问自答的过程会清除很多障碍,会让你知道不要写什么、不要那样去写,以及大约应该写成什么样。”卡夫卡讲,好书是“一把能击破心中冰河的利斧”。

《城堡》(1997)剧照。
谈波很认同,基于此,他信赖那些“写身边发生的事儿”的作家,他说:“生活本身已经很荒诞、很虚无了,如果一味只去强调这样的感觉,一是没劲儿,二是实际上还是对西方的某种模仿。
他们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创伤与我们不同,所以不管他们多么有名、多么时髦,我还是写跟自己生命体验相关的东西,写那些能够激活、唤醒感受力的东西,不被那些匆忙制造出来的概念、名词所动,更不受它们的约束限制。”
现在,谈波过着标准的老年生活,爬山、溜达,没事儿看看书、刷刷手机。与此同时,好奇心很重的他又总有一些新的念头冒出,尽管有时这些想法会在第二天被消灭。谈波说:“没写的时候,挺‘狂妄’,想象着它会一定多么多么好,真叫我写,就写不出来,但是咱不怕,今天写不出来,可以明天写,实在不行就后天。实际上,能有这种感觉就不错,我每一天都沉浸在这种‘我将要写出好作品’的白日梦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