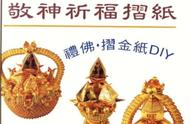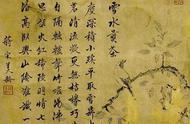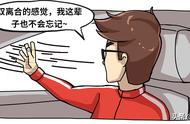舍利供奉,是佛教信仰中供养礼仪的重要组成,今天所能见到的实例,多发现于寺塔地宫。舍利容器使用最多的便是金银器,隋唐五代和辽都是如此。宋代舍利崇拜依然兴盛,并且它同译经和伴随译经而以朝廷为主导的中印佛教交流联系在一起,而瘗藏舍利的举措不少都有皇家背景,乃至帝王躬亲其事。宋代士人也不乏崇信三宝行此以祈福佑者。苏轼即以苏辙得自寺僧所赠的三颗舍利施入济南长清真相院塔地宫,并舍金一两、银六两以为奉安舍利的金棺银椁。当然舍利瘗埋更多的是民间行为,因此也促进了佛教的平民化、世俗化。涅槃、举哀、焚棺成为金棺银椁普遍取用的纹样,又或以小型涅槃像置于其内(图一),又制作缩微佛殿安放造像,总之,表现形式更加具象化,佛教艺术中的金银器制作也因此生出新的特色。

与此前相同,金银舍利容器的主要品类为金瓶银瓶,金棺银椁,银塔、鎏金银塔,还有银殿。日僧成寻记熙宁五年(1072年)他在开封礼拜启圣禅院佛牙堂所见云:届时“敕使自开封,有敕封。简之,内有七宝塔,高八尺许,塔内有纯金筥,方一尺许,以锦绫色色缝物绢等十重裹之,筥内有纯金小厨子,云云,以赤锦三重裹之。四面立白琉璃,内见撤银莲花座,上置佛牙”,可见当日舍利供养之大概。纯金筥,应即金函,宋人或称之曰匣。纯金小厨子,似即金棺。考古发现的寺塔地宫之舍利安放,也大致如此。
一 舍利瓶


宋代舍利瓶以琉璃器和瓷器为多,金银器相对少。出自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的金舍利瓶,通高12.65厘米,瓜棱式,又仿净瓶的式样在长颈处加装一个圆片,瓶盖中空,盖顶是莲花座上的合十弟子(图二)。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一件金舍利瓶,外罩鎏金银龛,下方六角形托座,底端六个如意足,托座上方圆盘里的金舍利瓶与盘焊接在一起,覆钵式鎏金银龛开一个尖拱门,此外又有三个剑环式开光,光内錾凤凰与花,光外錾折枝,龛顶打作莲花一大朵。通高10.3厘米(图三:1)。舍利瓶外壁錾铭两行,曰“冲汉舍瓶”“道清舍金”。盘缘铭曰:“弟子胡用囗勾当僧庆恩可观景祐二年乙亥岁十二月日造。”同出另一件金舍利瓶,通高7.8厘米,重63克。瓶身与瓶颈分别打制成形,然后接焊,荷叶为盖,荷茎绕作捉手。腹开三个圆光,光内是高高低低的出水莲花和莲蓬,光外鱼子地上满錾卷草(图三:2)。据同出的《建塔助缘施主名位》墨书写本,后件金舍利瓶与鎏金银盂、鎏金银请舍利箸,均为北宋庆历年间法明院比丘利和劝缘制造。“请舍利箸”,顶端仿塔刹之式以仰覆莲花托宝瓶,通长14.7厘米(图四),当是用来夹取和贮存舍利,只是这里仅存一支。舍利瓶一般口径很小,“请舍利”之际,用箸自然合宜,并且尤见虔敬。不过很多舍利十分细小,实在难以用箸来夹取。如此,必有其他工具。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出土一柄“千年万载”铭小银匙,通长9厘米(图五),系与舍利银瓶放在一起,或推测它是用来“请舍利”的。又有出自南京长干寺遗址的一件被称作“香匙”的银鎏金器具,高1.9、长11厘米,平底,一侧做出管状流,其余三面口沿各有如意耳,与流相对的耳上錾折枝牡丹,此外两耳錾折枝花叶。内底一个手持放光宝葫芦的仙人,脚前一只小鹿和他回首对望。上方几朵流云,两边几枝花叶(图六)。以此器的形制论,当非匙属。这一类平底容器,当日习称盂子。此盂有耳,便于持;有流,便于注。不妨设想,以小匙“请舍利”入盂,持盂将舍利自长流“请”入舍利瓶,应该是合乎情理的。首都博物馆藏辽天庆七年(1117年)石经寺释迦舍利塔记碑,记文说到功德主在建造砖塔之际,“特命良工造银塔一座,高一尺五寸,金释迦如来,银钵、盂子、匙、箸,金净瓶内有舍利,在石匣中”,以下别举其余供具,而石匣中的诸般物事,即盂子和匙、箸,当与“请舍利”的举措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