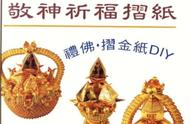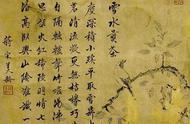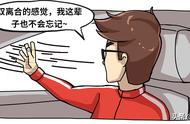前举邓州福胜寺塔地宫出土金棺上的涅槃图情节比较简单:佛陀右卧于床,身边六个悲泣的弟子。出自兖州兴隆塔地宫的鎏金银棺,则是纹样最为繁复的一例。它原是为供奉于阗国僧法藏自西天取得的“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而制。法藏开宝三年(970年)以于阗白玉三百九十斤,又细马三匹进奉,因得帘前赐紫及光正大师号。之后法藏相继往峨眉山、五台山、泗州等地巡回供奉舍利,以“在兖州住寄岁久,恋皇帝化风,不归本处”,然而起塔奉安佛舍利,则是他始终的心愿。本人未能实现,乃托付小师怀秀,怀秀依然未能完成,遂付与当寺大悲院主讲经僧法语,终于在嘉祐八年(1063年)建塔于寺。鎏金银棺以片材打制而成,其表鎏金。四周原有钩栏,龟背纹华版,望柱顶端为化生童子,但大部已破损。银棺略呈梯形,前高后低,前宽后窄,通长43厘米,棺头处高29、棺尾处高12.2厘米。棺两侧均为涅槃图,内容布局一致,人物设置稍有变化。左侧一幅,卧于矮榻的佛陀是向右侧身的“狮子卧”,右侧的一幅,佛陀却是向左侧身的“爱欲卧”。似可认为这是设计者为了两个画面构图之对称,并且如此安排之下,两幅图里,佛陀的头向是一致的,亦即佛足均在棺尾方向。左侧之幅,佛陀身后一排六人或合十悲哭,或捶胸嚎啕,或以手拭泪,是六个弟子。头前一人为最后的供养者纯陀,又一人左手托钵,右手前伸竖起二指,是以钵中之水洒向阿难,当是唤醒和劝止阿难的阿那律,他的手指处便是哭昏倒地的阿难。阿那律上方一人右手持磬锤,左手是莲花托上的圆磬,为最后赶到的迦叶。又执金刚神亦即金刚力士二,其一手持金刚杵,其一坐地举拳、金刚杵脱手横卧其侧若不胜悲痛。榻边抚足而泣者是佛母摩耶夫人。画面前方为普贤骑象,画面后方是四头六臂、颈系骷髅、两臂托日月的阿修罗。整个画面皆打作鱼子地,上方余白处满布缠枝花卉和两朵祥云,此外均为金铤、银锭、象牙、犀角、宝珠、螺、贝等杂宝(图一一:1)。右侧之幅,前方为文殊骑狮。阿难上方的二人为异域装束,应是表现前来举哀的四夷国主(图一一:2)。银棺前挡仿若尖拱券门,下方版门两扇,锥点卷草纹的地子上各有浮沤钉十二排,一对衔环铺首,环内贯锁。门两侧各一身合掌立在莲花座上的供养菩萨。上方如意式棺头顶端一佛二菩萨,火焰背光上方稍残,圆形身光的内里一圈錾毬路纹,外环一圈锥点卷草,莲座下方六个龙头,三龙左向,三龙右向,各个口中含珠,两边莲花座上是手捧果盘的供养菩萨。其下又是两只翼龙对捧宝珠,余白遍錾折枝花,上缘一侧略有残损,另一侧向后翻折,但仍可见上面的纹样是迦陵频伽。式如云朵的垂饰如同建筑构件的“雕云垂鱼”,底端升起一枝莲花,花心立着合掌菩萨,两侧对称的云朵中分别錾出日和月(图一一:4)。银棺后挡是山石座上的菩萨,两侧为护法天王,头光上方是牡丹对凤,山石座的两边各一身供养菩萨,一个盘里盛宝珠,一个盘里盛花朵。或认为前挡是表现佛陀入灭前于拘尸那罗城跋提河畔娑罗双树间为众弟子、诸天神最后说法;后挡是表现即将下生成佛的弥勒菩萨。盝顶式棺盖,顶面四个菱花式开光,两边光内为颠倒飞舞的一对伽陵频迦,中间两个,一为团龙图,一为三教会棋图。两坡各有六个菱花式开光,光内均为一佛二菩萨。

江苏句容崇明大圣寺塔建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金棺银椁出土时内棺有一尊涅槃像(图一二:1)。金棺素面无纹(图一二:2),底座铭曰:“当县女弟子江氏八娘同男王男佐舍金棺贮佛骨舍利安葬塔宫,愿生生安富,乞似龙女献珠脱体成正觉。大宋元祐癸酉刘滋舍手工。打造匠人袁安奕。”所谓“龙女献珠脱体成正觉”,见《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乃开示顿悟法门。银椁上有盝顶盖,下与须弥座式椁床连做,一侧为涅槃图,一侧为焚棺图。涅槃图中的佛陀也是左卧,九个弟子榻边悲泣,一端是驾云赶来的迦叶,另一端是乘云而至的摩耶夫人。椁盖錾刻婴戏图,八个童子吹笛、击钹、击拍板,又或持荷舞蹈(图一二:3)。

三 舍利塔、殿
金银舍利容器中,以塔的制作最见打制、攒造之工。金银塔式舍利容器,目前所知最早的实例,为隋代定州工匠所制,发现于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定州静志寺塔地宫。五代吴越国王钱俶仿效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宝塔,至北宋,阿育王塔的样式与纹饰早已十分成熟,金银制品的设计,自有通行的粉本为参照,而妆点华贵、攒造精细,则非其他材质可比。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五代吴越国纯银阿育王塔,即为难得的佳制。上海青龙镇遗址隆平寺塔地宫出土北宋铅贴金阿育王塔,通高25、底座长9.5厘米。铅塔系分片铸造,然后焊接成型,纹样透雕,外贴金箔(图一三)。靡丽侈富者,自推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七宝阿育王塔。据最外一重石函北壁所刻《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此系讲律演化大师可政,得宋真宗支持,即“寻奉纶言,赐崇寺塔”,遂聚工营造。寺宇建成,乃以“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安置于铁函,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瘗藏长干寺真身塔下。七宝阿育王塔通高117、塔座边长45厘米。塔身下方与基座固定在一起,上方与塔盖以子母口扣合,檀香木为骨架,其表覆银皮,通体鎏金,嵌宝处四百五十二,所嵌有水晶、玻璃、玛瑙、青金石等,多嵌作花朵和各式缠枝花的花心,又瑞兽额头的摩尼宝,此外则沿边和包角处。各个部件分别依形打制,包嵌后再以鎏金银钉固定(图一四:1)。中空的塔座内安置供养物。塔身中央立刹柱,刹柱底部套叠两个圆环,圆环上面打作金刚杵、迦陵频伽和天王,刹柱下方錾刻施舍人题记(图一四:2),上方从大到小五个相轮,顶端耸出宝瓶和宝珠。四个山花蕉叶亦中空,内容供养物。山花蕉叶的内侧式若拱门,其中一对,起拱处高悬璎珞伞盖,下方火焰圆光中是莲花上的坐佛,其下两侧为天王,下面方框内为施舍人题记。四天王分别擎杵、持剑、持斧、托塔(图一四:3),那么应是东方提头赖吒天王、西方毗楼博叉天王、南方毗琉璃天王、北方毗沙门天王。另外一对是莲瓣式背光中的立佛,两侧为供养菩萨,下方为题记。外侧面十九个佛传故事。塔身四面四个拐角均为莲花台上一身二用(在角为一、在面为二)的大鹏金翅鸟,绣羽低垂,造型如凤凰,四面四个拱门式开光,光内分别是本生故事,即萨埵太子饲虎(图一四:4)、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须大拏王变相。拱门两角各有二人合掌礼佛,上方是莲花上的坐佛,此外的空间满饰缠枝卷草和摩尼宝,好相端严,璀璨照耀。塔身上下各有两道连珠纹勾边的装饰带,装饰带内两端两朵嵌宝流云,中间是嵌宝三股金刚杵。基座与塔盖下方均为坐佛(图一四:5),后者两身坐佛之间是供养人题记,题记中央一个嵌宝兽面,上方为四字吉语—原是从发愿文的程式化用语中提取出来—四面分别是:“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风调雨顺”。

两宋金银舍利塔的制作,很有写实风格,乃至可以视作建造大塔的小样。南宋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七所记《真如院塔》的故事很有意思:“嘉兴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师者募缘兴建,烧造五色琉璃瓦以为庄严。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腊之乱,焚于烈焰,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掘凿其下,于地窖中得银塔一座。凡七层,高五尺,重千两,相轮栏楯,无不周备,刻画佛像,极为精巧,而无所镌记。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主者智炬梦一僧紫衣暖帽宛若大圣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废,可为兴复。’既寤,启心募化,至庆元三年丁巳,历十五岁而成。制范悉仿银塔不少异。冬十月,相轮合尖,以佛牙、银佛藏于地中为镇。”得银塔一座的“地窖”与藏佛牙和银佛的“地中”,当指佛塔地宫。此虽小说家言,并略有神异的成分,但素材必是采自实有之事—考古发现的舍利瘗埋情况,竟有不少与之相合,且验诸出土实物,如此精工之作,并不在少数。
出自定州静志寺塔基的银鎏金錾花舍利塔,高26.3厘米,重360克(图一五:1)。六角亭阁式,底座是唐五代至辽宋盛行不衰的风翻荷叶,不过这里风翻的卷边格外夸张,为求稳固当是原因之一。卷叶锥点叶脉,荷叶上五个开光,光内是鎏金水禽。上方仰莲托起六角平坐,毬路纹华版、宝珠望柱的一周栏杆。塔身正面两扇门,门扇三排浮沤钉,门环里挂着锁,此外五面錾刻一佛二菩萨二天王。塔檐上方饰宝珠,下方悬风铃。刹顶宝珠受花下垂刹链与塔檐宝珠相连。塔门下方錾刻发愿文“善心寺尼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并佛弟子张氏等十三人姓氏。同出的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石志记述当年五月廿二日葬三处舍利于地宫内,“又新施到银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银塔子二”,此即银塔之一。银塔之二,高26厘米,重321克。底为喇叭式圈足,坡面錾水禽并刻僧尼和信士十三人姓氏及“愿以此功德普沾诸有情同归解脱道囗到涅槃城”。上承仰莲座,塔身六面,正面门前两侧雕栏各有一身银片打制的拄剑天王,门侧两面为直棂窗。六角攒尖顶,出檐处錾铭“银共重一十两七分,金一钱”(图一五: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