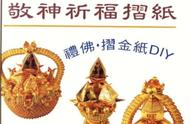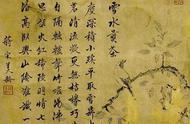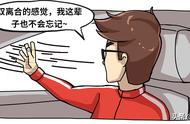造塔是功德,制作奉安舍利的金银容器如瓶、棺、塔、殿也是功德,功德主的名姓必要一一表出。表出的形式有多种。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七宝阿育王塔每一组图案的打制都有不同的出资人,在相应的图案中设计一个合宜的空间,使题记与纹样融为一体(图一四:4)。或做成荷首莲趺牌记的样子,即下为莲花托座,上为倒垂荷叶,中间錾铭。银牌记不妨单独成件(图二〇),又或以这种形式錾刻于施舍物,两种做法天封塔地宫都有实例。也有的借用道教斋醮用物如往名山洞府投简所用金龙银龙。宜兴法藏寺地宫出土五枚银龙,尺寸相当,身长都在12厘米,银龙均由两枚片材分别打制,然后扣合成型,龙身另外焊接火焰一般的两翼,努目奋睛,口吐长舌,舌尖回旋处悬缀银牌亦即施舍人题记(图二一),五龙所衔五枚银牌分别铭曰:庄十二娘舍银一两、崔大成舍龙一条、沈思明舍乞保男显僧、费氏舍龙一条保男女三人、张大忠舍银子一两。

捐资打造的材料费、手工费,七宝阿育王塔上的铭文记录最为详细。塔盖平顶围绕塔刹有四个剑环式开光,其中两个满錾铭文,详细记述施主名姓、捐资数目、打造之名目并银钱用度之状。其中述及“买银八十七两三分,计钱八十四贯二百四十文足陌。打造银塔手工钱二十二贯七百五十文足,〔镶〕珠宝手工三百八十五文足,五贯文足买檀香并手工作塔身,共用钱一百一十二贯三百七十五文足陌”。又“共渡过金二两八钱半”,“徐俗舍檀香七斤同作塔身,卢承福舍水晴五十个,演化大师将到大圣七宝念珠并水晴珠宝,并装在塔上,钟旺舍水晴”。宋代通用省陌(百)制,官方规定以七十七钱为一百,亦即以七百七十钱为一千(贯、缗),“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容斋三笔》卷四),因此贯、缗、千所表示的只是名义上的一千钱。因通用省陌制,在叙述政府收支、皇家赐予等等之钱数时,都不必说明是省陌,但在规定货物价格或民户赋税等等时,为了明确起见,常须说明是省陌还是足钱,省陌用“省”字表示,足钱用“足”字表示。宝塔铭文用这样的形式,当为表明诚敬。这里提供的重要信息,一是用银及当日之银价,一是制作工费。银价与传世文献所载当日银价的每两千钱相差无多。至于工价,买檀香并手工作塔身,五贯文;镶珠宝手工三百八十五文足;打造银塔手工钱二十二贯七百五十文足,显见得银塔的打制,技术含量最高,工费最昂。大中祥符元年,十文钱在秋收丰产地区可买粮一斗有余。同时代的金银器打制之工费,依此可推知大概。
宋代金银器的设计与制作,从造型到纹饰,都已经完全中土化,这也是金银舍利容器的演变趋向。不必说,佛教题材的世俗化是明显的,表现内容自然也不是与某一部佛经严格对应,粉本来源更非一途,乃至加入了工匠的发挥和创造。当代生活经验便是工匠的创意来源之一。金棺银椁的纹样设计取意于殿堂,或即与同时代的墓室壁画构思相通。出自兖州兴隆塔地宫的石函,其中一面线刻僧人启门,它与墓室壁画的妇人启门当是同源。早期涅槃图中天人和信众奏乐起舞供养赞叹的景象,在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银椁图案中表现为莲花台上的伎乐;出自句容崇明大圣寺塔的银椁,则在盖面錾刻奏乐舞蹈的孩儿,自是取用于其时流行的婴戏图。金银塔、殿和舍利容器的设计又多从当日的建筑形式撷取造型资源,如塔刹、须弥座,屋脊、版门、钩栏、雕云垂鱼,即便用作辅纹的图案,诸如折枝、毬路、方胜、缠枝卷草,也与建筑中的小木作不无关联。而这些图样均纳入《营造法式》。《营造法式》初成于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至徽宗朝,又诏李诫重新编修,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虽然它成书并不早,但作者编写的工作方法是“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考阅旧章,稽参众智”,因此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中言道,“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是在他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阅古代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依靠并集中了工匠的智慧和经验而写成的”。李诫既曾“勒人匠逐一讲说”,则工匠讲说的这一部分必是流行于当时。书里记述的装饰纹样,虽然今天见到的刊本图样因辗转摹绘已不免失真走形,但大致轮廓尚在,从中可见不少纹样唐五代即已出现,辽和北宋共同沿用,至此书纂就而汇总成式。本文叙述器物样式和纹饰,使用的名称即多采用《营造法式》中语,一是以此贯注笔者的理解与阐释,也是意在揭示造型和纹样与当代世俗生活的密切关系。
发现于寺塔地宫的金银舍利容器,或自身有铭记述供养人名姓及器具制作年月,或同出有石函、石碑记述舍利供养事迹,因此地域与时代都很明确。根据目前的发现,金银舍利容器的制作以北宋为多,而器皿与首饰的发现,却是南宋为多。作为金银器史的一部分,两宋舍利容器集中体现的打制与攒造的技艺,同样是这一时代金银首饰的特色,二者自然是相通的。那么从金银器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批资料更有一重实物标本的意义,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如七宝阿育王塔那样详细记述捐资和造价情况的铭文,则尤可珍视。(作者:扬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