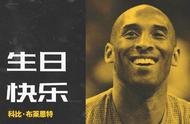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黄慎无可奈何,在职业画师的岗位上常发出怀疑人生的叹息:“以画谋生,良非得已”,但他没有敷衍,只是不甘心一生只做一个索然寡味的画工和生死由天的草木。十八九岁,迟迟没有长进的画技夹杂着青春期的叛逆,让黄慎感到懊恼。
黄母便点拨他:

小伙子听后醍醐灌顶。
纵观历史上的那些画界白月光,哪一位不是诗书画全优,看来谁都无法回避这千篇一律的成才之路——发奋读书。
黄慎的贫士苦读精神丝毫不亚于囊萤映雪,19岁的他寄宿在寺庙,白天作画,深夜借着佛龛的微光读书,像是一种漫长的修行,古人的“十年窗下无人问”在黄慎诗中变成了“无人知所处,寂寞掩松关”,他在绝对的孤独里完成了艺术上的求索,在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里只待厚积薄发的那一刻。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总是像连体婴出现在我们的意志里,驱使着所有想挤进成功人士名单的人争先恐后的贯彻这个必修的过场。

在到达扬州开启画家生涯之前的几年,黄慎为了卖出更多的画,远涉江南各地摸爬滚打,算是积攒了非凡的履历,迷之自信油然而生,大概是笃定了将来自己会出道,还为锦绣前程做了慎重的盘算——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黄慎的本名叫黄盛,35岁那年他偶然得知广东竟有画家与自己同名,直接影响到未来名垂画史独一无二的可能,果断把名字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