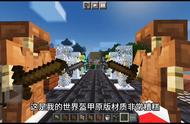和歌、俳句是日本古典诗歌的典范性样式,也是日本人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把和歌、俳句置于汉语文化的平台或语境中加以研究,首先就有赖于和歌、俳句的汉译,因而,无论从翻译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和歌、俳句的汉译及关于汉译方法的争鸣讨论本身,就是对和歌俳句的独特的研究形态。周作人、钱稻孙、杨烈、李芒、赵乐甡、林林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和歌俳句的汉译和汉俳的诞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俳句翻译及格律模仿中诞生的“汉俳”成为中国当代的新型小诗体,丰富了中国诗歌体式,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歌、俳句无论在内容表现,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与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王晓平等中国学者的和歌俳句的研究,在选题上也大都从中日文学关系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立场和中国文化的优势,在借鉴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日本和歌史、俳句史的研究上,郑民钦的《日本民族诗歌史》、《和歌美学》等著作最有代表性。
第一节 《万叶集》及古典和歌的译介
和歌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主要样式,日本最古老的和歌总集是《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万叶集》的地位相当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万叶集》收集了自公元4世纪到8世纪约400年间的和歌4500余首,全书共20卷,其中大部分是8世纪奈良时代的作品。《万叶集》写作和成书时,日本自己的“假名”文字还没有诞生,故全部借用汉字标记日语的发音(后被称为“万叶假名”),同时直接使用汉字(即所谓“真名”) 来表义,真名、假名混杂难辨,难以卒读。经日本历代学者研究考订,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用日语文言文整理出来的本子。《万叶集》中的各种体式的和歌都是五七调,但与汉诗的五言或七言的对偶句不同,一首和歌的句数和字数都是奇数的。其中“五七五七七”五句三十一字音的短歌在《万叶集》占绝大多数,《万叶集》之后便成为和歌的唯一体式。
明代的李言恭、郝杰编纂的《日本考》中,有编纂者翻译的日本和歌(短歌) 39首,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和歌翻译,译文形式不一,最多的是五言四句,其次是四言四句。晚清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也有对日本和歌的介绍。第一六二首云:“弦弦掩抑奈人何,假字哀吟伊吕波。三十一声都怆绝,莫披万叶读和歌。”并注云:“国俗好为歌。上古口耳相传,后借汉字音书之。‘伊、吕、波’作,乃用假字。句长短无定,今通行五句三十一言之体,始素盏鸣尊《八云咏》。初五字,次七字,又五字,又七字,又七字,以三十一字为节。声哀以怨,使人辄唤奈何。《万叶集》,古和歌名作。有歌仙、歌圣之名。”这是对和歌最早的较为概括的介绍。第一五七首诗及诗注介绍了和歌在宴饮等场合的使用,还介绍了日本古代“歌垣”(赛歌会) 的盛况。
到了现代,最早介绍和歌的是周作人。1921年,他发表《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 一文,介绍了日本和歌,并在与中国诗的比较中,对和歌的基本特点做了提示性的总结。他认为,和歌的特点是由日本语言的特点所决定的,“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作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而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得不含蓄。”他认为和歌与中国的诗比较起来,是“异多而同少”,这是由和歌的特殊形式所决定的,和歌短小,擅长抒情而不擅长叙事,也不能像汉诗那样使用典故。所以他认为和歌很难译成中文。周作人之后,谢六逸在1925 年6 月《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关于〈万叶集〉》的介绍性文章。
对于中国的和歌研究而言,和歌特别是《万叶集》的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万叶集》翻译一方面是中国学者、读者阅读理解的津梁,另一方面,对翻译者而言,翻译本身需要对原作有透彻的理解、准确的语言转换,需要对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注释、出典等加以鉴别和吸收。因此,汉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充满困难和挑战的研究。
最早翻译《万叶集》的是钱稻孙(1887—1...
《万叶集》的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是杨烈(1912—2001年)。早在1960年代杨烈就译完了《万叶集》。这是20世纪我国《万叶集》的仅有的一个全译本。但也由于国内社会动乱等原因,该译本一直到了1984年,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为“诗苑译林”之一种出版。关于为什么需要《万叶集》的全译本,杨烈在译序中说:“中国至今没有全译的《万叶集》。虽然有人和我自己都曾发表过少许,但在全书四千五百首中,所占比例太小,不足以窥全豹。所以仅从文献的立场看,也应该有此书的全译本问世。”杨烈的《万叶集》译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全译本,填补了我国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一大空白。《万叶集》中有许多歌,意义暧昧难解,翻译更难,全译本无法跳过。全部译出,难能可贵。杨译本除了译文本身的欣赏价值之外,还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曾帮助杨烈校对译文的施小炜在《〈万叶集〉〈古今集〉以杨译浅论》(《日本文学散论》,第21页) 中说:面对诗歌翻译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和难题,“杨先生作了一次用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翻译外国诗歌的成功尝试:杨先生将长歌和旋头歌等全部用五古和七古的形式译出,而短歌则全部译成格律严谨的五绝,既传神达意,又形式完美,而且符合我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兼得形似与神似之妙”。的确,严格按中国的五言律诗的韵律和体式来译,译文风格统一。用整齐的汉诗体来翻译“五七调”的和歌,实在很不容易,这其中不但是意义的传达翻译,也势必是原作的意义的增值和阐释,译者为此付出的心血、智慧和创造性劳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全部以汉诗的体式来翻译和歌,原作的形式便不可兼顾了。例如,以短歌而论,短歌的“五七五七七”五句共三十一音节大约只相当于十个左右的汉字所承载的信息,以五绝的形式翻译三十一个音节的短歌,往往势必会增加原作中没有的词和意义,这在形式上不可谓“忠实”的翻译,但确实符合中国一般读者的欣赏趣味。
还应该提到的是杨烈对《古今和歌集》的翻译。《古今和歌集》,又简称《古今集》,是继《万叶集》后,在10世纪初年出现的第二部和歌集。同时又是第一部由天皇下诏编辑成书的所谓“敕撰和歌集”,也是第一部由刚创制不久的“假名”文字写成的和歌集。《古今集》仿《万叶集》的体制,也分为二十卷,收录了《万叶集》未收的和歌与新作和歌1110首,除个别例外,全部是“短歌”,篇幅约有《万叶集》的四分之一。《古今集》的风格与《万叶集》的雄浑、质朴颇有不同,其风格特点被称为“古今调”,题材狭窄,专写四季变迁、风花雪月、人情与爱情,风格纤细婉曲,精镂细刻,讲究技巧与形式。《古今集》代表了和歌的成熟状态,对后来出现的和歌集的影响也超过了《万叶集》。杨烈的《古今集》的翻译,也是在六十年代完成的,但直到1983年,才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杨烈在《译者序》中说:“我在六十年代先后译完《古今和歌集》和《万叶集》。六十年代对我来说是寂寞的年代,住在斗室之中以翻译吟咏为事,每每译出得意的几首,便在室内徘徊顾盼,自觉一世之雄,所有寂寞悲哀之感一扫而光。”杨烈的《古今集》译文,绝大多数仍使用五言古诗的句式,大部译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如译著名女歌人小野小町的歌:“念久终沉睡,所思入梦频,早知原是梦,不作醒来人”;“莫道秋长夜,夜长空有名,相逢难尽语,转瞬又黎明”等等,都很有韵味。
在已有的翻译的《万叶集》及古典和歌翻译的基础上,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就《万叶集》及和歌的汉译理论与方法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是李芒(1920—2000年)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79年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和歌汉译问题小议》的文章,认为以往的和歌翻译有两种主要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钱稻孙的翻译,钱的翻译在正确理解原意、遣词造句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大部分译文使用《诗经》的笔法,文字过于古奥、难懂,不利于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万叶集》,因此其译法是不可取的;第二种情形是主张一律用五言或七言四句的形式(杨烈译文),这种译法使译文具备中国古诗的形式,如果在实践上做得好还是可取的。但是,以短歌而论,句法和内容多种多样,应采取相应的译法,而不宜在形式上强求一律,宜从原歌出发,使用七言(一般多用于翻译长歌)、五言、四言和长短句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该文发表后,李芒又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1期上发表《和歌汉译问题再议》,通过进一步举出自己和他人的译例,将前文的观点加以展开,认为和歌汉译最重要的要做到“信”,同时也要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李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罗兴典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和歌汉译要有独特的形式美——兼与李芒同志商榷》一文,认为李芒译的短歌,在译文形式上多种多样,但“作为一首首不定型的和歌,似乎还缺少他独具的特色——形式美”,因此他提出:“除了李芒同志采用的那些和歌汉译句式以外,能否还采用一种和歌固有的句式——‘五七五七七’句式。”他认为,虽然这样译,要在译文中增加原文中没有的字词,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不损害原诗形象的前提下,汉译时可以适当增词,灵活地变通。这在翻译理论上也是容许的”。对此,李芒在发表《和歌汉译问题三议》(《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 中,认为“不能片面地绝对地界定诗歌的形式问题”,多种多样的译法也有“另一种形式美——参差美”,同时认为罗兴典提出的按和歌原有句式来翻译,也可以作为“多种多样”的译法的一种。王晓平又在同刊1981年第2期上,发表《风格美、形式美、音乐美——向和歌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建议》,认为和歌翻译中这三“美”都必须兼顾,不可单纯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沈策在同刊1981年第7期上,发表《也谈和歌汉译问题》,指出:《万叶集》“这部歌集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实际上那些和歌在当时的读者中,听起来是很容易明白和欣赏的”,他提出也可以用汉语口语来翻译和歌,并举出了自己的一些译案。接着,孙久富发表《关于〈万叶集〉汉译的语言问题的探讨》,对沈策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万叶集》所使用的是日本上代古语,它同现代日语差别很大,将《万叶集》译成现代日语,对传达原作风格尚且有很大局限,而以现代汉语翻译《万叶集》,局限性就更大。他最后说:“我认为采用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翻译这部歌集更为有利。”接着,孙久富又发表《关于〈万叶集〉古语译法的探讨》,进一步举例探讨了用古汉语翻译《万叶集》的可行性问题。丘仕俊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上,发表《和歌的格调与汉译问题》,提出为保持其格调,和歌直译成“三五三五五”的格式。总之,关于和歌汉译问题的讨论,历时四年多,而且若干年后余音不绝,是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史上少有的就日本文学某一体裁的翻译所进行的专门的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吸引了读者对日本文学翻译问题的注意,对和歌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增进了人们对和歌与《万叶集》的阅读与研究的兴趣。
李芒翻译的《万叶集选》,是改革开放后译出的第一种《万叶集》的选译本。这个译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998年10月正式出版。《万叶集选》选译和歌734首。李芒在《译本序》中说:“我们过去的译文,有的偏重于古奥,有的较为平易。但有人照搬原作的音数句式,由于中日文结构迥异,这样译成中文必然比原文长出不少,就难免产生画蛇添足的现象。然而,总的来说,大家都为我国的《万叶集》欣赏和研究做出了贡献。本书译者参考了上述种种译作,采取在表达内容上求准确、在用词上求平易、基本上运用古调今文的方法,以便于大学文科毕业,喜爱诗歌又有些这方面常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个别词查查字典就能读懂。”李芒的译文是他和歌汉译理论主张的实践,即译文不拘泥于某一种格式,根据情况灵活变化。他在《万叶集选》中的绝大多数译文使用的是五言律诗的形式,少量译文五言、七言并用,或夹以长短句。李译本较为晚出,有条件借鉴前译,加之所选和歌均为《万叶集》中之珍品,也为现代日本读者所广泛传颂。译文锤炼精当,既有古诗之风,又晓畅易懂,具有较强的欣赏价值。赵乐甡《万叶集》译本是继杨烈译本后的第二个全译本。1980年代开始翻译,到2000年全部完成,200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历时二十多年。赵乐甡在“译序”中谈到了此前的《万叶集》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古奥。以为古歌要用古语,因此译得比《诗经》还难懂。当时日本人的语文也不见得那么古。
二是添加。“戏不够,神来凑”似的,字数不够硬要凑,便添加一些原歌没有(不可能有) 的词,甚至改变了歌的主旨或意趣。
三是打扮。本来是些朴实无华的作品,却有意尽量选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浓施粉黛,打扮得花枝招展,似乎这才是“诗”。
四是改装。不论原作的表现特点如何,一律纳入起承转合的四句里,倒也像“诗”,只是不是那首“歌”。
上述问题,在钱译本、杨译本中的确是存在的。总起来说就是重视中国读者的阅读感觉,而使和歌“归化”于中国的汉诗,而不太尊重原作独特的形式,赵译本是对此前译本的一种反驳,强调尊重和歌(主要是短歌) 的形式,打破过去的五言、七言律诗的译法,采用日本近代以来流行分三行分写的短歌体式,每句字数不等,使用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以直译为主,尽量不添加原作中没有的意义和词语。相对于钱译和杨译的“归化”和“仿古”的翻译,赵译则是一种以“存貌”为主要原则的“异化”翻译,文字上文白夹杂,有时长短句参差交错,有时句式整齐划一,不避俚语俗语,也有古语雅词,还照顾了中国读者的感觉,就是在句末使用了汉诗才有的韵脚。这样的翻译,就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在欣赏性上可能不如归化的“翻译”,例如,“苦恋阿妹/古昔,有人亦如我耶/辗转不能眠/”(第497 首);“我家院中,/花橘零落结珠实,/可串绳”(第1489首);“坐立等,不耐烦;/来此幸逢君,/胡枝子,插发端”(第4253首)。实际上是一种“述意”(转述大意) 式的翻译,这一点上有似于当年周作人在小林一茶俳句翻译时所采用的方法。但俳句以古拙、幼稚为美,和歌则以古雅为尚,这种带着“拙”味的“述意”式的翻译是否适合和歌美的呈现,不能不说还是一个问题。不过,另一方面,考虑到当今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对日本和歌的了解比此前增多,对日本文学样式的理解和接受度也比从前大有提高,赵译的这种“异化”的翻译在“归化”的翻译之外,更有出现和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万叶集》的研究而言,以前不通,或粗通日文的研究者大多以杨译本作参照,但由于杨译本常常增加原作中没有的字词,例如,谈到日本的色彩感,有的论者直接以杨译本为根据,找出其中的红绿黄白之类的词,实际上原文未必存在,有时是靠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赵译本更尊重原文,力求对原作的信息不增不减,对于中国的《万叶集》研究者、中日诗歌比较研究者,更有可靠的文献意义和参考价值。
赵乐甡全译本出版(2008年) 几年后,金伟、吴彦夫妇的合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日本文学丛书”出版,这是第三种汉语全译本,一律采用现代汉语翻译,形式不拘一格。译者在“译序”中说:“本书在翻译期间,参考了各种《万叶集》相关的注释书、校本、索引、辞书、年表、定期刊物、学会杂志以及各种中日古辞书,在此不一一列举,谨表感谢。”但不知为何,唯独不提对已有的多种汉译本是否有所参考。从翻译学上的“复译”的角度来看,如果复译者不知道之前有汉译本存在,则属无知,是译者和研究者的大忌;如果故意无视已有的译本的存在,不参考已有的诸种译本,要扬长避短、超越以前的译本、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复译的必要性、合理性都成了疑问。比较地看,这个译本的特点是所有的篇目都用现代汉语来译,而且不使用韵脚,从语体的口语化上看要比赵译本来得更彻底;短歌有时写为三行,有时写为四行或五行,从形式上看也比赵译本来得更为自由。总之,该译本比此前的译本更为通俗易读。值得提到的是,在此之前,金伟、吴彦还根据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古代歌谣集》翻译出版了《日本古代歌谣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使用现代汉语,对散见于《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文献中的古代歌谣做了系统翻译,对研究日本和歌及日本古典民俗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节 俳句的译介及汉俳的兴起
俳句是从和歌中演化、独立出来的日本古典诗歌样式之一,经典的俳句在形式上是“五七五”三句共十七个音节,其中在用词或句意上要暗含着表示春夏秋冬某一季节的“季题”或“季语”。还要使用带有调整音节和表示咏叹之意的“切字”。近代以前俳句一般称为一般“俳谐”,“俳谐”与中国古代的“俳谐诗”有着一定的关系。
据周一良先生在《八十年前中国的俳句诗人》(《日语学习与研究》,1980年第4期) 和郑民钦《中国俳人苏山人》(《中日文化与交流》第2辑,1985年) 的研究和介绍,清末的旅日人士罗卧云(俳号苏山人) 是第一个写俳句的中国作家,在当时日本俳坛也有一定影响。而最早翻译和详细介绍俳句的,则是周作人。1916年,周作人(启明)在《若社丛刊》第三期上,用文言文发表了题为《日本之俳句》的小短文,是说日本的俳句“其体出于和歌,但节为十七字,以五七为句,寥寥数言,寄情写意,悠然有不尽之味。仿佛如中国绝句,而尤多含蓄”。又说:“俳句以芭蕉及芜村作为最胜,唯余尤喜一茶之句,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并说俳句的翻译,自己“百试不能成,虽存其词语,而意境殊异,念什师嚼饭哺人之言,故终废止也”。他在《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1921年5月) 一文中,对俳句的由来、体式、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正冈子规等做了介绍,认为:“芭蕉提倡闲适趣味,首创蕉风的俳句;芜村是一个画人,所以作句也多画意,比较地更为鲜明;子规受到了自然主义时代的影响,主张写生,偏重客观。表面上的倾向,虽似不同,但实写情景这个目的,总是一样。”周作人还对俳句的通俗变体“川柳”做了介绍,谈到川柳“与俳句一样,但没有季题与切字这些规则”,关于川柳的用语,周作人说:“短歌俳句都用文言,(一茶等运用俗语,乃是例外,) 川柳则用俗语,专咏人情风俗,加以讽刺。”实际上,短歌用文言雅语,而俳句包括蕉门俳谐,虽然不少使用汉语词汇,但也都是提倡使用俗语的,蕉门俳论书《二十五条》更鲜明地提出俳谐创作就是“将俗谈俚语雅正化”,与谢芜村在《春泥发句集序》中也提出俳谐应使用俗语,可见,在使用俗语的问题上,小林一茶并不是“例外”。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还再次强调了日本诗歌(包括和歌、俳句)“不可译”。但他还是译了几首,如松尾芭蕉:“下时雨初,猿猴也好像想着小蓑衣的样子”;“望着十五夜的明月,终夜只绕着池走”。小林一茶:“瘦虾蟆,不要败退,一茶在这里”;“这是我归宿的家吗?雪五尺”等。可见,周作人一开始就知道和歌俳句不可译,所以他干脆完全不管俳句的“五七五”的形式,而只是做解释性的翻译,即他所说的“译解”,即把意思翻译、解释出来就行了。译出后,他又承认:“各自美妙的意趣,但一经译解,便全失了。”然而另一方面,他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此后对小林一茶的译介中。
在日本的俳人中,周作人对小林一茶可谓情有独钟。他在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上,发表了题为《一茶的诗》的文章,开篇就写道:
日本的俳句,原是不可译的诗,一茶的俳句却尤为不可译。俳句是一种十七音的短诗,描写情景,以暗示为主,所以简洁含蓄,意在言外,若经翻译直说,便不免将它主要的特色有所毁损了。一茶的句,更是特别;他因为特殊景况的关系,造成一种乖张而且慈悲的性格;他的诗脱离了松尾芭蕉的闲寂的禅味,几乎又回到松永贞德的诙谐与洒落(Share 即文字的游戏) 去了。但在根本上却有一个异点:便是他的俳谐是人情的,他的冷笑里含着热泪,他的对于强大的反抗与对于弱小的同情,都是出于一本的。他不像芭蕉派的闲寂,然而贞德派的诙谐里面,也没有他的热情。一茶在日本俳诗人中,几乎是空前而且绝后,所以有人称他作俳句界的彗星……
这段话不长,也不深奥,却把小林一茶俳句的特点精确地点了出来。“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周作人之所以特别推崇小林一茶,恐怕与他的“人的文学”的提倡、与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密切相关的。他在这篇约五千字的文章里,一连译出了一茶的俳句49首,且翻译且评议,可以说将一茶最有特点的作品大都翻译出来。至于翻译方法,一如他的《日本的诗歌》一文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散文译述大意,去掉了原文形式的外壳,却歪打正着,不经意间传达出了一茶俳句的“俳味”,而令人觉得清新可喜,如“来和我游戏罢,没有母亲的雀儿!”“笑罢爬罢,二岁了呵,从今朝开始!”“一面哺乳,数着跳蚤的痕迹”;“秋风啊,撕剩的红花,拿来作供”等等,这种天真稚拙、轻松随意、悲凉而又温馨的小诗,与“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严肃板正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文化、与五四诗坛的“少年中国”的气息,不期而合。所以,周作人的俳句翻译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周译俳句和泰戈尔的小诗的影响下,192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国诗坛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小诗”运动,“小诗”在很大程度是对周作人俳句翻译的模仿,也是对中国传统古诗的矫枉过正。
1937 年,周作人发表《谈俳文》(《文学杂志》,第1 卷第2 期,1937年7月),由俳句而进一步谈到“俳文”(俳谐文),这也许是中国最早地系统介绍日本“俳文”的文章。周作人给俳文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俳文者即是这些弄俳谐的人所写的文章。”认为日本的“俳谐”这一名词源自中国,“俳文”和中国的“俳谐文”有着渊源关系,并指出:“用常语写俗事,与普通的诗有异,即此便已是俳谐”,认为“日本的俳文有一种特别的地方,这不是文人所作而是俳人及俳谐诗人的手笔,俳人专作俳谐连歌以及俳句(在以前称为发句,意云发端的一句),也写散文,即是俳文,因为其观察与表现方法都是俳谐的,没有这种修炼的普通文人便不能写。……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虐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但其表现方法同以简洁为贵,喜有余韵而忌枝节,故文章有一致的趋向,多用巧妙的譬喻适切的典故,精炼的笔致与含蓄的语句,复有自由驱使雅俗和汉语,于杂糅中见调和,此其所以难也”。并指出“现今日本的随笔(及中国的小品) 实在大半都是俳文一类”,这就点出了当时中国盛行已久的小品散文与日本古代俳文、现代随笔之间的关系。
谈到俳文的时候,必须要说到的是,周作人所说的“俳文”,到了70年后的2008年有了系统的翻译,那就是翻译家陈德文的《松尾芭蕉散文》。松尾芭蕉的俳文不是日本最早的俳文,但堪称古典俳文的典范。陈德文在“译者前言”中指出:“照现在的观点,所谓俳文,就是俳人所写的既有俳谐趣味,又有真实思想意义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结尾处附有一首或数首发句(俳句)。”这是通常的定义,也与周作人的俳文定义一脉相通。陈德文在《松尾芭蕉散文》中,将芭蕉的散文分为“纪行、日记编”和“俳文编”两类,这也是权宜的分法,其实纪行和日记等总体上都视为“俳文”也未尝不可。《松尾芭蕉散文》将芭蕉俳文的主要作品都翻译出来了,对读者来说,译者实现了在“前言”中所说的“送您一个完整的芭蕉”的承诺。
此外,在1930 年代,还有傅仲涛发表了《松尾芭蕉俳句译评》(《新月》,第4卷第5号,1932年11月1日),翻译介绍了松尾芭蕉的若干作品;1936年,徐祖正发表《日本人的俳谐精神》(《宇宙风》,1936年10月1日)。抗日战争及此后的国共四年内战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像俳句这种闲适脱俗的、纯审美的诗体的译介就失去了环境和余地。
到了1980年代,诗人、翻译家林林(1910年生) 的《日本古典俳句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为“诗苑译林”之一种,于1983 年底出版。译本选译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三位最著名的俳人作品约400首。林林的译文,基本上使用了白话、散文体的译法,即使有的译文用了较整饬的文言句式,也都通俗易懂,一般分两行或三行。如松尾芭蕉的几首俳句,译文如此:“请纳凉,北窗凿通个小窗”;“知了在叫,不知死期快到”;“蚤虱横行,枕畔又闻马尿声”;“旅中正卧病,梦绕荒野行”。小林一茶的俳句:“小麻雀,躲开,躲开,马儿就要过来。”“瘦青蛙,别输掉,这里有我一茶”;“像‘大’字一样躺着,又凉爽又无聊”。可以说译文风格基本承袭了周作人。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民俗学家钟敬文为林林的译本所写的序言,是一篇颇得俳句的要领和精髓的文章,钟敬文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古今有一些诗体,如两句成章的信天游(陕北)、爬山歌(内蒙古一带) 等,在同是形制短小这一点上,与日本的俳句是相通的。关于俳句的体味和欣赏,钟敬文形象地指出:俳句是凝缩的,“它像我们对经过焙*茶叶一样,要用开水给它泡过来,这样,不但可以使它那蜷缩的叶子展开,色泽也恢复了(如果是绿茶)。更重要的是它那香味也出来了。对于俳句这种小诗。如果读者不具备上述的那些条件,结果恐怕要像俗语所说的‘囫囵吞枣’那样,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了。”他并结合芭蕉和一茶的俳句,对俳句的思想感情、情绪感觉、象征、同感等手法的运用等等,做了细致的分析。关于俳句的翻译,钟敬文认为,尽管采用口语散文体来翻译有缺点,但它也有两点颇为值得注意的好处,一是它能尽量保存原文中的感叹词,如“や”“かな”等,这些叹词很重要,往往起着传神的作用;第二它有利于表现出异国情调,因为我们译的毕竟是外国诗。……钟敬文作为一个诗人曾写过汉俳,对日本俳句之美有着深切的体会,故能有切中肯綮之论。
在译介古典俳句的同时,现当代俳人的作品在1990年代也陆续被译介了不少。其中,葛祖兰的《正冈子规俳句选译》是出版最早的近代俳句译作集。正冈子规(1867—1902年) 是明治时代人,也是19世纪后半期由古典走向近代的俳句革新的领袖人物。译者葛祖兰(1887—1988年) 本人也是一个俳人,从1940年代起一直写作俳句。1979年,他的《祖兰俳存》在日本出版,引起重视,日本还为他树立了“句碑”和铜像。葛译《正冈子规俳句选译》198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共选译、注释子规的俳句163首。每首都先列原文,再列汉译,最后是作者的注解和译者的注解。译文大都用七言两句或五言两句的古诗句式翻译,和上述的周作人、林林的翻译属于不同的两种路数,与钱稻孙、杨烈用中国古诗体翻译和歌一样,葛祖兰可以说是俳句翻译中的“归化”派。
李芒在当代俳句的译介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1993年译出了《赤松蕙子俳句选》,1995 年出版了《藤木俱子俳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由李芒主编、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1995年出版的“和歌俳句丛书”,收录了金子兜太、加藤耕子、赤松唯等俳人的作品数种,全部采用原文与汉译对照的形式,就译介的系统性和规模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日本俳句的翻译介绍的同时,仿照俳句的“五七五”格律写成的“汉俳”,也悄然兴起了,并成为近1980年以降中国诗坛的一种崭新的诗体。
早在五四时期,在所谓小诗中,郭沫若等就曾用“五七五”句式写过作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汉俳”。但那时的诗人在写作时,并没有“汉俳”的自觉意识。汉俳的真正发足,还是在1980年代。1980年5月底,在欢迎以大林野火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赵朴初仿照俳句的“五七五”的格律写了几首别致的诗,其中一首诗曰:“绿荫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这大概就是“汉俳”一词的由来。此后,杜宣、林林、袁鹰等相继发表了一些汉俳作品。北京的《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中国风》,江西的《九州诗文》等报刊,提供了发表的园地。“汉俳”作为诗歌之一体,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到了1990 年代后,汉俳创作的势头有了更大的发展,《香港文学》、《诗刊》、《当代》、《文史天地》、《人民论坛》、《民俗研究》、《中国作家》、《日语知识》、《佛教文化》、《金秋》、《扬子江诗刊》、《黄河》、《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中华魂》、《北京观察》等许多报刊陆续刊登汉俳。到2012年为止,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已出版的各种汉俳集有20多种,如中国香港的晓帆的《迷朦的港湾》(文学报社出版公司,1991年),谷威的《情丝》(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林林的汉俳集《剪云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林岫的《林岫汉俳诗选》(青岛出版社,1997年),段乐三的《段乐三汉俳诗选》(珠海出版社,2000 年),刘德有的《旅怀吟笺——汉俳百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年),曹鸿志的《汉俳诗五百首》(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年),张玉伦的《双燕飞——汉俳诗百首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肖玉的《肖玉汉俳集》(香港,2001年),杨平的《杨平汉俳诗选》(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 等。此外,中日俳句、汉俳交流的集子也有出版,如上海俳句(汉俳) 研究交流协会编辑的中日汉俳、俳句集《杜鹃声声》,北京的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竹笋(たかんな)俳句访华团和中国中日歌俳研究中心共同创作和编辑的《俳句汉俳交流集》等。一些城市和地方(如长沙、益阳、长春等) 还成立了汉俳协会之类的团体。如1995 年在北京成立了以林林为顾问、李芒为主任的“中国中日歌俳研究中心”,2009年长春成立长春汉俳学会,以及全国性的“中国汉俳学会”等,还出现专门的汉俳同仁杂志,如长沙的《汉俳诗人》、长春的《汉俳诗刊》等。
其中,中国香港的晓帆(原名郑天宝,1935年生) 的《迷朦的港湾》,是中国最早的汉俳集,1993年出版的《汉俳论》是最早的专门论述汉俳的理论著作,在理论与创作方面具有相当影响。后来,晓帆在1997年《香港文学》杂志(1997年10月) 上发表《汉诗—俳句—汉俳:中日文化的双向交流》的文章,该文根据作者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讲座稿修改而成,也是作者此前观点的一种提炼和概括,对汉俳的来龙去脉、艺术特点、世界十几个国家的俳句(英俳、法俳、德俳、美俳等) 创作情况,还有本人的汉俳创作心得,都做了清晰的表述。晓帆认为,日本俳句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广为流行,在于俳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题材发现的独特性”,二是“创造的新奇性”,三是“简练的必然性”,四是“捕捉实态”,五是“象征的力量”,六是“季语的作用”。其中在第五条中说:“俳句要求有深刻的内涵、令人寻味的余韵和朦胧美,我想这就是人们所欣赏的‘俳味’。这种功能靠象征来完成。”提出“汉俳的艺术技巧”主要是要表现出“意象美、意境美、含蓄美”,他把自己写作汉俳分为五种不同的风格,并举例证之。即“雅俳”(典雅优美、押韵,如《紫荆》:“山色浮窗外/燕子低飞紫荆开/幽香落满腮”)、“俗俳”(通俗平易、口语化,如《香港时装》:“时装走天涯/香江风情染华夏/难辨是哪家”)、“谐俳”(风趣、活泼、诙谐、押韵,如《寻句》:“手扶辛弃疾/踏遍深山绕小溪/不怕没有句”)、“讽俳”(讥笑、讽刺、押韵,如《蜜语》:“蜜语一箩箩/苦口良药常缺货/今朝无华佗”)、“散俳”(自由抒发的现代散文式小诗,可不押韵,如《琴手》:“自从那一夜/弹响了你的心弦/我才算琴手”)。晓帆的理论与创作,对后来的汉俳理论与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汉俳理论方面的专著还有林克胜的《汉俳体式初探》(长春出版社,2009年) 等,李芒、刘德有、纪鹏、罗孟东、段乐三,都写过汉俳论方面的文章。
最早出版的诸家汉俳合集《汉俳首选集》(青岛出版社,1997年),收集了包括老中青三代、共33名汉俳诗人的代表作,如钟敬文的“终于见面了/多年相慕的心情/凝在这一握”;赵朴初的“入梦海潮音/卅年踪迹念前人/检点往来心”;林林的“相招开盛宴/远客尝新荞麦面/深情常念念”;公木的“逢君又别君/桥头执手看流云/云海染黄昏”;杜宣的“葡萄阴下坐/蕉扇不摇凉自生/断续听蝉声”;邹荻帆的“高树衍根深/地层泉水青空云/自有天地心”;李芒的“白梅辞丽春/缤纷蝶翅离枝去/犹遗青梦痕”;屠岸的“画室满春风/笔下桃花万朵红/身在彩云中”;袁鹰的“昨夜雨潇潇/梦绕樱花第几桥/未知归路遥”;纪鹏的“金门邻厦门/两岸烟雨幻彩云/炎黄骨肉亲”;刘德有的“霏霏降初雪/欣喜推窗伸手接/晶莹掌中灭”;陈明远的“青涩的果子/一夜之间变红了/只是为了你”;林岫的“西服套袈裟/儒释而今各半家/蛋糕输讲茶”;郑民钦的“秋野雨初晴/月色今宵分外明/可怜冷如冰”等33人的汉俳约300首,可以说是汉俳精品的集大成的选集。林岫为此书写的《和风起浪俳——兼谈汉俳创作及其他》附于书后,论述了俳句与汉俳的关系,总结了汉俳写作在格律、季(俳句中表示或暗示四季的字词) 方面的特点。
汉俳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深化的结晶。汉俳虽是日本俳句影响下产生的外来诗体,但鉴于古典俳句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所以我国有些学者、诗人并不把汉俳看成是纯粹外来的东西,鉴于历史上中日诗歌和中日语言的特殊的因缘关系,汉俳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快,作者和欣赏者较多,理论与创作上都有声有色。但是,另一方面,汉俳作者们对日本俳句的美学精髓加以体会与把握的不多。在理论上,对汉俳的外在形式谈得多,而对汉俳的审美特征,特别是对“俳味”的体悟与论述太少。所谓“俳味”,也就是俳谐精神,归根到底要归结于“俳圣”松尾芭蕉及蕉门弟子提出并论述的俳谐审美概念——“寂”。“寂”就是一种闲适、余裕的生活态度,洒脱、游戏的艺术精神,静观、写生的诗学方法。就是要求俳人有独特的“俳眼”,能够看到“寂之色”;要有独特的“俳耳”,能聆听到“寂之声”,要有独特的“寂之心”,能去感受和体悟虚与实、雅与俗、老与少、“不易”与“流行”的和谐统一,还要有对这一切的艺术地、审美地表达,那就是“寂姿”。总之,汉俳应该在审美上将俳句这些美学精髓吸收过来,才能一定程度地矫正中国传统诗歌那种“文以载道”、“忧国忧民”、“发愤”、“言志”、“风骨”等传统士大夫的泛社会化、泛政治化的思维习惯,才能在中国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传统诗学与诗作中吹进异域之风,从而丰富我们的诗学趣味。这才是我们输入汉俳这种外来诗体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否则,汉俳只不过是用“五七五”写的传统意义上的汉诗而已,就失去了“汉俳”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日本俳句的审美特色是与中国传统诗歌互为对比和补充的,而现有的绝大部分汉俳却是以汉诗词的创作思路与习惯来写的,徒有“五七五”的外形,仍自觉不自觉地沿袭古典诗词的思维方法和写法,严肃雅正有余而轻松潇洒不足,使很多作品在立意、取景、遣词上都十分平庸,没有汉俳应该有的潇洒、机警、超脱与新鲜味,甚至一些作品用汉俳来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等社会问题,过于“文以载道”、过于“工具化”,便没有了汉俳应该有的超越与余裕。尽管如此,随着日本俳句研究及“寂”的美学研究与体悟的深入,随着国人精神境界的进一步超越和拓展,可以相信,“汉俳”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在中国将会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第三节 李芒、王晓平等的《万叶集》及歌俳研究
中国和歌俳句的研究,一开始就与和歌俳句的汉译联系在一起。李芒先生是中国最早对歌俳翻译问题做出理论探索的学者,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带头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在日本文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和歌俳句,二是现代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1986年前发表的相关成果都收入了《投石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 一书中。现在看来,李芒在歌俳方面的文章似乎更有学术价值。如上所述,他在1979—1982年间在《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上连续发表的数篇相关文章,曾引发了关于歌俳翻译问题的讨论,推动了歌俳在中国翻译传播乃至汉俳的产生,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上,是值得记忆的。
《投石集》中的相关文章的总体特点,是作者以日本文学的启蒙者的姿态,从鉴赏的角度出发,对日本文学之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审美特质,做了具体的分析解说。他的基本理论根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来自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特征论,再结合他自己的中日文学比较论,然后加以诠释和发挥。除了上面提到的1979—1982年间发表关于和歌汉译问题系列文章之外,还有若干文章,涉及歌俳研究问题。其中,《壮游佳句多——日本俳句访华佳作译评》(《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 是一篇将纪游、评论、研究熔为一炉的文章,将日本俳句作家访华时吟咏中国山水景物的作品,加以介绍和评析,在1980 年代初期,起到了促使国人注意俳句、欣赏俳句的启蒙作用。《日本文学欣赏刍议》(《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年第3、4期) 从和歌俳句、物语等日本独特的文学样式出发,对吉田精一等人提出的日本文学的特点做了概括,如“喜爱阴翳和朦胧,追求深幽的余韵和优美”、无逻辑的结构、局部描写的细腻与光彩等,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日本古典诗歌的源头——记纪歌谣》(《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1期) 是周作人之后我国研究记纪歌谣的最为翔实的一篇文章,对《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古代歌谣做了系统介绍,又将其中的重要作品引出原文并译成中文,并从诗歌起源的角度,比较了中日两国偏重“言志”和偏重“抒情”、表现社会政治与疏离社会政治的两种不同的诗学传统。《从和歌到俳句》(《日语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5期) 一文,介绍了从和歌、连歌,再到俳句的发展演化历程,并援引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歌俳作品,原文之后加上汉译,做具体的个案分析,是歌俳知识的启蒙性文章。《和歌·俳句·汉诗·汉译》(《日本研究》,1986年3、4期) 是一篇总结性的长文,从中日诗歌比较的角度,将作者此前关于歌俳及其汉译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歌俳汉译形式多样化的主张,进一步加以发挥和强调。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李芒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第二本论文集《采玉集》(译林出版社,2000年) 中。作者把《采玉集》中的四十篇文章分为五个栏目:依次为“中日比较文学”、“古代日本文学”、“日本近现代短歌、俳句和汉俳”、“日本现代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翻译”,其中第一、三、五的栏目中的全部文章都属于歌俳研究的,占全部论文集的一大半,可见,李芒后期的日本文学研究的重心仍在和歌俳句。除了继续强调他在此前提出的一些观点主张外,这些文章还在两个方面有所拓展,一是中日诗歌的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栏目的几篇讲座稿中,作者对和歌、俳句与中国诗歌、芭蕉的俳句和杜甫的诗歌等做了比较的讨论,他表示不同意那种将芭蕉说成是日本的杜甫那样的比附方法,在该书“前言”中强调:比较研究“就是要分清中日两国文学的特点和相异与相同之处,为正确地理解和欣赏日本文学提供充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资料和参考观点”,在实际研究中,比起“求同”来,李芒似乎更倾向于“求异”,即通过比较揭示日本歌俳的独特的民族特点。第二个方面的拓展就是通过赏析文章、序文等方式,对日本近现代和歌、俳句,如石川啄木、上头火、赤松穗子、加藤耕子、宇咲冬男等的俳句创作做了更多、更深入的评介和研究。更值得提到的是,李芒在《日本短歌的翻译及汉歌——1998年4月初在中日两国短歌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汉歌”的概念,并说:“关于汉歌的创作,起步比汉俳的创作较晚,更是处于摸索阶段。大体一致的做法,是在字数句式遵循日本短歌的格律,比较普遍地采取押韵的方法……在形式方面无疑受到了日本短歌的影响,在艺术上也必然继承中国诗词的方法。”并提出自己的一首汉歌:“西天一片霞/胭脂红似梦中花/采撷趁仙槎/瑶台今夕尝佳果/蓬莱明朝问酒家。”这样的“汉歌”看上去很像是中国传统的长短句,是中国古词中早就存在的。尽管作者对“汉歌”的内容与形式上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没有展开论证,没有使“汉歌”特点突显出来,故后来和之者甚寡,但是提出“汉歌”的概念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李芒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关注歌俳及其汉译问题,并发表文章最多、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对此后和歌、俳句的翻译与研究、对汉俳的创作与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王晓平在《万叶集》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上也有突出成绩,他本人早年研究《诗经》,并学习日语,从而发现了《万叶集》和歌与《诗经》的关系并进入研究。1995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学者中西进的《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一书,从中西进的《万叶集比较研究》、《万叶史的研究》、《万叶和大海彼岸》、《山上忆良》四部著作中,选取了十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万叶集》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及《万叶集》反映的9世纪之前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本书大概是最早的一本中文版有关《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专门著作,对国内读者及研究者而言,有相当的启蒙价值和参考作用。这本书和两年后由石观海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辰巳正明著《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一道,成为中国读者窥视日本学界《万叶集》及其与中国关系之研究的窗口。十年后,王晓平和隽雪艳、赵怡合作翻译了另一个日本学者川本浩嗣的《日本诗歌的传统——五七五的诗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这是一部站在比较文学角度写成的论述日本歌俳及其特点(特别是体式和韵律上的特点) 的著作。
除上述的翻译作品之外,王晓平在日本和歌及中日诗歌比较方面的代表性的著作,是与中西进合著的《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中华书局,1995年)。采用“对谈”的方式著书,在日文出版物中颇为常见,这种著书方式的好处是不必过于顾及全书的体系建构,话题转换较为灵活,风格较为平易近人,可强化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也具备了这类书的优点。尽管是对谈,但没有失之于散漫,全书的主题是相对集中的,就是以《万叶集》及9世纪前的日本诗歌为中心,对中日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的描写,包括风花雨雪、日月山河、草木飞鸟等,都结合具体作品的赏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在这本书中,中西进将自己此前的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对谈的方式加以更为通俗易懂的表述,而王晓平则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对相关话题加以引导,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人的对谈可谓探幽发微、珠联璧合,通过跨文化比较和相互发明式的对话,表明从《万叶集》时代起,日本和歌借用中国诗歌中的意象,特别是自然意象,包括想象性的意象,以便更好地抒情表意,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了。作者不仅仅指出了这种现象,而且对这背后的文化背景、审美心理等都做了分析,在中日诗歌比较中,既见出两国文化的深刻联系,也反衬出两国诗歌各自不同的民族风格。
《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出版的前一年(1994年),梁继国的《万叶和歌新探——汉文虚词在万叶和歌中的受容及其训读意义》一书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运用比较语言方法对万叶和歌所作的独辟蹊径的研究。《万叶集》本来就是全部使用汉字作为标记符号(万叶假名) 来书写日语的。其中,汉字绝大部分作为纯粹的符号来使用,但也有一小部分是直接引进的汉语词,形音义兼具,因此,研究汉字与万叶假名的复杂关系,是历代学者解读《万叶集》的关键环节和必由之路。《万叶集》成书不久,由于假名的发明使用及语言的变化,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很难读懂了。在这种情况下,天历五年(951年),村上天皇授命五位学者(所谓“梨壶五人”) 对其进行初步训点,直到镰仓时代的1269年才出现了对它进行全面校对注释的著作,即学僧仙觉的《万叶集注释》。此后一直到17世纪江户时代所谓“国学”思潮的兴起,五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注释训读的有价值的成果。而在江户时代“国学家”契冲在《万叶代匠记》、贺茂真渊在《万叶考》等著作中,对《万叶集》进行训释,奠定了万叶和歌释义的基础。但是,那些江户国学家是站在弘扬日本国学、贬低中国文化的日本民族主义立场上进行《万叶集》训释的,他们千方百计淡化和漠视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因而有些观点和结论是不科学的。战后一批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科学的研究,基本解决了《万叶集》训释中的绝大部分问题。但是,梁继国认为,对万叶和歌的汉语虚词使用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他指出,在虚词方面,汉语和日语都没有词尾变化现象,因此,汉语虚词较其他词类更容易被日语所吸收和使用,换言之,日语与汉语最具关联性的主要是虚词部分,因而,研究万叶和歌中的虚词的使用及其变化过程,是研究《万叶集》吸收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的线索。鉴于此,他在该书中对四十多个副词、二十多个助词、十多个助动词在万叶和歌中的使用做了考察,对其中的“同音多词”、“一词多训”、“呼应现象”等做了辨析,对汉语虚词在万叶和歌中被赋予的“新意”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对有些汉语虚词重新释义的必要与可能。他强调,在万叶和歌中,有些汉语虚词不仅仅是作为表音符号来使用,而且也与古汉语中的意义、用法有深刻联系。在万叶和歌中,许多汉字虚词,如“太”、“胡”、“当”等。不仅仅用作表音,他在汉语中作为虚词的意义、用法常常被保留,具有表音兼表意的双重作用,而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对有关和歌作出更合理、更合逻辑的释义。尽管作者的观点在相对保守的日本《万叶集》研究界不一定轻易被接纳,但这种大胆立论、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还有从语言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中国学者万叶和歌研究中独树一帜。
自1990年代中期《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万叶和歌新探——汉文虚词在万叶和歌中的受容及其训读意义》问世之后的十几年间,用中文撰写并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有分量的关于《万叶集》研究的著作很少见。200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雨珍著《〈万叶集〉的世界》一书,分“前篇—— 《万叶集》中的主要歌人及其作品”和“后篇——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两部分,是一部对《万叶集》的内容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加以祖述的书,对于读者系统了解相关知识应该是有用的。但其中的许多段落与论述,与已有的研究成果大体相同,如后篇的第六章《〈万叶集〉与汉语》,从观点到材料(包括举的例子) 许多是来自日本学者中西进在《智水仁山》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可惜作者却未做注释和说明,该书还有极为严重的文字上的错误(如第179—180页)。此外还有张继文著《日本古典短歌与唐诗的隐喻认知研究》(日文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等,单篇论文中,有吕莉的论文《“炎”考:关于万叶集第48首歌的探讨》(《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西渡”考:关于万叶集第48首歌的探讨》(《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第4期) 等文章,都有自己的特定视角,着眼于微观的比较分析和出典研究,不避琐屑,以细致见长。
在俳句及其中日比较方面,杭州大学的陆坚与日本学者关森胜夫合作撰写的《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该书副标题文法上稍有不通) 是1990年代值得注意的成果,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者与日本的俳句专家合作研究的结晶。该书在形式上独具一格,全书选出芭蕉俳句一百多首,每首都作为相对独立的一节,先列出日文原作,在原文之下注明该句的季语为何,之后依次是“汉译”、“引评”和“备考”三部分。其中,汉译的方法一律使用俳句原有的“五七五”格律,有些译文相当成功,如第八首,芭蕉的原文是“花ううき世我酒白く食黑し”,汉译为:“世道忧心头,浊酒淡饭解我愁,赏花人如流。”又如第六十一首,原文:“初しぐれ猿も小蓑をほしげ也”,汉译为:“初冬时雨期,猿猴也要小蓑衣,朔气冷凄凄”,都十分传神,富有俳味。汉译之后是“引评”,对该首俳句的写作背景、含义加以解说,并提出主题、题材或意境上相关的中国古典诗歌,加以比较研究,或提出并分析芭蕉可能受到的中国诗歌影响,或做平行对比,并在比较中加以评论和鉴赏。最后是“备考”,补充一些“引评”中插不进去的内容,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知识与资料。在陆坚执笔的全书“前言”中,对芭蕉俳句及其与中国古典诗词在意境、炼字、通感等方面的相似与关联,也做了总体论述。总之,这是一部属于以细读、细品为特征、带有研究性质的赏析之作,具有工具书与专门著作的双重价值,同时,也没有同类著作中的咀嚼过细、嚼饭哺人的过度阐释,而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点到穴位,关乎痛痒,可谓恰到好处,对于从作品出发理解芭蕉俳句及其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联,颇具参考价值。
进入21世纪后,对和歌俳句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作者和新成果。
首先,出现了相关的学术组成。2000年,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会”,会员达到六十多人,由刘德有任会长,并主编出版了《中日诗歌研究》第一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和《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3年),收入中日两国学者、作者的相关论文及作品多篇,是一个相当好的交流园地,很可惜这样的不定期出版的学刊此后似乎未得为继。
其次,中日诗歌比较研究的文章与著述陆续出现,平均一年约有两三篇,虽然不多,但也不绝如缕。其中,有的文章承续1980年代上半期关于和歌、俳句汉译的话题,继续进行探讨,如宿久高的《和歌的鉴赏与汉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1期)、佟君的《俳句汉译的形式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有的文章论述松尾芭蕉及俳谐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如郑宗荣的《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句的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吴波的《日本禅宗文化影响下的古典俳句诗探析》(《南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唐小宁的《松尾芭蕉俳句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分析》(《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0期)、齐金玲的《松尾芭蕉俳谐作品中汉诗的点化》(《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12期)、郑腾川的《管窥芭蕉俳句之中国文化因子》(《集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有的从“意象”表现为切入点做中日诗歌的比较,如刘海军的《从月意象看中日古典诗歌审美差异》(《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曹颖的《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8期)、邹茜的《松尾芭蕉俳句中的三种花意象》(《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万芳的《日本古典和歌中“雪月花”的美意识研究》(《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3期);有的从色彩的表现来研究俳句的审美特点,如钱国英的《论俳句中色彩语的审美效应》(《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等。
尹允镇、徐东日、禹尚烈、权宇四位教授合著的《日本古代诗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共30万字,从上古时代的《万叶集》开始谈起,到《古今和歌集》以及近世俳谐。论述了日本在上古、中古、中世、近世的日本诗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关系,涉及到“记纪歌谣”、《万叶集》、汉诗集《怀风藻》和“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五山汉诗,连歌、俳谐、近代汉诗等日本诗歌的主要样式和重要作品。通过文献资料的引用和作品文本细读、分析,列举了日本诗歌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包含的中国要素,将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指出中国文学对于日本诗歌的深刻影响,包括主题、题材、意象、构思、修辞手法等方面对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借鉴与吸收。撰写该书的四位教授都是朝鲜族出身,本身也精通朝鲜文学,这本书的特点也主要体现在把中日诗歌关系纳入中日韩东亚文化圈的视野中进行研究,指出了朝鲜半岛在中日诗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津梁作用,并随时将三国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具有自觉的东亚区域文学的视野。书中涉及到的问题较为全面,具备了史的线索与构架,但显然还不是全面的中日诗歌关系史的研究。或许由于立意角度或材料的限制,有些重要问题未能纳入研究范围,如第四章第二节“近世和歌论与中国文学”,对于近世和歌论的重要理论家及其歌论著作,如贺茂真渊的《歌意考》、荷田春满的《国歌八论》、本居宣长的《石上私淑言》、香川景树的《〈新学〉异见》等歌论经典著作及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或一语带过,或没有提及,这对“近世和歌论与中国文学”这一论题而言是一个缺憾;第三章第五节“连歌、小歌与中国文学”,没有对日本连歌与中国“联句”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第四章第四节“近世俳谐与中国文学”也没有就中国的汉代以后的“俳谐诗”、“俳谐文”等与日本“俳谐”这一概念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应有的分析。但无论如何,该书作为一部严肃的、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是有一定的创新价值的。
2006年,西北大学外语系日文专业的高兵兵(1967年生)《雪·月·花——由古典诗歌看中日审美之异》(三秦出版社,2006年) 是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实改写而成的15万字的小册子,是一个在内容上有一定关联性的多篇文章的结集。该书在冠于卷首的《汉诗与和歌之间——代序》中认为,以往对日本汉诗文的研究,过多强调的是中国六朝及唐代文学的影响,“这是基于日本人追踪溯源的立场,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同时又不免有其片面性。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日本创作的汉诗、汉文,与中国文学之间,只能说是形似。在本质上,日本汉诗反而与和歌更为神似,而且日本汉诗与和歌的许多的共同点都与中国文学相异”。基于这一认识,作者主要从求“异”的角度,展开中日诗歌的比较分析,强调中日文学的本质区别,这种立意显然是可取的。作者主要以“花”为中心,论述了日本文学对“白色”描写的偏好,又分析了中日诗歌中“残菊”、“莺花”意象表现的不同,还举例式地对中国诗歌与和歌进行平行比较,包括李清照与紫式部笔下的“梅花”、中日古典诗歌中的“以花插头”题材。该书在结构与言说方式上,深受日本主流学界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全书没有体系构架,选题细小,对文本的细微之处做了细致赏析,但作为学术论著,特别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在“论”上较为乏力,其思想的含量、理论的展开、分析的深度都相对缺乏。作为全书核心结论的“日本人及日本文学‘偏好白色’”的问题,也是日本学界早就有的定论,例如,中国人较为熟悉的今道友新的《东洋美学》中就有论述。但即便如此,该书作为高雅的普及性学术读物来看,是可取的、有益的。
这方面的普及性读物还有数种。其中,郑民钦编著《和歌的魅力——日本名歌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以春夏秋冬四季为题,选取古典和歌200多首加以赏析;刘德润、孙青、孙士超编著《东瀛听潮——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和歌与俳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选取60多人的短歌148首,50多位俳人的俳句157首,共305首加以赏析。刘德润编著《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年),对日本传统上类似中国的《唐诗三百首》的著名选本《小仓百人一首》,有日语原文、日语现代语译文、重点词语解释、作者简介、鉴赏几个部分,对日语有基础的和歌爱好者是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科教师铁军、潘小多、王静、施雯合著《日本古典和歌审美新视点——以〈小仓百人一首〉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按题材将《小仓百人一首》重新加以分类,其中包括爱情歌、咏月歌、山水情结、原野情结、春夏歌、秋歌、冬歌、动物昆虫歌、自然现象歌、花草木歌、作者、技巧十三类,并对同类作品加以整体赏析与研究,虽然分类标准并不统一,但对了解和歌的传统主题与题材是有助益的。早早(张春晓)的《东瀛悲歌:和歌中的菊与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一书,采取“以诗证史”的方法,以名歌介入日本历史,分为“武家卷”、“战国卷”、“风月卷”、“怨灵卷”、“宫闱卷”、“风雅卷”,讲述历史事件,分析日本历史人物、呈现民族文化心理,将学术随笔与和歌赏析融为一体,在构思写法上别具一格。
第四节 郑民钦等的歌俳史研究
专题史著作的出现,常常是某一学术领域得以形成的标志,也是学术研究体系化的表征,对于中国的和歌、俳句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在中国,最早为日本的和歌、俳句写史的,是上海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彭恩华(1944—2004年) 教授。
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是由中国人编写、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日本俳句史专著。为中国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俳句的历史发展演化的过程,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书。据彭恩华在该书序言中自述,该书原稿完成于1966年,字数约40万左右,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散失无遗,改革开放后重写。虽然篇幅只有16万字,但以时代为经,以俳人为点,对从古至今各时代俳人的佳作及俳论都有较为简要而又具体的评析,尤其是最后一章论述俳句在西方各国及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可以见出俳句的国际性。在日本,俳句史方面的著作很多,用中文撰写俳句史可以参考日本的同类著作,从资料上看照理说不算很难,但最困难的,是要将大量的俳句译成中文之后,方可称为中文版的俳句史。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涉及到俳句原作上千首,因此,俳句史的写作最重要的其实在于俳句的翻译。彭恩华有其自己固定的翻译方法,就是将“五七五”格律的俳句,译成五言体两句或七言体两句,多数采用五言的句式。在用词上基本上与原作相当,一般不用额外添加原文中没有的词,同时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俳句的“五七五”的形式则被淹没了。作者用这种方法,译出了古今俳句名作一千首,并且以日汉对照的方式,作为附录附于书后。所以说,《日本俳句史》不仅是一部俳句历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有特色的俳句译作集。如松尾芭蕉的“草の叶をおつるよりとぶほたる哉”,彭译作“流萤翩翩舞,起落草叶中”;芭蕉的“送られつ送りつはては木曾の秋”,彭译作“君送我兮我送君,往来木曾秋气深”。宝井其角的俳句“虫の音の中咳き出すねぎめかな”,彭译作:“咳嗽梦惊醒,人在虫声中”等等,均能达意传神。
1986 年,彭恩华又出版了《日本俳句史》的姊妹篇《日本和歌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这也是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日本和歌史的著作。其写法与俳句史相同,仍使用以陈述史实、赏析作品为主、以介绍歌人为中心的写作方法。在1980年代,中国一般读者对和歌还很陌生的情况下,这样的书,这种写法是必要的,也是很有用的,也为中国的和歌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参考。全书依次论述“记纪”歌谣、《万叶集》、以《古今和歌集》为中心的平安朝和歌、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中心的镰仓朝和歌、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和歌、江户时代的和歌、明治与大正时代的和歌、昭和时代的和歌,并附录《古今和歌佳作一千首》(日汉对照),其译文大多采用七言两句的古诗句式,整饬而又雅致。可以说,在以古诗句式翻译的和歌译作中,彭恩华的两句译案与杨烈的四句译案,代表了“古诗派”翻译的两种主要形态。
1996年,马兴国先生的《十七音的世界——日本俳句》的小册子(上、下两册,共14万字) 作为“世界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印制相当粗陋,但作为知识性的读物,也不乏学术价值,内容颇为可取。全书分为“俳句的产生及发展”、“古典俳句与松尾芭蕉”、“近代俳句与正冈子规”、“当代日本俳坛”、“俳句规则”、“俳句与禅文化”、“俳句与中国”、“俳句与世界”共八章,对俳句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梳理、评介和分析,与上述彭恩华的歌俳史以歌人、俳人为单位的纵向评述的写法有所不同。特别是最后三章,不仅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资料,而且也有颇得要领的分析。例如,“俳句与文化”一章,借鉴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等人的看法,对禅宗东传及如何影响日本的自然观乃至人生观,对松尾芭蕉作品中的禅意禅境,特别是芭蕉的“寂”与禅宗思想的关系做了分析。但马兴国仍沿用此前彭恩华等的译法,将“寂”(さび) 译为并理解为“闲寂”,显然是将这个词的内涵缩小了,也进一步限定了一般中文读者对“寂”作出的“闲寂”的理解。“俳句与中国”一章,对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正冈子规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介绍和分析,对俳句在中国的译介及汉俳的诞生做了评述,都不乏参考价值。
此后不久,北京大学的王瑞林编著的《日本文化的皇冠宝珠——短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一书出版,全书共分“短歌的起源”、“短歌的历史”和“短歌赏析”三章,既有和歌起源与历史沿革的梳理,也有名家名作的原作、翻译及鉴赏分析,对一般读者而言,是一本内容系统、通俗易懂的和歌知识入门书。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歌俳史研究更上一层楼,而登楼者就是日本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郑民钦(1946年生)。
2000年,郑民钦《日本俳句史》由京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内容系统翔实、资料丰富、富有学术性的日本俳句通史。日本的俳句史类的著作非常多,但很多的书流于堆砌材料和句作赏析,郑民钦的这部史充分吸收借鉴了日本同类著作,但是同时自觉突显中国学者的学术追求,写成了一部贯通古今、有史有识的俳句史。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作的立足点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历史,力图表现个性,即自我见解。要做到不落窠臼,有所创新,实非易事。在占有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了解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披阅爬梳,去粗取精,吸收营养,自成机杼。当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在研究过程中的确觉得有自己的话要说,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体会。”统观全书,对这些,作者都完全做到了。写史除了掌握充分史料外,关键是要有“史识”,要有史家自己的文化立场、学术理念和独到的鉴别分析,这就要将史料与史论结合在一起,《日本俳句史》最大的特点是史论结合。作者无论是对俳句史的叙述,还是对俳人创作的分析,都在史料的使用中渗透着透辟的理论分析,从而形成了一种叙述张力,使读者在阅读中不但能体会到求知的快乐,而且能够享受到思维与思想的快感。一般受日本式思维影响过重的中国学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传统日语特有的那种拖沓绵软的表述、缺乏理论思辨的写生式的表达,而郑民钦的书,却通篇充满着中国学者的阳刚文气,处处可见透彻的评论与辨析,这是十分可贵的。这样写出来的《日本俳句史》虽然篇幅不小(34万字),读之却不觉得疲沓,急欲读毕而后快。例如,在第四章介绍小林一茶的创作的时候,作者写道:“在近代俳句史上,一茶与芭蕉、芜村齐名,但三人的风格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各不相同。芭蕉为俳谐正风之祖,把俳句升华为真正的文学、走进艺术的殿堂。他的理论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芜村是中兴俳坛的第一人,对俳谐的复兴和天明时期的新风的树立做出光辉的业绩。而一茶处在俳谐相对衰退的时期,又离开江户,回到家乡定居,他的独具奇特魅力的句风未能被世人理解,没有得到社会上的承认,在俳坛几乎没有影响。……一茶属于‘生前寂寞生后荣’,在他死后,人们才认识到他的俳谐的真正价值。那种充满泥土气息的、极具个性的作品给芭蕉、芜村以后沉滞、衰竭的传统风雅观注入野性的血液……”全书几乎通篇都是这样的以史代论、夹叙夹议的写法。假如没有对日本俳句史各方面知识的熟稔于心与融会贯通,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2004年,郑民钦在《日本俳句史》的基础上,将俳句与和歌熔为一炉,出版了《日本民族诗歌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全书68万字,这是一部厚重的著作,评述了一千多年的和歌和六百多年的俳句的发展历史,从和歌的萌芽时期的记纪歌谣写起,到《万叶集》时代、《古今集》时代、中世《新古今集》等,到连歌、连句、俳句、川柳、狂歌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做了系统的评述,特别是对近现代短歌、俳句用了占全书一半的篇幅加以评述,指出了和歌、俳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发展及其困境。在写法上仍然采用《日本俳句史》那样的以史代论的方法,但由于将和歌、俳句作为一个日本民族诗歌的整体加以处理,在内容上更为条贯,更能强化历史的纵深感,对一些问题上的思考与表述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和歌论、俳论纳入,并分专门章节加以评述,对各家理论观点做了分析阐释,从而将和歌、俳句史写成创作与理论相辅相成的历史。这更强化了该书的理论色彩和学术思想含量。因而,可以说该书不但是日本民族诗歌发展演进的历史,也是从诗歌角度切入的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历史。当然,一般而论,理论问题涉及越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对也就越多,该书也不例外,例如,第五章“和歌理论”,以“余情”、“幽玄”、“有心”三个概念为中心,论述了中世纪和歌理论的概貌。但作者对三个概念是并列论述的,没有加以逻辑层次上的厘定和划分,若站在日本美学和文论的发展史上看,“幽玄”应该是中世和歌理论的最高概念,而“余情”、“有心”等,应该是“幽玄”的从属概念;第九章谈到松尾芭蕉的俳论的时候,将“风雅之诚”论作为芭蕉俳论的最根本审美概念,实际上,“风雅之诚”就是“俳谐之诚”,重心在“诚”字上,而这个“诚”作为文学真实论,早在芭蕉之前的古代文论中就被反复强调过了,这是日本文论的一般概念,与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中的真实论相比,也缺乏理论特色。对蕉门俳论而言,真实论即“风雅之诚”论似乎并不是芭蕉俳论的核心,更不是芭蕉俳谐美学的最高理想,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寂”,关于这一点,大西克礼等现代日本美学家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论证。再如该书第九章第六节“松尾芭蕉的俳论——寂、余情、纤细”中,将“寂、余情、纤细”三个概念作为并列的概念加以论述,实际上,对蕉门俳论的内在理论体系加以细致考察就会看出,“余情”和“纤细”(或译为“细柔”) 只是“寂”的次级概念,是“寂”的具体化表现。另外,第四章第四节“平淡美与极信体的理念”,在标题中出现了“极信体”这个令人困惑的词(抑或概念),而在该节正文中却没有使用这个词,更没有做任何解释,不知是出于印刷错误还是别的原因。不过,另一方面,任何一部好的学术著作都不是一劳永逸地向读者呈现真理,而是启发读者去思考真理、追求真理,《日本民族诗歌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一部面向中国读者的专题文学史,填补了和歌俳句整体纵向研究的一个空白。可以说,这样高水平的著作,在日本同类著作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显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化与文学的钻研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郑民钦在理论上的追求,使得在和歌理论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聚焦和系统化,于2008年出版了《和歌美学》(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丛书”) 一书,该书是在上述两部书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以和歌美学的重要范畴,以20万字的篇幅,分九章分别对“抒情”、“物哀”、“心·词·姿·实”、“余情”、“幽玄”、“有心”、“风雅”、“优艳”、“无常”这些范畴和概念做了分析。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和歌美学的著作,在日本,以“和歌美学”为题的著作似乎也没有,因而又填补了选题上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有价值而又相当困难的选题。关于日本古代文论与美学,日本学者虽然做了大量研究,但或许是由于偏向情感思维而不善理论思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集体无意识遗传的影响,除大西克礼等少数学者外,大部分日本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缺乏深度感和思辨力。因此,要对和歌美学的历史轨迹、特别横向的结构体系加以建构,可资参考的成熟的著作并不多,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和歌美学》的立足点在“和歌”,而不是“美学”本身,是从文学批评的、文艺美学的角度对历代和歌论与和歌的审美内涵所做的分析,作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基于和歌作品的分析来印证相关的范畴和概念,而不是用美学思辨的方法,对概念和范畴的内在理论逻辑加以寻绎并加以美学体系化。《和歌美学》一书的特点和局限都在这里。作者第一次对和歌美学——它占据了日本传统美学的半壁江山——的基本范畴,结合和歌史和歌论史做了动态的梳理,为中国读者系统了解这些独特的审美范畴提供了知识与参考。但是,由于对这些概念进行相对孤立的分别论述,因而对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清理就受到削弱。同时,对属于和歌的独特的审美概念,和那些不仅属于和歌的一般的思想性、宗教性概念,也未能加以严格区分,例如,第一章“抒情”,将“抒情”这个一般词汇作为和歌概念来处理,就显得勉为其难,导致这一章的分析论述很一般化。再如,第九章“无常”所论述的“无常”,是来自佛教的日本人传统的世界观,当然也与审美观相联系,但无论如何不是和歌独有的概念。第八章的“优艳”,实际上在歌论中最经常地写为“艶”(えん),“艶”有时候训读(解释为)“优”(やさし),但“优艳”作为一概念的使用是很少的,倒是“妖艳”一词更常见。总之,《和歌美学》作为开拓性的著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一些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思考提供了一个参照和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