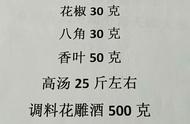放到手里,是孔乙己对伙计的尊重,而那四文大钱的重量,就是20年后伙计再次想起这件事时,悔恨情绪的重量。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鲁迅安排伙计在20年后再次回忆孔乙己,就是想让伙计通过构建回忆来达到自我救赎。
然而,在回忆的结尾,孔乙己还是消失了,伙计意识到自己也同“短衣帮”一样对孔乙己的“消失”(伙计猜测孔乙己是死了)负有难以逃脱的责任,自我救赎相当于失败了,忏悔情绪油然而生。
什么是忏悔?
一种无法弥补的罪恶——由于你的过失,做错了一件不能挽回的事情。忏悔里面不仅有悔过、有反省,还有一种无以挽救的苦痛。
这种意识到自身错误——救赎——忏悔的模式,就是鲁迅写小说的惯用手法,在小说人物的忏悔中,掺杂着鲁迅自我的反省以及对人性的深思。
孔乙己的结局——门槛的暗示在《孔乙己》的结尾,鲁迅写到: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孔乙己真的死了吗?
不!
很可能孔乙己只是离开了鲁镇。

在回忆中,伙计最后一次见孔乙己,有这样一段描述: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注意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点:“门槛”与“蒲包”。
先来说“蒲包”,孔乙己腿折了,那么为了行走,在腿下垫一个蒲包挂在肩上,防止腿磨伤,这似乎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残疾人的真实写照,是写实的。

但是,“蒲包”本身也具有象征的意义,是出门远行必备的行囊。
当然,仅凭此就猜测孔乙己离开了鲁镇是有些牵强,但考虑到“门槛”这个词,情况就不一样了。
请再注意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是继《狂人日记》后的第二篇。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曾多次发声如果想要摆脱吃人的罗网,只要肯跨过“一条门槛,一个关头”就足够了。

而在《孔乙己》中再一次提到“门槛”,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伙计把酒放在孔乙己坐着的门槛上,那最后一碗酒,相当于鲁迅借伙计之手给孔乙己安排的一碗践行酒——致敬他跨过了“门槛”。
有人会问,“断腿”的孔乙己为何要离开鲁镇,鲁迅又为何要如此安排?
这就要结合鲁迅的生平了。
对于鲁迅来说,他极为理解(不仅仅是同情)被流言中伤的孔乙己。
在《琐记》中,鲁迅曾自述过童年的一段遭遇:
“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当时的鲁迅与小说中的孔乙己的状态是一样的,面对流言的攻击,无力解释,也没法辩白。
流言是事实吗?
不是。
可不是事实的流言,却会让听到的人产生“应该有、可能有、也许有”的猜测,而这种猜测就相当于给一个人泼上了抹不掉的黑油漆。
最终在流言袭身下,鲁迅作出的选择是:
“好。那么,走罢!”
由此鲁迅离开了故乡,在愤恨中踏入了学堂。流言的流弊,是鲁迅一生难以释怀的恨,也因此鲁迅会大骂流言“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出自鲁迅《并非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