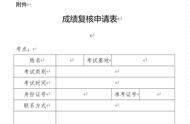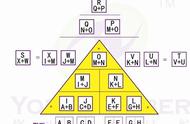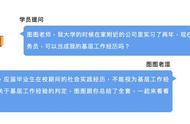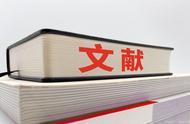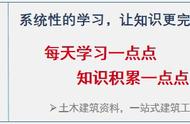摘要:程颐“敬”论的“主一”说,由于缺乏文字训诂的支持而被以段玉裁为代表的考据家所质疑。段玉裁认为程子以“主一”说“敬”源于《文子》,而实际上程子更可能从《论语》“无适无莫”中得到“无适之谓一”的启发。无论是理学家自身的论述,还是现代学者对儒家宗教性维度的探究,都指出将“主一”与“敬”真正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斋戒时的精神体验。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也可以看出,“敬”的心态内在于祭祀斋戒的发生与发展之中。这些都表明,程颐所开创的对“敬”思想的新理解,建立在超越训诂的工夫诠释学之上。
关键词:主一无适;敬;祭祀斋戒;工夫
在理学“敬”论的诸多释义中,“主一无适”居于核心地位。然而“敬”在一般的语境中被理解为对某个对象的尊敬,因而“主一无适”这种关注自身的无对象的心理状态,为何可以被看作是敬的内涵,已经不易被人所了解,更不必说作为核心含义了。学界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应该说还没有较为深入地揭示“主一之谓敬”的思想根源。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看,以“一”说“敬”似乎没有根据。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便反对以“主一无适”言“敬”,认为“主一”与“敬”字本义无关:
敬,肃也。肃部曰:肃者,持事振敬也。与此为转注。心部曰:忠,敬也。戁,敬也。憼,敬也,恭肃也。憜,不敬也。义皆相足。后儒或云“主一无适”为敬,夫“主一”与敬义无涉,且《文子》曰:“一也者,无适之道”;《淮南·诠言》曰:“一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适即敌字,非他往之谓。敌,仇也。仇,讎也。《左传》曰:“怨耦曰仇。”仇者,兼好恶之词,相等为敌,因之相角为敌,古多假借适为敌。《杂记》“讣于适者”,《史记》“适人开户”“适不及拒”,《荀卿子》“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文子》曰“一也者,無敌之道也”。按后人取《文子》注《论语》曰“敬者,主一无适之谓”,适读如字。夫主一则有适矣,乃云无适乎?敬者,持事振敬,非谓主一也。《淮南书》曰“一者,万物之本也,无适之道也”,与《文子》同,正作敌。1
段玉裁的批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主一”与敬义无涉,这是说“敬”字的训诂如“恭”“肃”等已经充分,与“一”无关。这是反驳“主一之谓敬”。二是通过指出程子以“无适”解“一”是依据《文子》,而《文子》中“适”的原意是“匹敌”而非“他往”,说明“无适之谓一”是错解,也有瓦解程子工夫解说的意味。由此,段玉裁似乎从整体上推翻了程颐“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的说法。若此说成立,那么理学最重要的工夫论之一的“主敬”就是建立在错误的训诂之上,这对于整个理学大厦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回应段玉裁的质疑。
一、无适之谓一”源自《论语》而非《文子》适,往也,一般认为无适就是无所往。伊川曰“一则无二三矣”(一作“不一则二三矣”),二、三便是往;还有一处曰:“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2无适无往,便是不之东西彼此。适,一般也就是训作“往”的,例如《诗·郑风·缁衣》“适子之馆”,朱子便训为“之”,之也是往的意思。3但是以无适、无往来解“一”,却并不常见。当然,以与无往相近的含义来解“一”的例子的确不少。例如以专一、精专来训“一”,就是古书中很常见的说法。无适、无往,当然表达的就是专一的意思,但是伊川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说“专精之谓一”,而是说“无适之谓一”,他这样说有哪些特殊的考量或意义呢?
实际上,《文子》并非如段玉裁所说是程颐“无适之谓一”说的来源。关于以无适解“一”的来源,吾妻重二也认为与《文子》有关。《文子·道德篇》有“一也者,无适之道也,万物之本也”,唐人徐灵府注曰“一者法也,适者往也”,吾妻氏以此来证明“这个解释与程颐及朱熹的解释一致,这说明了道学的敬之说并没有完全游离于传统思想”。4看起来伊川的说法与《文子》很相近,但如上文引段玉裁所说,《文子》原文乃作“无敌之道”,与所往无关。徐注的完整版是“一者法也,适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则万物皆归往于君,故无不适也。”这里,徐注解“无适之道”的意思反而是无不适,而不是无适,颇令人费解。《文子疏义》引于大成曰:
此注大谬,“适”即“敌”字,此用《淮南·诠言篇》文,淮南正作“敌”。《吕氏春秋·为欲篇》“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圣王托于无敌,故民命系焉。”(今本《吕氏春秋》“系”作“敌”,从陈昌齐说改)《淮南·齐俗篇》作:“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圣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本书《下德篇》用《淮南·齐俗》文,字亦作“适”。5
可见此处本义与“无往”无关,而是无敌,无所匹敌的意思。可见,吾妻重二引徐注只能证明程子以“往”训“适”是渊源有自的,但并不能说明在《文子》的语境中“无适”本身就是无往的意思,也不能证明程子以“无所往”解“一”与《文子》有关,更不能证明这个解法符合先秦的古训。因此《文子》显然不是伊川“无适之谓一”的来源。
其实,先秦典籍中,不只《文子》,《庄子》中也提到“无适”,《齐物论》便有“无适焉,因是已”的说法。成玄英疏曰:“自,从也;适,往也。”这里的“适”不可能解为“敌”。道通为一,而做到“一”的关键便在于无适之因。当然,这里重点在于“无”其“适”,在于对“适”的否定,而并非主要以“无适”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但这里的“无适之因”是直接与“一”相关的。因为庄子主张“道通为一”,要做到这样的“一”,就不要有所“适”,不要自无适有,自有适有,适人之适。无适之因便是尊重物自身本来的样子,不离开事物自身来观察、理解与评价。这样的观点,在理学看来,便是“物各付物”。尽管庄子这里的说法确实有可能启发了伊川,但庄子所谓“自适其适”的说法,却容易使学者追求安乐惬意,而忽视严谨的道德训练。这不符合伊川的个性。
熊禾《勿轩集》卷六有《适堂说》,对“适”的问题颇有关注:
《书》曰“惟我事不贰适”,《易大传》曰“惟变所适”,此周公孔子之言适也。不贰适者,谓此心当一于其所往,而不可以有间也。先儒“主一无适”之旨,盖起于此。“惟变所适”,则虽千途万辙,皆可适之地,而我之心固未尝不一,而初未始有适也。又岂即其安者之所可得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所适者固在乎道,此道也,秦汉而下盖无传焉。6
熊禾关心程子以“无适”说“一”的来源问题,认为《多士》“惟我事不贰适”是程子说无适的来源。按照熊禾的说法,三代以上,所适者只有道,孔子也说“适道”,所以无适的意思只是“无他适”“不二适”,并不是要彻底无所往,只是所往的对象要是道而已。只要是适道,“唯变所适”亦无妨。因此,伊川使用“无适”二字的直接来源,恐怕还是来自于儒家典籍。
《论语·里仁》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这里的“适”也是“敌”。郑注皇疏皆作“敌”。朱注曰:“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7《语类》中也有相关的讨论,其中朱子对伊川的注释有所批评。伊川《论语解》曰:“君子之于天下,无必往也,无莫往也,惟义是亲。”8可见伊川是以“往”来解“适”的。尽管以“往”训“适”并不罕见,但的确不符合此处的解释传统。朱子认为“此章诸说多误,盖由音读之学不明,以‘适’为‘子适卫’之‘适’之故也”。9在《论语或问》中,朱子虽没有明点程子,但大概还是针对程子之说的。因此朱子认为伊川的“无适”与此处无关。
伊川以“往”解“适”,他的弟子们却多不如此说。只有范宁与之比较接近:“无适故无所就,无莫故无所去”。10但是可以比较直接地看出来的是,“无适之谓一”,与君子无适无莫还是有关系。适和莫,无论是敌慕,还是厚薄,还是亲疏,还是可与不可,都是有所分别,有所偏倚,都是二,而不是一。因此相反,无适便是没有意必,没有偏倚,便是一。正因为无适无莫的这种含义,早期佛经翻译中,就经常使用“无适莫”“无适无莫”等语词。有所偏倚,有适有莫,便离开了一,也就离开了道,所以程子说“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11,这是二程首要考虑的,而具体的这里的“适”和“莫”是什么意思,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适”与“莫”形成一个对立,有这样的对立,这才是二程比较关注的。朱子《集注》独称许上蔡之说,引上蔡曰“然则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可见无适无莫,君子之心不应有所倚。
二、以“一”说“敬”并非文字训诂以上我们证明了《文子》的说法并非伊川“无适”说的来源,相比于碰巧用字相同的《文子》,《论语》“无适无莫”一段在义理和学统上更具可能性。尽管段玉裁的反驳站不住脚,但我们也只是证明了“无适之谓一”有文献和义理的基础,“敬”之训诂与“一”无关的疑难仍未解决。
“敬”之古训有很多,《尔雅·释诂》说“俨,恪,祇,翼,諲,恭,钦,寅,熯,敬也”,《释名·释言语》曰“敬,警也,恒自肃警也”。这些古训,理学家是完全知道的,例如吴澄说“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也。释其字义,曰钦、曰寅、曰祗,由中而外,曰恭、曰庄、曰肃”,12胡居仁《居业录》卷二也说“古今圣贤说敬字,曰钦、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惧、曰战兢、曰斋庄,字虽不同,其实一也”13。但的确如段玉裁所说,即使遍览《故训汇纂》,也查不到除了程朱以外有以“一”来训“敬”的。而且,从这些训释也难以推论出“一”的内涵。例如,“钦”主要训为“敬”,《尔雅·释诂下》曰“钦,敬也”,《尧典》有“钦明文思”“钦若昊天”之说,又经常有“钦哉”之警训,但“钦”字本身没有专一的意思。其他含义如“严也”“重也”“忧也”,也与“一”无关。同样,“寅”主要也解为“敬”,《尧典》有“寅宾出日”,《舜典》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无逸》有“严恭寅畏”,《多方》有“弗永寅念于祀”等等。其他含义,例如《广雅·释言》《白虎通·五行》《释名·释天》都有“寅,演也”,又作为星辰之名,象征东方,因此主要用在律历中。这些内容看不到与“一”有联系。“恭”“庄”“肃”“戒惧”“战兢”“斋庄”的情况与此类似。《论语》中出现“敬”的地方也很多,也都没有明显地以“一”来训释。
另一方面,陈来先生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指出:“所谓主一,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如《管子》《荀子》)关于‘一’的思想,在认识上包含主体修养的内容,在心理学上即所谓有意注意的问题。”14先秦思想家论“一”处甚多。《老子》有“抱一以为天下式”等说法,并为《管子》《庄子》《文子》所大量阐发;儒家思想中,孔子有“吾道一以贯之”,荀子论“一”也甚详。《诗经》中有“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曹风·鸤鸠》),乃是先秦两汉儒学论“一”时非常喜欢引用的一段文字,朱子在《诗集传》中也从用心专一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以用心专一为工夫,孟子有“专心致志”,庄子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朱子也曾引用后者来说明专一。但尽管这里的“一”确实有工夫论和精神性的因素。但是,“一”还是没能与“敬”产生直接关联。我们要想把这些“一”与“敬”联系起来,还缺少一个关键的桥梁。
既然一方面“敬”的古训中没有以“一”说“敬”的,另一方面“一”的阐释中也没有直接联系到“敬”的,这就说明以“主一”说“敬”的思想根源并不来自文字训诂,而是程颐自己的独创。他之所以能得出这种创见,显然是由于对于经典采取了字义训诂以外的诠释方法,或从义理本身、或从工夫体验出发。吴澄《敬堂说》有“独程子摆脱训诂”之说,就点明了这种方法上的分判:
古圣人垂世之言,肇自唐虞,而典谟之书言敬者不一;商人周人之诗、周公孔子之易,继继言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下逮传记诸家之言,又累累及之。然惟商颂、周雅“圣敬日跻”“于缉熙敬止”两辞为以此赞咏汤文之徳,其余言敬各随所指,鲜或该体用之全而言也。夫子答子路君子之问曰“修已以敬”,所该则广矣。而子路曾莫之悟,反疑圣人之言浅近而不知其甚深甚远也。千数百年之后,程子始阐明之,以极于天地位、万物育,而读者亦或为之茫然。夫敬者人心之宰,圣学之基也。释其字义,曰钦、曰寅、曰祗,由中而外,曰恭、曰庄、曰肃,独程子摆脱训诂,而谓之“主一无适”,其开小学者之意至切也。15
按照吴澄的说法,敬字的含义在商周时代虽然广为传颂,然而从孔子的弟子开始,敬的内涵却已经晦暗不明。直到千年以后的伊川才摆脱了字义训诂的窠臼,重新解释了敬的最本质的内涵。因此,既然伊川以“主一”说“敬”的理由根本不是字义的训诂,那么我们也可以排除探究敬字古训的讨论方法,直接从义理本身来寻找其根源。
三、斋戒体验的工夫诠释学其实,对于儒家之敬的思想的起源,一般都会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寻找。因此这个将“一”与“敬”沟通起来的桥梁,或许也与祭祀活动有关。理学家经常把“敬”与斋戒的体验联系在一起。《朱子语类》中提到明道喜欢引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一句:
先生曰:“遗书录明道语,多有只载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无邪’,如曰‘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当时举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语至此,整容而诵“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圣人也要神明。这个本是一个灵圣底物事,自家斋戒,便会灵圣;不斋戒,便不灵圣。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斋。”胡叔器曰:“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斋较谨于戒。湛然纯一之谓斋,肃然警惕之谓戒。到湛然纯一时,那肃然警惕也无了。”义刚16
今检《二程遗书》,引用此句在卷六有一处,卷十一有三处,果真只载古人全句而不添一字。而且朱子整容而诵一段,亦颇具现场感,使人如身临其境。胡叔器点出了斋戒的根本在于敬,朱子是完全赞同的,只是补充说明斋与戒二者具有不同的侧重。朱子又说:
“明道爱举‘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虽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举之。幹问:“此恐是‘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谓‘敬是常惺惺法’。”又问:“此恐非是圣人分上事。”曰:“便是说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毕,再三诵之。幹17
这里朱子直接点出斋戒与常惺惺法有关,也就是敬。斋戒就是要用常惺惺法。虽说朱子又补充道不是“本文意思”,但斋戒既然有湛然纯一这种主一的精神状态,也并不能说就不是其本义。胡居仁在《居业录》卷三也对此评论道:“程子发主一之论,与易‘斋戒以神明其德’相同”,卷八曰:“易曰斋戒以神明其徳,程子主一无适是斋,子思戒慎恐惧是戒,合而言之敬也。”18可见胡居仁也是如此理解的。朱子说湛然纯一是斋,胡居仁说程子主一无适是斋,二者也是相合的。因为主一无适正可以达到湛然纯一的状态。子思之戒慎恐惧与肃然警惕也是相合的。
此外,尹和靖从伊川学,体验“敬以直内”,而他的体验也与斋戒祭祀有关:
祁宽问:“如何是主一?愿先生善喻。”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不着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19
尹焞以神祠中致敬的心态类比“主一”,可谓善喻。朱子很熟悉这一段,不仅总结为“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而且早年杨方所录的语录中也有与此内容相关。20朱子在解释萃卦的时候,也以“聚”己之精神来说:“庙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则可以至于庙而承祖考也。”21“敬,德之聚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聚己之精神显然与“主一”也有关系。袁燮也提到尹和靖的这个说法:
伊川谓“主一无适之谓敬”,尹和靖后来方晓得,谓入神祠中,此心不曾散失,不曾散失处便是主一,主一便是直,直则清。《记》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人岂可不清明?然茍不能敬以直内,则方寸扰扰,胸中蔽塞,何以能清?直则心无私曲,表里洞然彻底。如此清故,曰“惟敬故直,惟直故清”。22
可见,理学家对于“主一”与斋戒的精神状态的关联是有自觉的。斋戒是儒家的宗教性、精神性的集中体现。因此,“一”与“敬”之间的这个桥梁,或许就应该从祭祀与斋戒中寻找。
从祭祀与斋戒中寻找“主敬”工夫的根源,实际上也普遍为现代学者所重视。例如重视儒学的宗教性的学者,就容易发现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宗教维度的关联。例如李申认为,“程朱的新儒学,是把旧儒学仅要求在祭祀时所保持的敬畏心情,贯彻到时时刻刻,贯彻到一言一行,没有一时的间断。这是一种成熟了的宗教虔诚,远非那较为原始的、初期的宗教虔诚可比”。23但是这里只是泛泛地提到“敬畏心情”,未能从“主一”的角度对这种心情的意识状态进行剖析。这是因为他对祭祀的宗教虔诚评价不高,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但实际上,祭祀斋戒的特殊性在于其是礼仪生活中特别需要精神修炼的一个部分,以至于杨儒宾认为这是儒家工夫的主要来源。杨儒宾通过对《祭义》《祭统》等文献呈现所谓“恍惚的伦理”:
《祭义》……蕴含的天人之际工夫论的内涵确实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祭者在此段期间内要严守戒律,集中心力……斋戒所引致的身心变形以见鬼神之效果,乃是《祭义》篇的一大特色,这种祭祀宗教学的叙述在心性论大兴之后,没有受到重视,但斋戒确实有工夫论的内涵……《祭义》《祭统》诸篇……它们合构成儒家祭祀-斋戒论的工夫论内涵……由于祭典伦理要求阳世子孙需要观想、存念,以强烈的道德情感逼显先人的身影重现于斋戒的境遇,所以这样的祭典伦理也可以视为祭典的工夫论。一旦阳世儿女透过了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的精神集中过程,克服了与亲人死别的存有论断裂之不幸,伦理即可重得其伦。而在此重得其伦的过程中,主体的精神锻炼也完成了,“散斋”、“致斋”的祭礼可视孔子之前儒门颇有代表性的原始工夫论……这种筑基于观想作用的恍惚伦理在后世儒家的工夫论中确实不占重要地位,甚至说被遗忘了。祭祀还是重要的,而且始终是重要的,但进入圣的存在次元的模式基本上已被“主静”或“主敬”的工夫论所取代。24
杨儒宾肯定,无论是基于观想的恍惚伦理,还是主静或主敬,都是超凡入圣(所谓“进入圣的存在次元”)的手段,在这里二者是有一致性的。他承认这种一致性:“此处所言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大学》的‘定静安虑得’,也容易联想到‘主一之谓敬’的工夫,这种定、静、斋一体的工夫基本上都是经由意识的逆觉以体证更深层的本性。”而他想要强调的是二者的断裂,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宋明儒者的工夫论体系谱中,恍惚与已逝的亲人睹面相照此视觉意象的因素已不存在,至少是不重要了”。然而,表面上的断裂掩盖了深层逻辑的继承性。理学工夫论的确不再强调所谓视觉意象,但是视觉意象所以产生的原理及其对精神修炼的意义,应该说与后世“主一之谓敬”的工夫并无二致。相较而言,郑开也重视祭祀对于内在精神层面的感动与洗礼,尤其是唤起“神圣感”。25这种“神圣感”在内心就表现为“敬”的心态。
在诸现代学者研究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在祭礼,也就是祭祀活动中看出“专一”的重要性,看出“主一”如何成为“敬”的本质意涵。依据《祭义》等文献,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对祭祀斋戒的精神状态的描述中找到与“专一”有关的描写。在祭祀的整个过程中,孝子要做的就是专一地观想亲人之容颜。因此《说苑·修文》会说:“圣主将祭,必洁斋精思,若亲之在;方兴未登憧憧,专一想亲之容貌仿佛,此孝子之诚也。”《白虎通义·杂录》也说“斋者,言己之意念专一精明也”。观想亲人容颜的心理状态是精神专一的状态,而主一,也是某种精神的专一。程子曾说敬时“有主则虚”,而祭祀观想的心理状态也有类似之处。例如《礼记·祭义》说:
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物既备,夫妇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
“虚中以治之”,从郑玄开始就认为是“言不兼念余事”,《仪礼经传通解》完全承袭。不念余事,专念此事,也符合“主一无适”的原则。更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祭义》中用“洞洞属属”来形容此虚中的心理状态。《仪礼经传通解》疏曰:
洞洞、属属,是严敬之貌。言孝子之心奉承而进祭之时,其心洞洞乎、属属乎,恭敬心盛,如举物之弗胜。心所奉持,如似将失于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极也。按《广雅》:“洞洞、属属,敬也。”26
用“洞洞属属”来形容敬之貌,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字书中一直这样训释,且朱子《敬斋箴》即用了此句:“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或敢轻。”陈淳《敬斋箴解》曰:“洞洞谓质悫,敬于言之貌;属属谓专一,敬于意之貌”。先秦文献中,这种叠字的形容词极多,有时很难确切了解其含义。但若稍微探求一下“洞”“属”的原义,也能大致明白为什么用此二字来形容心敬之貌。《广雅疏证》引高诱注曰:“冯、翼、洞、属,无形之貌。”“洞”是通达、贯彻、深远、中空之义。“属”是缀、系、连续、会聚之义。所以一方面是中空通达,一方面是连续会聚。中空通达便可以联想到“有主则虚”;连续会聚,便可以联想到“无间断”。《礼器》亦有对洞洞属属的描写:“洞洞乎其敬也,属属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飨之也。”
专一还体现为“不散”,如《祭统》有:
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茍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茍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
这里讲的是“斋”的效用,其实讲的还是“所以斋”的功用。程子也讲过“有主则实”,实则邪不能入,与这里不斋则于物无防,斋则能防嗜欲的论调也是一致的。斋需要统一其意志,因此若旁务其他的娱乐,则会破坏这种专一的心志。“心不苟虑”“手足不苟动”都是专一的要求。可见,“一”与“敬”之间那“丢失”的一环大概可以确定就是祭祀斋戒的功夫体验。
最后,我们补充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此加以考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敬”观念的发展与三代文化和宗教形态的演进有着密切关系,也能说明“敬”的心态内在于祭祀斋戒的发生与发展之中。在斋戒中所体验到的“敬”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的整肃状态,这种意义的“敬”不大可能是先民一开始就具有的,而是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中,陈来先生引用了卡西尔的文化人类学观点,考察了三代文化形态的演进,是从巫术到宗教,从上帝宗教到伦理宗教。27在这一过程中,正可以窥见“敬”的发展脉络。首先,“敬”的观念作为对一个对象的畏惧心态,不可能与随意控制自然力的巫术同时并存。也就是说,“敬”起源于巫术时代结束以后,当先民对自然力产生了畏惧,尤其是产生了至上神的概念以后,“敬”的观念才随之而起。当然,此时的“敬”还是有对象的尊敬、敬畏,而不是后世那种纯粹的内心紧张状态。但是至上神的观念产生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神的贿赂———献祭,而献祭意味着对自我*的收敛、克制,因此,有对象的敬畏便进展到以自身为对象的克制,也就是无对象的谨肃。这时,我们已经看到“敬”与祭祀的本质联系,无对象的“敬”产生于祭祀斋戒的场域。而“敬”的后来的发展,即逐渐发展为普遍的伦理要求,则是要到殷人的上帝宗教发展为周人的伦理宗教以后了。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出,尽管文字学上无法找到以“一”训“敬”的直接证据,训诂家质疑伊川“主一之谓敬”说的合理性,然而理学家直接指出了祭祀斋戒作为体验“敬”的内心状态的场域,而现代学者则从各个角度阐释了“祭祀”与“敬”的根本关联。可见,将“主一”与“敬”通过训诂以外的诠释学联系起来的关键桥梁就是祭祀斋戒。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伊川所开创的对“敬”思想的新理解,乃是建立在超越训诂的工夫诠释学之上。
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