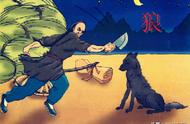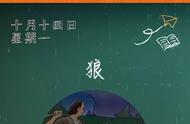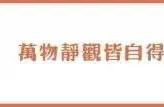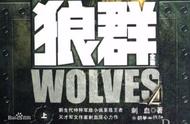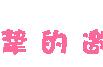开栏的话
2023年,我们推出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评选,迄今已评选出六期共60本,涵盖中外小说、散文、诗歌、理论评论等体裁,内容丰富、种类繁多,题材新颖。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评选在文学界、出版界取得较大反响,也为广大热爱文学的读者朋友提供了与文学佳作相遇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让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妙处,中国作家网特在微信公号开设“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栏目,以创作谈、文学评论、访谈等多种形式对“文学好书”进行推介。
本期推荐作家韩东的中短篇小说集《狼踪》,该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当代诗人、小说家韩东的中短篇小说选集,所选小说皆为其时隔20年重返中短篇小说写作后的最新作品,共计8篇,分别为《对门的夫妻》《狼踪》《大卖》《晚餐》《临窗一杯酒》《素素和李芸》《女儿可乐》《秦岭》。所收作品具体而微地讲述了一代人的故事,聚焦琐碎的生活状态,挖掘生活中很多细小、易被人忽略但耐人寻味的部分,同时关注更加广袤的人的精神状态。语言凝练、平易,富有诗性,风格冷峻与幽默并存,有力地刻画出平凡生活中人之存在的纵深底蕴。
——栏目主持人李菁

《狼踪》
作者:韩东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5
批判性与游戏性:韩东小说的“双面神”——《狼踪》《幽暗》漫论
文/ 陈霖
韩东新近出版的《狼踪》《幽暗》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将幽微而晦暗、缠绕而混杂的生活世界转化为清新明澈的故事世界,好像生活本来就要求被描绘成那样,韩东小说不过是说出了它们想说出的东西。这种印象或许缘于韩东小说以一种低调、谦抑、克制的态度面对和处理他的生活经验。但不能因此而忽视,韩东小说中哪怕是极简单的事情,当其被讲述之后,甚至是在讲述之中,总给人以深意藏焉之感,那种弦外之音比小说本身更加让人难以忘怀。韩东小说何以有如此魅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小说让人与事处在经验之中并通过经验向我们呈现,使我们得以面对这些经验意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叙事者控制和展开的叙述活动,构筑起语言游戏的空间,又散发着日常生活批判的意蕴。
一、自我的抽离与转化
如果将《狼踪》《幽暗》中的叙事者人格化,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中年男性的轮廓。这个男人很多时候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或是一个教授、一个画家、一个导演、一个主编。有时候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有时候讲述别人的故事;有时候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有时候则用第三人称。他在诗坛已有盛名,甚至被称为诗坛领袖;他出书了,朋友们希望能够“大卖”,结果却闹出暴力事件;他与文坛各色人等交游甚广,为某家著名的文学刊物担任组稿的工作;他的朋友们有的自*,有的入狱,有的深陷情感困境,有的堕落;他在朋友的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个朋友的各种出格行为以及他们一起打牌的情形;他在刚进入大学做教师时,经历了足够令人惊掉下巴的奇事或者糗事;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遭遇匪夷所思的事情,譬如与失联20多年的前女友在岛国相逢,又或者在幻觉中与已故去的女人欢爱;他一不小心就陷入一段平凡无聊却又复杂无比的关系之中,包括但不限于男女关系;他冷眼旁观身边的人如何不无自欺地设定解决俗世问题的因果框架,或是不动声色地拆解男男女女编织的爱情故事;与人的故事相比,他对小猫小狗的讲述更富温情……
毫无疑问,这个“他”折射着韩东本人在现实世界的影像,甚至暴露着韩东私人生活的轨迹,包括他的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可以说,这个“他”是韩东的“化身”,是在小说的“元宇宙”里的角色玩家。与韩东熟悉的朋友甚至能够从中准确地判断谁谁谁被写进了小说,可能担心或者期待自己与韩东的交往也被韩东征用。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将这些文本当作“自传体”小说,因为它们并非仅仅出于自我表达的情感冲动抑或其他自我护持的理性动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恰恰是对“自我”的悬置——这一点将在后文具体展开。这些小说当然更不是一段时间文坛热衷谈论的所谓“非虚构”,因为,它们明确地遵循着虚构的惯例。人们经常引用韩东自己的说法:“将假的写成真的,将真的写成假的。”其实这一表述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个“假”都指向虚构,而“真”,在前者是逼真,指向感觉;在后者则是事实,指向客观的存在。就取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讲,这两个“真”之间构成的辩证,是一次自我的抽离——将自己的生活抽绎为小说中“他者”的生活;同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将“他者”转化为作为叙述主体的“自我”——别人的生活成就着“我”的叙事。这种自反性与他者性构成的一体两面,预示了韩东小说中游戏和批判的双重性。
这种双重性建基于两种经验的关系。本雅明曾试图作出区别,“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1]可见经验对于叙事艺术的重要性。只是,本雅明这里强调的是小说将个体的经验作为对象,而在我们看来,就像杜威所宣称的“艺术即经验”,不仅指艺术来自经验,而且指艺术创造本身即是经验。小说这一堪称古老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在于它总是植根于人的经验,讲述人的故事,小说叙事在此过程中也成为一种艺术经验,作用于人们的感知方式。因此,当我们面对韩东取自自身经验的小说叙事时,需要关注的是两种经验形态的互动和转化。
二、灰色系与孩子气
在每日如斯的平静生活的外表下,那些疯狂、荒诞而不自知或不能自已的喧闹、*动、焦灼,并不为人所关注,人们通常将其视为例外而打发,殊不知它往往内在地构成了生活质地,并且通过一些节点与外部的生活息息相通。《大卖》中,先是“花姐”以老情人的身份打了一通电话,让作家小林在新书发布会上一直感到不安;再是发布会后的酒宴上,闷声不吭的光头,突然拎起空酒瓶砸向酒酣之际高谈阔论的高总,造成流血事件,然后一片慌乱;接着是围绕对高总的赔偿,大家煞有介事地讨论,将小林当作了下酒菜;最后是“花姐”解密,并将此前“剧情”的设计归因于“我爱你”。如此,整个首发式具有了一种神秘的闹剧色彩。那些看起来不无夸张的推销方式、内心的执念、极端的言辞、出格的行为,从小林那敏感多虑的视角呈现,并与这一视角的质地相叠加,既令人如观喜剧般地忍俊不禁,又不时能够从中跳出而报以嘲弄或同情——你会发现,虽然整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足够特殊,但是其共享的逻辑却与现实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从酒桌排位到出谋划策,从动机解释到内心表白,莫不如此。
正如很多人谈到过,韩东小说讲述的都是日常生活。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对这样的日常经验,作家并非事无巨细地呈现,而是有所选择。他笔下多是作家、画家、诗人、音乐人、媒体人、大学教师,那些光鲜的身份,不说多么耀眼,至少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韩东显然不是从社会认可的角度来选择,而是恰恰避开了他们被大众所接受的日常,让他们脱去文化的外衣,偏离社会角色的舞台,将其置于日常琐细的生活之中,凸显出他们生活中失败的、灰色的一面。我们看到,《狼踪》里的韩梦,尽管身居海外,拥有豪宅,生活安逸舒适,但内心深处却被难言之隐持久折磨,直到生活中的某个危机时刻——她视为人生成功之标志甚至作为其人生意义之全部的丈夫,跟别的女人好上了,于是情绪的崩溃不可收拾也顾不上体面了。
需要立刻指出的是,这一面向并非就足够完整或指向更为真实的存在,而是表明它们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形成了身份的幻象;因此,选择这一面,即可击破这幻象。这里当然免不了所谓的私人性,但与所谓“私小说”不同的是,韩东不是以揭秘的冲动驱使自己,也不是以猎奇的噱头迎合读者,而是以朴实的姿态进入,以平视的目光打量。这里有小孩子般的天真。在小孩的眼睛里,成人的世界总是奇妙的,令人惊讶或令人厌恶,而“简简单单地做一个孩子,就让这个孩子成了成人日常生活的批判家”[2]。《佛系》的结尾,江月告诉“我”,因为放生黑鱼,鲍家英的孩子皮肤变白了,而“我”对其加以否定的反应,颇有说“皇帝什么也没穿”之意。更多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形象不是直接诉诸具体的人物和情节,而是表现在观察的视角和讲述的语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调性。我们看到,在《幽暗》《动物》中,人物内心的欲念、幻觉、挣扎、屈从、恍惚,可谓复杂之至,但是,小说的叙事却使其直观可见;《兔死狐悲》《峥嵘岁月》写人物的命运在跨度颇大的时间里沉浮,充满人情世故,但讲述的快感令之如在目前展开的游戏,并无沧桑之感,而似乐在其中。因此,在韩东小说里,孩子除了作为“批判家”的形象存在,还有着游戏“玩家”的意味。
三、一切从语言的经验而来
一如韩东此前的小说,《狼踪》《幽暗》的语言质地给人以朴素洁净之感,相比较而言,这些近作更显得素面朝天,毫无炫技之意,乍一看没有什么精彩绝伦,只是耐心地传达外显的物事和抵近内心的幽微。但其实,技法潜隐其中,或者说已然成为物事和内心的构成部分。像《秦岭》的最后,看起来如此漫不经心地说话,却一下子将前面S县曾经发生过的连环*人案连接起来,这就是技法。这些技法将生活经验重新当作新生的有机体来把握,赋予作为素材的经验一种有形的意义,这种有形的意义即是对生活的再造。
相比于生活的经验,对小说家来说,语言的经验更加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生活的经验就是语言的经验,反之亦然。套用海德格尔的一篇题为《从思想的经验而来》的短文,韩东小说的一切是“从语言的经验而来”。海德格尔在那篇文章中试图将某种思想丰富然而缺乏行动的前戏或余波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被视为捕捉思想的利器,无法摆脱作为工具的地位。当然,在韩东小说的操作层面,语言无疑也是巨大的工具箱,但是,一如他早年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他的小说实际上也秉承了这样的语言观。这一语言观的实质,是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与语言共舞、与语言周旋。在这里,语言并非作为客体和对象,等待着主人的使用,而是作为行动者,参与和生成着叙事的走向。就像梅洛-庞蒂所指出的,“它在我仍然缄默的意向与词语之间充当中介,以至我的言语突然出现在我自己面前并把我的思想告诉我。那些被组织起来的符号有其内在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从属于‘我思’,而是从属于‘我能’”[3]。
“我能”,在韩东的这些小说中,首先是叙事的语言机制对故事进程的把控,就像特定的程序将数据库里离散的信息呈现得可见和有序。不同的是,韩东的“算法”体现为训练有素的语言经验,在显得自然而然的叙事言语流动中,随物赋形。像《我们见过面吗》《对门的夫妻》《晚餐》等,看起来像是几个组件或几个画面,貌似可以随时挪动,但却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而其间的留白则生发着叙事内在的情绪或氛围;《秦岭》《大卖》《狼踪》中的叙事,则在绵密与跳脱、沉浸与疏离的变奏中埋伏着玄机;《临窗一杯酒》《峥嵘岁月》《兔死狐悲》则仿佛是歌吟与长啸的轮替……这样的“形式感”当然是语言的奇迹,但那些词语和句子毫不“文学”, 不会一下子惊艳到你,就像我们日常的用语,只有你身心俱在其中,与其相处,才能心领神会。
列斐伏尔曾谈到艺术家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创作的材料,他非常敏锐地指出:“我们近距离观察一种从土地上、从各种各样的植物中挑出来的不起眼的植物,这种植物就变得神奇无比了。然而,一旦这样的形象与它们的日常背景分开,表达这些形象的日常属性的描述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就是天才们的秘密……(也许)这种秘密提供了一种超前现实的可能途径。”[4]韩东小说里经常让我们感慨其精准而又独特的描摹之所在,恰是对这种困难的成功克服之处。《狼踪》写曾小帆去美国看闺蜜韩梦,小说主要采取曾小帆的视角,人物与事件的描述势必投映了她的情感和心绪,却表达得内敛而极简。譬如其中一段写她与韩梦的丈夫段志伟在车库抽烟的情景:
卷帘门完全升起,外面的空气新鲜甚至凛冽。他们没有走出去,轻声细语地说了点什么。就像他们的话会像烟雾一样,弄不好的话会飘上楼去,惊吓到韩梦。在关了车库的灯,卷帘门尚未全部降下,他们准备上楼返回去的一个片刻,曾小帆瞥见了外面的星空,星星密密麻麻的,就像头皮屑。也许是曾小帆的幻觉吧。
这里的描述当然精准,但是这种精准不仅是现场的还原式再现,即并非就这里事件发生的场景而言,而是就整部小说而言的。除了富有沉浸性的画面感,这里最让人惊异同时也可能很是令人困惑的是“惊吓”和“头皮屑”。只有读到小说的最后,我们才会恍然大悟,此情此景中饱含着如此复杂的往事前情。细节的描绘不仅是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点位的高亮,而且是对整个持续过程的辉映。这样的段落,在韩东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它们在小说文本构成中指向着动态的、整体的情境,就像我们在一个熟悉的区域里,站在任何一个地点,都能迅速建立起与周边的空间关系。韩东小说对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描绘,不是停留于外部可见的呈现,而是深入到内心,就像《素素和李芸》中那样,“我”与两个女人,以及两个女人之间,在或拉扯、纠缠,或切换、交叉,或刻意、巧合之中,一点点将男人和女人的重重心事一一揭开。
四、意义在哪里
如果说,韩东以往的小说中,非叙事性言语时有强制性地介入,叙事者的声音非常突出,将人们引向对叙事操控者语言行为的关注,并且令人感到叙事者在智力上的优越感;那么,在《狼踪》《幽暗》中,这种优越感的调性虽依然存在,但显得更为蕴藉,非叙事性言语与人物行动的描述,与故事的讲述,贴合得更为紧密,像是墨线划过白纸上时衍开的影晕,在强化读者感受正在进行的故事的同时,也让读者与人物的行动产生某种疏离感,并形成韩东小说叙事所特有的冷幽默。譬如,在《佛系》中,鲍家英夫妇和江月为放生黑鱼而艰难寻找合适的地方——专找人迹罕至之处,但现在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于是“他们就像落在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里的蜘蛛,不,是蜘蛛捕获的虫子,试图寻找一点可能的疏漏用以逃脱。现在黑鱼们的逃生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逃生,不仅感同身受,也有了命运与共的意思”。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浑浊但闪闪发光的水塘,就像时空隧道的入口一般,他们把塑料袋里的黑鱼统统掀了进去”。
如此叙事,不仅传递着故事的“事态”信息,而且生成着故事的“意态”信息。我们看到,韩东小说里的事件几乎多是凡人俗事,仅仅就事情而言,几乎“无事”可言,如果止于如其所是的描述,则是“一地鸡毛”,也沉闷而无聊。而通过叙事的转化,生活进入了语言,变成了语言,织入语言的基底和纹理。于是,生活经验与语言经验不再分割,语言不仅是“器”而且是“道”,小说叙事成为反观生活世界的隐喻。《峥嵘岁月》写到《西部文学》主编马东,在一次聚会上,试图与老潘等艺术家套近乎,但是艺术家不买账,小说描述道:
“说出来听听。”老潘说,口气尤其冷静。但在李畅看来就像猛兽捕猎前的潜伏,他甚至听见了草梢窸窸窣窣的响动。
这样的叙事,奇妙之处在于:“语言离它意指的东西既非常近又非常远。在某种意义上语言背对着含义,它对含义并不关心……语言与其说是一张有关那些令人满意的陈述的表格,毋宁说是那些完全着迷于彼此区分和彼此印证的姿势的扩张。”[5]我们看到,细节的描绘,不只是停留于还原,而更是在重构。这种重构的言语释放出具有穿透性的心理效应,因此而泛出的嬉笑之声里,有语言游戏的快感,有对存在的否定,也有对人的同情。这并非仅仅适用于《峥嵘岁月》里马东这类生活的失败者,而同样辉映着小圈子里的所有人物及其处境,李畅也好,小二也罢,他们的某些行状,包括内心里的盘算,都与马东的灵魂构成了深层的呼应。
这种呼应,在韩东小说中不啻为一种空气般的存在,弥漫于《老师和学生》《兔死狐悲》《临窗一杯酒》《大卖》《秦岭》《动物》《素素和李芸》《幽暗》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力承担的责任、左支右绌的伦理秩序、成功的虚浮标准、不择手段的利益争夺、*和虚荣、背叛和遗忘……当然,在韩东的小说中,同样并不缺少对友谊、亲情、活力、善意的表现,我们每每被这些善意自然的释放所打动,但是,并不因此陷入某种刻板印象或幻象,因为小说的叙事总是及时地将你从沉溺其间的边缘拉回。《兔死狐悲》中写在张殿的告别仪式上,“我”本来不准备流泪的,但当看见张殿的女儿张画画抱着张殿的遗像时,“突然就不行了”,“这种灵异般的体验无法向人道明,确实把我给吓坏了”。向逝去的老友告别,可能在很多人心目中有着某种共情。流泪是共情的表现,但是,韩东在这里将它表现出来的同时,又将它轻轻瓦解:“与其说我是因悲伤落泪,不如说是被吓哭的。”
我们对意义获致的描述,是对阅读体验的定性和抽象,但小说当然从未指明这些抽象的内容,而是将其处理成如雾状的背景中浮动的颗粒,人们在呼吸视听之间感知和承受其存在,使之通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由现象学观之,韩东小说的叙事自觉地抵御“误置具体性”,即力求避免把要素当成实体性部分,而“意义正是居于它的所有表达项之中但又在它们背后的同一性”[6]。
五、爱,从虚无中升起
韩东小说叙事的批判性与游戏性,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而是彼此渗透、互生互构。这种批判性的游戏或游戏性的批判构成的语言本体,呈现出反讽的特质。反讽意味着在叙事行进中多种力量、多重意味——否定、怀疑、悬置、不确定性——对直线型的叙事外观进行扭曲、变形、中断或抹*。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实际上都归于“自我”的精神实验或者说语言实验。叙事言语活动不仅是对处于小说世界之外的生活世界的再现,也是对讲述者自身的一种现象性展示。小说叙事的自我指涉在韩东这里,固然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自我作为审视的对象,也让他的小说显露出传统的人文情怀。
当经验自我在语言的经验中抽绎、转化和回返,被语言重塑或再造的时候,超验自我正在形成,批判性植根于此,并指向自我。正如韩东所说:“自我批判尤为重要……批判若只停留于对他人嘲弄、对他人的阴暗的揭露,是很不够的,必须首先针对自身,首先得过这一关。因为你对别人阴暗的感受程度恰恰是以自身的阴暗程度为依据的。”[7]我们的生活似乎没有明确的外部冲突和危机,但并不妨碍孤独和隔绝中的自我与自己的“他者”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韩东小说中的人物遭际即是韩东的“自我”通过语言实现的精神反刍和记忆重建。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自我批判也是自我拯救。我们在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通过各种话语建立起生活的对立面,以此构建一个看起来更值得一过的生活,尽管这个“更值得一过”的意思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但是其在结构性上却往往高度一致:漠视现实,驰骋想象,用精致和响亮的言辞装饰贫乏空虚的精神空间。韩东小说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转化,区别于这样的话语,是对这样的话语的挣脱——它显然不能被取而代之,而在其一侧释放出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构成的悖反是,它指向虚无的绝望之境,同时又是对虚无的反抗。尽管韩东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呈现为一种失败感、无力感的灰色系,触及他们内心深处难以祛除的暗疮痼疾,但是,敞露而非暴露、趋近而非认同的反讽叙事基调,导引出冰面之下的温暖和同情,包含着对生命存在的无差别接纳。这在韩东小说涉笔动物的篇什时尤为显豁。
早年韩东写过《花花传奇》,出于一种生命对待另一种生命、人对一般动物的毫无道理的优越感,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偏狭与虚妄被无情地揭示出来,戕害显得触目惊心。婆媳、夫妻、母子、情人等等角色关系,由于猫的存在而凸显出微妙又怪诞的色彩。如此,小说表现出对一个弱小的生命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对卑微的生命的尊重,传达出深隐于心、无以祛除的疼痛和怜悯。相比之下,收入《狼踪》里的《女儿可乐》,写人与狗的交往少了许多阴沉暗黑的色彩,没有那么多“事故”,而更多是寻常日子。更重要的是,人与狗之间的亲密、陪伴和矛盾,相较于韩东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单纯明朗,即便是可乐的骄傲、自尊、嫉妒、暴饮暴食,也是那么得人所怜。像下面这段,尽管笔触克制,温柔的感觉还是溢于言表。
“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不愿意做爸爸的女儿?”
可乐看着我。
“你不说话就是愿意。爸爸也愿意做你爸爸。”
可乐仍然看着我,我觉得那亮闪闪的是她涌出的泪水。
“那我们说好了,是真做我的女儿,而不是做一只狗狗。”
这样的谈话是因何发生的?我不得而知。大概是为了补偿我工作时对她的置之不理吧。安抚一番后我继续写作,继续对可乐置之不理。她又沦为这房子里的一件东西了。
小狗这类动物作为他者,同样也在映现着人类自我的偏狭、自私、世故,但最终消融于生命本身的共在之中,对人而言,这或许是一种救赎。显然,《女儿可乐》不是韩东小说中的一个例外,而是一种底色。当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回头去看其他小说,或会更好地体验到在其底部支撑着的生命之爱,那是抵抗虚无的力量之源。就像托多罗夫所指出的那样:“小说更多地倾向于道德而非科学。折中经验的终点线不是真,而是爱,即人类关系的最高形式。”[8]韩东的《狼踪》《幽暗》以其特有的方式将我们引向了这种最高形式。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城市共同体研究:媒介视角下的新都市文明 ”(项目编号:22JJD86000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转引自[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9页。
[2][4]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版序言》(第1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12页。
[3] [法]梅洛-庞蒂:《论语言现象学》,见杨大春、张尧均主编:《梅洛-庞蒂文集:哲学赞词》(第5卷),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1页。
[5] [法]梅洛-庞蒂:《算法与语言的神秘》,《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1页。
[6] [美]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高秉江、张建华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7] 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8]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濒危的文学》,栾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作者简介
韩东

韩东,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导演。1961年生,曾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革命性纲领。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重新做人》《他们》《你见过大海》《我因此爱你》《奇迹》等,言论集《五万言》。另有其他作品四十余种。新近出版的重要小说集有“年代三部曲”:《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短篇小说集《狼踪》《幽暗》。荣获包括第一届“先锋书店诗歌奖·先锋诗人奖”“金凤凰奖章”“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磨铁诗歌奖·2020年度汉语十佳诗人”在内的多种诗歌和文学奖项。
相关阅读: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张平《换届》:政治生活文学表达的新视野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米亚•科托“帝王之沙”三部曲:历史的名字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刘年《不要怕》—— 献给所有胆小的人儿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钟求是《地上的天空》:九个故事,九种人生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朱文颖《深海夜航》:文字构筑的引力装置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周瑄璞《芬芳》:大地的女儿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美】卡尔•桑德堡《烟与钢:桑德堡诗选》:喷烟的烟囱、矿场和巨圆石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苏珊娜•麦康奈尔《写作是从事一种娱乐行业》:教条啊,我即上帝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黄昱宁《体面人生》:当代体面人生的AB面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萧星寒《碳铁之战》:我把重庆写进科幻里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太阳降落的地方》:阿微木依萝在“太阳降落的地方”继续讲卡夫卡式的故事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刘汀《水落石出》:作者应该把小说中的角色当成生活中的人去对待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阿舍《阿娜河畔》:深情致敬兵团的拓荒者、建设者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石一枫《逍遥仙儿》 : 在“人间”何以“逍遥”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 | 2023年第五期:太阳降落的地方,有芬芳的人生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张进步《我,一个驾驶蝴蝶的人》 : 我的词语开始燃烧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王得后《年轮》 : 年轮中的文坛往事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李晁《雾中河》 : 书写世间如同盐一样的人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 | 2023年9-10月入围书单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革命者》 : 五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黄永玉《还有谁谁谁》 : 让这回忆抚慰我一切的忧伤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甫跃辉《嚼铁屑》 : 60万字长篇,3600公里骑行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鲍尔吉·原野《乌苏里密林奇遇》 : 走进原始森林,领略人间百态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反抗的忧郁》:毁灭也会更新换代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人文与自然的交界处,有着最疗愈的力量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工作为何伤人?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潘峰《天地扬尘》:跨越岁月长河的记忆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朱婧《猫选中的人》:我对问题的追问超过了对故事的渴求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于坚《漫游:于坚诗选(2011-2021)》:写作之道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杨怡芬《海上繁花》:重返现场,是不够的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骁骑校《长乐里:盛世如我所愿》:没有风浪的人生就不是大海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莫言剧本《鳄鱼》:不花哨的传统叙事也能具有传奇性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夏坚勇 《东京梦寻录》:宋史炽热却为何?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常小琥 《如英》:那些不得不说出口的终将发出鸣响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 | 2023年第三期:抓住喜鹊的尾巴,在热浪里漫游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蔡骏《谎言之子》:光明与黑暗之间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曹寇《鸭镇往事》:我的写作与生活同步,跟现实平行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张旭东《藕香零拾》:蓼虫避葵堇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王蒙《霞满天》:真正展现了什么是“日子”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王芸《纸上万物浮现如初》:一卷书香贯古今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科尔姆·托宾《魔术师》:一个摇摇晃晃的大师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 | 2023年5-6月入围书单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今夜谁家月最明》:锺叔河谈读书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何顿:《国术》是这样喷薄而出的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田耳《秘要》:在小说里玩细节是最开心的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杨苡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星沉海底当窗见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塞壬 《无尘车间》:流水线不需要同情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彼得•凯尔 《马略卡的四季》:一个值得追寻的梦想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张炜 《橘颂》:老人和石屋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范雨素 《久别重逢》:在满地六便士的世界里仰望月亮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傅菲 《灵兽之语》:每个字都很珍贵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薛超伟 《隐语》:到过去休息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韩松落《春山夜行》:在西北的春天里走向荒野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老藤《北爱》:在朴素中再现东北的辽阔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荐书 | 龚静染《边城新纪》:怎样去描述一座边城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 | 2023年第二期:纸上万物仿若一场人生的魔术
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 | 2023年第一期:撷英十朵 奔赴春天
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编辑:邓洁舲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