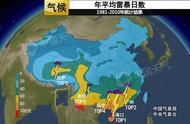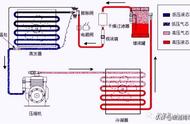作者:冯圆芳
李敬泽《会饮记》写到欣赏京剧《红鬃烈马》里《武家坡》一折时说:薛平贵的老生并不真老,佻挞自喜间,有一种天朗气清的贵气。
佻挞,轻薄意。武家坡上,不肯直接与发妻相认的薛平贵偷摸王宝钏那几下,自是“佻挞”无疑。而说起“天朗气清的贵气”,私以为,女老生王珮瑜扮演的薛平贵,那举手投足、眉梢眼角间杂糅的天真与世故、俏皮与狡黠,最当得起这份称誉。
在看个京剧也要“嗑CP”的年代,王珮瑜、吕洋这对拍档是我最属意的“薛王”组合。身为著名程派青衣、梅花奖得主,吕洋在诠释王宝钏人物的细腻度上极其到位。《武家坡》里,宝钏尚未出场,声音已袅袅绕梁;及至登台,一袭素衣,映着粉面桃腮,既是风流难抑,又透着股贞静自持,有种“美人在骨不在皮”的自信。在我看来,吕洋塑造人物的秘诀在于做减法:整个人的气质偏冷峻,既不讨好薛平贵也不讨好观众;眼里的戏要拿捏得稳,切不可用力过猛,形象的张力反而更大。程派的独特发音,更使宝钏的开场独白如泉水呜咽,隐隐有不平之鸣。
喜欢“瑜洋”CP,是因为这一版《武家坡》实在曲折逶迤,明里暗里戏都多。坡前与发妻相遇,薛平贵心生一计,想试探下妻子是否忠贞:“她若有心,将她认下;如若不然,打马就走。有理啊有理!”于是佯称自己与薛平贵同营吃粮,又说平贵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向自己借了十两纹银,便卖妻来还。这场戏里,清俊狡黠的王珮瑜步步紧逼,屡屡揩油,轻薄狎昵,吕洋则机智反攻,不时扳回一局,最终在“确信”丈夫典卖自己后,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嚎:啊,狠心的强盗哇……
即使分别十八载,何至于对面不相识?李敬泽说,陌上相逢,所认的不过是心,试一试心还在否。可怎样才算是“有心”?穷守寒窑十八年算不算“有心”?还是以为丈夫要典卖自己,宁死不屈从,才算是“有心”?
台下说戏,王珮瑜直截了当:薛平贵就是个渣男啊!
当这出戏就要向控诉男权的方向发展时,故事突然反转了:薛平贵追至寒窑门外,认下了这位“傲骨贤妻”。这是一出令人五味杂陈的相遇:有感慨岁月不羁、容颜变化的沧桑唏嘘,有夫妻间拌嘴、调侃、揶揄的生活情趣,也有王宝钏得知薛平贵封西凉王之后的画风陡转:“走向前忙跪倒,薛郎面前讨封号。”
一个穷守寒窑十八年的“有气之人”,怎么就180度大转弯,觍颜讨封了呢!怎么就在知道薛郎另娶代战公主之后,心甘情愿于“她为正来我为偏”呢!不知别人作何感受,至少我看到王宝钏慨叹“十八载才把凤衣穿”时差点喜极而泣的样子,那副自觉用男权社会的游戏规则来自我驯化的模样,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所有这些,令《武家坡》一折变得非常耐“嚼”。“拧巴”的剧情,出人意表的对白,男主人公身上的“平庸之恶”,在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画风转化,都诱使着现代观众审视情节的缝隙之处,那被明快的色调所遮蔽的人物的真实悲喜,和背后交织的权力话语、那难以凝视的深渊。
王珮瑜早就给出过解读:京剧传统老戏里是没有爱情的,讲的只是伦理,《武家坡》即是代表。这出戏从前的戏词里,甚至有“她若不贞,一剑将她*死”的语句,随着时代的进步才做出了修改。
悖论之处在于,这不妨碍《红鬃烈马》常演常新,也不妨碍薛王成为熠熠生辉的舞台形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戏曲的消费不再囿于道德训诫的层面,而是更关注纲常伦理框架之外的人性质地,正如“渣男”一词远远无法概括薛平贵的形象一样。事实上,在他的“直男癌”、自我中心、不负责任、睚眦必报等弱点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他真实可爱的另一面:慨叹“少年子弟江湖老”时的悲凉难抑,出人头地后的得意忘形,调戏王宝钏时的狡黠天真,时隔十八年后仍然愿意认领糟糠之妻、并将其封为正室的有情有义……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侧面,我们才在谴责他所代表的权力结构的同时,也由衷地喜爱他。
这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主人公:也许,当我们愿意放下对完美人性的期待或苛求,反倒有可能看到更多生长,领略更勾魂摄魄的人性风景。(冯圆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