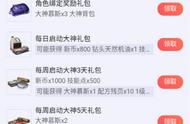我们的文学终于遇上了屎尿问题!从当代文化的发展逻辑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很显然,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文学艺术教育的孩子气的过分纯洁化,由于前卫文学艺术的资讯传播在相当程度上一直局限于前卫和精英小圈子,整个社会都没有为接受常识之外的文学艺术实践做好准备。
所以当时间来到2021年初,多少年都与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全无关联的高低各阶层的人们、热爱古典诗歌的人们、担心孩子成长的人们,在个别文学批评者的带动下,偶然抓住了当代个别诗人的屎尿书写,一下子亢奋起来,形成网络合力,要清算当代诗歌写作圈子里存在的特权、腐败、堕落和丑陋,以及带有实验倾向的诗人们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大致养成的文学观念。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些网民觉得屎尿书写是对自己崇高文学认知的羞辱和挑战。清算诗歌写作的丑陋,这说明:1,由于传统精英文化的影响,获得网络授权的大众依然很拿诗歌当回事;2,由于相信了白居易作诗能让老太太听懂的传说,人们真以为诗歌写作是个人人可捏的软柿子。
屎尿,作为审美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思想问题,甚至宗教问题,的确重要。不过这虽然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自古以来,不论中外,人们对它的文化接受却相当“有意思”。我从公元前的远方说起:
释迦牟尼逝世百年之后(这是哲学史的说法;宗教传说是公元前240年左右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即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古印度的佛教徒中间爆发过一场大辩论,这大辩论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大分裂:一部分信徒归入南传上座部,一部分信徒归入大众部。导致分裂的原因说来有趣,是一位名叫大天(Mahādeva)的比丘认为修到阿罗汉果位的修行者依然具有五种局限(即所谓“大天五事”),其中包括:阿罗汉的生理机能依然存在,而生理机能指的是情欲、大小便等。同意大天比丘观点的佛教徒就站队成了大众部,不同意的成了上座部。而后来的大乘佛教就是从大众部发展而来。此事小乘和大乘佛教文献中都有记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修行者、思想者而言,大小便问题能把人逼到绝对的精神死角,更遑论普通人。这个死角从来没能被抹去过。
屎尿问题不仅曾经困扰过部派佛教时期的僧众,也曾困扰过中东和欧洲的基督徒们。而且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直到今天,还为某些并不浅薄的人们津津乐道。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虽不是基督徒,但他在一首名为《屎》的诗中写道:“《圣经》里虽没记载/亚当也拉过屎吧/而夏娃在伊甸园的草丛中/也拉过苹果屎吧”。不知会否有人觉得自己被冒犯到?在日本,人们并不觉得被这几行诗亵渎和冒犯。这首诗收在谷川的儿童诗集《无聊之歌》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六章《伟大的进军》中写道:“早在2世纪,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就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他声称:‘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粪。……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麻烦的神学问题。’”
当这个“神学问题”冲进诗人、作家、艺术家们的大脑时,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便超出了老实人的审美预期。大家喜爱的格言诸如“上善若水”、“宁静致远”、“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难得糊涂”等等,直接撞上了屎尿文学和屎尿视觉艺术,以及书法领域的“丑书”、电影领域的“阴暗面叙事”等等。这是个世界性文化现象,不是只有当下的中国人受到了屎尿的挑战:20世纪英语世界诞生了两部在大胆、离奇、污秽、神叨等方面充满创造力的伟大小说: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美国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还有别的作家作品,例如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但没有这两部书重要)。在对屎尿和性的兴趣上,两位作家不相上下。这里,两个人的例子不能都举,那咱们就看看品钦的杰作吧:《万有引力之虹》开篇没多久,品钦就写到斯洛索普爬马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游下来了一阵极端可怕的激流,响声如波涛骤起,波涛前端是乍离闸门的大便、呕吐物、手纸和红果莓,组成动人心魄的图案……”

作者: [美] 托马斯·品钦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意大利诗人、电影导演、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追随者、改写过但丁《神曲》的皮埃尔·保罗·帕佐里尼,在1975年拍摄过一部屎尿横飞、施虐受虐的电影《索多玛的120天》。这部片子改编自法国18、19世纪之交的色情作家、哲学家萨德侯爵的小说《索多玛120天或放纵学校》。萨德侯爵对20世纪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乔治·巴塔耶等人都产生过重要启发。而帕佐里尼由其著作改编的电影,矛头直指墨索里尼,揭示出法西斯主义在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全方位堕落。影片拍得冷静、血腥、肮脏又黑暗,曾经被多国禁映。1980年代、90年代中国够格的文艺青年中有许多人通过盗版碟看过这部电影,或者至少听说过这部电影。
帕佐里尼既热爱下层人民又对其信心不足(令我们隐隐联想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名言),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简单说他堕落显然不合适。那我们就调整一下目光,来看看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纽约出道的德国女雕塑家基基·史密斯,她对人体以及心肺胃肝脾等各人体器官兴趣浓厚;由于对艾滋病和妇女权利的关注,其艺术探索一直延伸到包括屎尿、经血在内的各种体液。史密斯有一件惊世骇俗的作品,塑造的是一个裸体女人跪爬在地上,身后拖着一道长长的大便。再看看美国1990年代崛起的艺术家马修·巴尼。在其混合了表演、摄影、录像、装置等因素的实验电影《重生之河》中,艺术家居然为大便贴上了金箔,而这部电影讨论的是生死和信仰问题!其实1945年出生的、受到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影响的美国艺术家保罗·麦卡锡在影像中使用的屎尿语言更过分,连我都看得恶心!但是,在许多人对文学艺术中的屎尿语言产生不适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的同时,够格的文艺青年和文艺中年们,可能也会因为获知他们的作品形态而意识到一种世界性的审美变迁:19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文化阶段;197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68年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的撼动,世界文化进入我们现在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当代”。认同不认同这种变迁是咱们自己的事,但文化情报多了解一点儿没坏处。

2010年6月9日,英国伦敦,马塞尔·杜尚的“小便池”作品《泉》在白教堂画廊展出。人民视觉 资料图
曾见有人举出法国艺术家杜尚的小便池作品《泉》的例子,为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屎尿书写做辩护(但杜尚关注的更多是艺术观念问题:即小便池现成品。它没有直指人类的排泄,当然排泄的问题肯定也包含在其中),这件最初展览于纽约的作品诞生在1917年,比我们的五四运动还要早两年,比当时欧洲、美国蓬勃传递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观念还要激进。那时的中国人在搞我们自己的新文化运动,喊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但很有趣,徐悲鸿在科学大旗的指引下从法国引入的却是19世纪(和以前)的欧洲写实主义绘画。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从那时开始就走拧了。——当然,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政治逻辑,走拧了也不是错误,但把19世纪(和以前)的西方艺术接受为中国艺术(完全不同于文人画)肯定也简单了些。杜尚的小便池给20世纪的世界视觉艺术和艺术思想提供了持久的话题。我至今记得1980年代初期当我了解到这件颠覆性的作品时内心所产生的震动。不过到如今一般中国人喜欢的,或者说习惯的,依然还是徐悲鸿的写实、齐白石的生活情趣。管他什么马修·巴尼、保罗·麦卡锡、基基·史密斯、皮埃尔·帕佐里尼、托马斯·品钦、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杜尚(还有其他人),我们只要奔驰汽车、阿迪达斯运动服、卡布奇诺咖啡、波尔多葡萄酒、香奈儿包包、墨镜和香水,还有苹果手机。
马修·巴尼、托马斯·品钦、詹姆斯·乔伊斯那些恶心人的、堕落的、肮脏的图像和文字,经典化的唐诗宋词里可没有!20世纪初曾经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他们感到尴尬的原生态生殖器民歌倒是有,但早就被移风易俗掉了。拥有漫长文明史的中国人、拥有辉煌文化记忆的中国人,怎么能跟风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玩屎尿诗和屎尿艺术!估计从未听说过《重生之河》与《万有引力之虹》的当代中国读者们在网络上对屎尿诗破口大骂、竭力取笑之后,会闭上眼睛背一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以恢复内心对文学的崇高感受,以恢复自己前现代的文化自信,然后心生对世界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厌恶。乔伊斯、品钦和他们分布在各大洲的文学同类们证明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堕落和无耻——不管他们是否具有革命性,是否挑战了中产阶级客厅文化!包括《天地阴阳》作者白行简(白居易的弟弟)、《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肉蒲团》作者(传)李渔在内的小说家和诗人们的趣味至少不像资产阶级作家一样堕落!这些西方资产阶级作家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即使没读过《诗经》、屈原、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他们也应该读过汪国真、臧克家、贺敬之、余光中吧!他们难道没听说过貔貅这种有嘴无屁股,招财聚宝,吞万物而不排泻的洁净的瑞兽吗?他们真是孤陋寡闻呐!貔貅才是文明的象征,与我们古老文明相匹配的优雅的文学也得具有貔貅的品质!

水晶貔貅 人民视觉 资料图
不过貔貅自有貔貅思维的盲区。连老祖宗们都看不过去。于是庄子的小声嘀咕传了过来:“道在屎溺。”庄子提到屎尿这回事——他那么大的头脑看来还不够大:他一定不理解这貔貅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既然庄子都说了“道在屎溺”,那乔伊斯、品钦他们就可以写屎尿吧。——不对!你个大学教授做的什么学问?庄子本来的意思是道在万物,不是道仅在屎尿!——你脑子进水了吗?你是闲得非要显摆一下你读过并且正确理解了《庄子》吗?我在说“道”的事吗?我在说屎尿的事!网上清华大学教授指出北京大学教授滥用庄子“道在屎溺”说法的文章后面,排山倒海的附和跟帖中有一个帖子说“庄子笑了”。但这之后另一个跟帖说:“庄子笑了,老子没笑。”这后一个跟帖的作者不一般,肯定是个明眼人,而且话说得绝对委婉。老子的名言是:“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讨论的是形而上学,但他干嘛非要以“玄牝”这样的字眼来讨论呀!他是来自母系社会吗?我们不讨论形而上学,我们是善良的、干净的老实人,我们的脖子上挂着貔貅。去你的假幽默真邪恶,屎尿就是屎尿,你别兜圈子!
对不起,我是故意这样说的。而且不仅是我一个人故意这样讨论屎尿和生殖器问题。此刻我严肃地关心文学写作中的当代感受和当代表达,这与——对不起——“现代性”这个讨厌的大词有关;这是前现代的、已经经典化的唐诗宋词里没有的东西。——那么写屎尿你就“现代”了、“当代”了?没法简单回答:庄子是古人,部派佛教的僧侣们是古人,诺斯替教派的瓦伦廷是古人。中国古代未被经典化的屎尿诗篇虽然没那么多但也有一些。禅宗僧人们尤喜言及屎尿。屎尿,不仅是现当代文学、艺术、思想话题,作为写作对象、思考对象,它贯穿人类始终。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从取消了时间的人类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我们毕竟生活在具体的今天。我们都熟悉的“现代”这个词,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产生了。当“人本主义”取代了“神本主义”,一些意大利人就觉得自己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时期的大作家薄伽丘以其永垂不朽的故事集《十日谈》闻名于世。意大利当代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他的《宁芙》这本书中提到,持有“粗糙实在论”的薄伽丘认为缪斯女神虽然是女子但她们不会撒尿。这是薄伽丘在自己和过去的写作之间划了一道界线。
屎尿屁,还有性行为,作为书写对象,长期困扰、逗引着文学写作者们——不论是歌德这样的半神(见《浮士德》)还是野蛮的莎士比亚,不论是上半身写作者还是下本身写作者,不论是身体写作者还是纳入了历史与形而上思考的写作者——都想试试,看自己能否处理好这类话题、这些词。这些词很难处理,没有足够的才华处理不好;很多诗人、小说家、艺术家被屎尿屁打垮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处理这类话题,处理这些词,对于现代以来的诗人、作家们来说,有着与前现代诗人、作家们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受到全球诗歌读者赞佩的19世纪末法国天才诗人兰波曾经写到过维纳斯的“屁眼儿”。他的文学、道德挑衅意味十足。当然,他写得好。
挑衅、冒犯、亵渎,对经常持有文化、道德、社会、历史批判立场的现代作家、艺术家来说几乎像家常便饭。这应该与世界性的现代国家、现代文化转型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时期)。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尤其是被动谋求现代性国家(包括中国)的转型,其实都充满了挣扎与缠斗。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俄罗斯。几乎没有人敢对19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三道四,尽管他老人家诋毁起莎士比亚来也够瞧的。他曾经被俄罗斯东正教革出教门。也就是说,托尔斯泰违背了当时俄国正统的、主流的宗教、道德观念。不过托尔斯泰的经历还不是最惨的,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遭遇相比,托翁已经算幸运了。挪威是个小国,并且不像俄罗斯、中国一样被动转型。可是挪威人居然曾经宣布易卜生为“人民公敌”。他不得不远走他乡。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在今天看来都是高大无比的人物,是人们崇拜、感激的对象,但在当时,他们显然“亵渎”了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观与宗教信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现代的傻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对既成思想的不思考。”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当然是真正的思考者。昆德拉所说的“既成思想”,若扩展开来并且弱化它,指的就是对既成道德习惯和审美方式的逆来顺受,并且自以为在维护、捍卫传统,并且是以人民的名义。
20世纪的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文学艺术革命,甚至宗教思想革命(例如法国宗教—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无不与“亵渎”这个词有关。它为我们反思时代生活、寻找文化创造的可能性提供了滋养;它对旧有文化秩序形成了冲击。这是一个复杂的、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得能够证明自己虽然讨论到了屎尿,但我们不是处在儿童心理学所说的“肛门期”。中国当代具有实验色彩的诗歌,秘密萌发于“文革”时期,在1970年代末文化、政治启蒙的大潮流中确立其存在,其反思对象是此前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它后来形成了一套文化逻辑和文学、艺术、思想趣味,形成了其语言指向。我记得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某一天,我曾与诗人田晓青讨论到女神维纳斯。田晓青说既然维纳斯不是胎生,那就不应该有肚脐眼儿,所以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肯定是画错了!我想这类讨论对老辈诗人们来说一定是陌生的。不曾深入文学书写的人们喜欢谈论文学的永恒价值,但臧、贺的诗歌其实也不是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而是革命、政治、时代生活的产物。对于晚清、民国的旧文化来说,臧、贺的写作也带有“亵渎”性质。尽管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每一位诗人、作家、艺术家直接面对的是他的时代、他的现实。
1970年代末以来具有实验色彩的中国诗人们自觉走上了一条荆棘之路。大家反思生活,学习世界各国文学,发力探索,以求掌握符合我们历史进程的语言方式、文学观念,以求不被甩在世界文学之外(正如我们的改革者和经济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以求最终荣耀我们的文化。这种探索很具体,有时也艰难:它既是朝上的,也是朝下的,也是朝向四方的,最终是朝向未来的。这样的文化逻辑并非说扭转就能够扭转。当然诗人们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语言和观念。我称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时代的写作为“大河拐大弯”。在拐大弯的时候,一部分面向未来的文学写作与当下大众朝向过去的文化诉求不免会形成抗力。大众朝向过去寻求文化榜样和标尺的潮流说明,人们不满意,不满足,不信任现实生活的给与。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题目。由此也就能看出:1,诗人们虽然不能对GDP有所贡献(也不一定),但GDP要安顿人心其实也离不开诗人、作家、艺术家。2,没有1980年代的文化、政治启蒙也就没有今天的GDP。而朝向过去和朝向未来的文化寻索终归会汇合在未来。
我提到了诗人们“朝下”的探索。“朝下”就会遇到屎尿问题,就会被认为是对健康文学、文雅文学、文学的永恒价值的“亵渎”。但“有意思”的是,剔除了屎尿话语、词汇、问题的文学写作和艺术实践,几乎不具备当代意义,因为对当代诗人们来说,题材、语词没有三六九等之分,这是写作的民主性——这当然是过而言之。一般说来,缺乏文雅的人追求文雅,而业已越过文雅门槛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若仍旧只处理文雅,那他要么是由于缺乏创造力而徘徊不前,要么是追求前现代的貔貅品质,要么是已经变成了取悦于人的文化商人。
在今日中国,没有一位真正的诗人不曾学习甚至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学。但诗人们还得尝试使自己的写作获得当代意义。我指的是文学谱系层面上的、审美(包括审丑)层面上的、思想层面上的当代意义,而不是市场层面上的当代意义。当然,也不是说你写到了屎尿写到了性,你就自动获得了当代意义,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些没有写到屎尿性的了不起的作家、诗人自有他们获得当代性的办法,需要我们展开更广泛、更专业的讨论。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屎尿屁书写当然不是诗人、作家们的最终目的所在、最终文学抱负所在。而这个话题的讨论也许属于另一篇文章。
2004年去世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中讨论到“亵渎”的话题:“人民所信仰的东西不容讨论,就像我们并不讨论我们信仰的空气……对公共生活的日常参与以及某种集体热情,能够帮助一个人保持其声称的信念……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城墙的那一种……我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来捍卫我自己……”但是,所有真正的当代中国诗人们感谢米沃什的孤独。这可能是不在文学写作这一领域里摸爬滚打的人们所不了解的情况。专业写作者与仅仅是偶然触碰过文学、诗歌的读者还是有区别的。我这里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道理就像我虽然会骑自行车,但没修过,我对修理自行车这一行完全陌生,我得对修车人喊一声“师傅”。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诗人田原、高星、艺术家姜杰的帮助,在此感谢)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