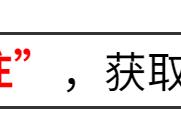史上最纠结的音乐家,大概非柴科夫斯基莫属了。音乐上明明他是自信和执拗的,可是评论一来——欧洲乐评家说他的音乐发臭——他立刻就满腹牢*,天地失色;一部作品明明很喜欢的,可他转身就讨厌起来;他信誓旦旦地说从此不写歌剧了,可是几个月后,一部伟大的歌剧就诞生了。他一边说自己从生理上厌恶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的声音组合,一边却写出了一部题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也就是世人所称的悲歌三重奏。
老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纠结了几团乱麻。一团在他一生未曾谋面的赞助人和精神恋人梅克夫人,她特别喜欢三重奏。另一团在刚刚去世的钢琴家、指挥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他是老柴的伯乐,在他最穷困潦倒时收留了他,聘他为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让他搬进自己的家;他也是他最好的阐释者与传播者,一手把老柴推向乐坛,推向整个欧洲。可两个人也针尖对麦芒,没少说过对方的坏话,直到鲁宾斯坦去世,老柴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最重量级的知音。
悲伤把纠结变成了深切的缅怀。老柴的神来之笔在第二乐章的变奏曲,主题用的是在当年他与鲁宾斯坦在莫斯科郊外郊游时路遇的农民唱的民歌——那个时候,他与鲁宾斯坦正相知甚笃。十几次变奏,钢琴悲怆,大提琴忧郁,小提琴心酸,听起来就像三个性格不同的老朋友,执手相看泪眼,千言万语,切切嘈嘈,从此依依惜别,天各一方。老柴一辈子只写过这唯一的钢琴三重奏,在其中,他似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却耗尽了一生的悲伤。与他众多宏大的悲怆的交响乐和协奏曲相比,这首A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种低调的挥之不去的伤感,有人说它的旋律优美,美得就像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许多时候,我却听出来一种和解——一个音乐家在用他感伤的怀旧,纤弱的自怜,病态的内心分裂,向现实求和,求得宽容、原谅和理解。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老柴为鲁宾斯坦所作的悲歌音犹在耳,十二年之后又轮到别人为他作了挽歌。这个人就是年仅20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就像当年鲁宾斯坦提携自己一样,老柴对青年学生拉赫玛尼诺夫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希望。身为老柴的嫡传弟子,拉氏性格上虽然不像老师那样纠结,但是他的忧郁、深情和丰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闻知噩耗的当晚,他便仿照老柴悼念鲁宾斯坦的方式,谱下题名同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悲歌——D小调钢琴三重奏。他在老柴如歌般宛转悠扬的旋律之上扩张音乐的力度和宽度,忧伤如瀑布,壮怀激烈,悲痛如抽丝,婉转低回。拉氏的神来之笔同样来自第二乐章的变奏,主题旋律来自老柴特别欣赏的一部管弦乐幻想曲《岩石》——在他去世的那年夏天,拉氏把它和《图画交响曲》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老柴当时还开玩笑说:真是后生可畏啊。
两首悲歌连接起来听,像是音符在奔腾运转,将音乐史上的三个大师——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他们的爱恨悲欢,以一种悲情和凄美的方式流成了一条永恒的时间之河。对中年的柴科夫斯基而言,死是一场华美的告别,一种无奈的离殇,“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对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而言,死是泰山崩于前的决绝和悲怆,是一种永恒的苦难,“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徜徉其中,会有种被淹没和击中的感觉,像是一个极度悲伤的人,自始至终都把自己浸泡在眼泪里,从第一击钢琴敲出的泫然欲泣,到中间的潸然泪下,再到最后的一句乐音变成啜泣和呜咽,正如诗人雪莱在一首田园哀歌中所写:“只要天是蓝的,地是绿的/黄昏必然预示夜晚,夜晚必然捧出来日/月复一月悲伤,年复一年哀戚。”然而在悲伤中,你又感到无尽的宽慰,因为其中有朋友与朋友生动的默契,声音与声音的深情对话,生命的流转与延续,音乐的光荣与伟大,它们足以抵消生的短暂和死的无常。
悲歌三重奏有许许多多伟大的录音,我耳边回响的却经常是一个最新的版本——瓦沙·麦斯基的大提琴、瓦吉姆·列宾的小提琴和郎朗的钢琴。三个人,三种乐器,三种声音,不绝如缕的旋律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忧愁、哀伤和安详,他们既是在讲述一个关于友谊、悲伤与感恩的故事,又在慨叹命运、时间和死亡。这是三个音乐家分别是61岁、38岁和27岁。瓦沙·麦斯基、瓦吉姆·列宾都是我喜欢的俄罗斯当代演奏家,他们的演奏细腻、精致和高贵,在他们的伴奏下,郎朗的炫技被充分中和了,竟然散发出了一种深沉和诗意的光芒。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听到的是三个演奏家的相互补充和激发;我也听到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三人行,终有一别焉”——我指的是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也指那个一去永不返的浪漫主义时代。
作者:雷淑容 来源:扬子晚报 编辑:华明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