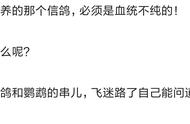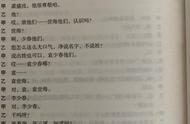相声是什么?似乎一直也没有一个大家都完全认可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心中对相声的认定。其实,从艺术特点上来看,可以说,相声就是“包袱”的艺术。
好的相声,应该多在包袱的艺术性上下功夫
曲艺人提到相声,都会说相声有“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尽管近年来有人在表述时加了一项“演”,但大多数场合里,四门功课还是曲艺人习惯性的说法。四门也好,五门也罢,“逗”,绝对是相声艺术风格的核心呈现,是相声区别于其他艺术的一个主要标志。诚然,其他艺术门类里也有“逗”的成分,尤其大多数曲艺形式里都是含“逗”的。“逗”,不是相声的专利,但唯有在相声里,“逗”是它的灵魂、核心和生命。没有什么都可以,但没有“逗”,那就绝对不是相声了。
“逗”,说白了,就是制造包袱。包袱这个词原本为相声这种艺术形式独有,后来也被其他曲艺形式所采用。而如今,这个词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了,戏剧、影视、文学、主持、演讲等,有时也会弄个包袱。这就要求我们曲艺人,必须要更认真地研究包袱,下气力去做出更精彩的包袱。
相声是包袱的艺术,但是并不是每个包袱都体现出艺术性。好的包袱、高级的包袱,是艺术的、有感染力的、令人回味的。不好的包袱、低级的包袱,虽然也能达到令人发笑的目的,但体现的不是艺术的魅力和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先生等相声艺术家发起对相声艺术的改进,使相声艺术老树发新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绝对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好的相声,就应该多在包袱的艺术性上下功夫。在这方面,马季先生堪称楷模。马季先生一生创作了几百段作品,涉猎多种题材,留下了大量的精品。而尤其难得的是他作品里的包袱,大都极具艺术性。像《找舅舅》《画像》《友谊颂》《山鹰》《海燕》《高原彩虹》等作品,本身并不具备更多的喜剧性,而马季先生仍能表现得那么精彩,努力把每一个包袱都提炼得那么有艺术性,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地研究、学习。
营造好喜剧的情境,是相声创作的第一要素
一段好的相声,首先得有一个最大的包袱,其余的包袱都是在这个最大的包袱身上生长出来的“子包袱”。最大的包袱就是“打造出喜剧的情境”这个核心。一段相声只有设计好了喜剧的情节,营造出浓郁的喜剧氛围,才能使人物和事件都在这个喜剧情境里游走,就会有一个一个的“子包袱”自然生成。在创作相声时最好去选择喜剧性的题材。像《买猴儿》《夜行记》《如此照相》《五官争功》《虎口遐想》《巧立名目》等,题材本身就具有喜剧性。像前面提到的马季先生一些作品,本身喜剧性是缺乏或者说比较弱的,那就必须更加努力地去设计喜剧性的情境和氛围。比如《找舅舅》,歌颂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包头。它的喜剧情境是建立在一个信息错位、时空不对等的基点上。外甥拿着一封信,去找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舅舅。而信里提供的信息和他的一路所见所闻都对不上号,导致一路费尽周折、张冠李戴,于是笑料迭出。《画像》,塑造的是一个劳动模范的形象。马季先生选择了一个画家去为劳动模范画速写,但居然怎么也画不像。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速写,画家都完不成呢?因为他画的过程中那人物老是处于动态,抓不住,这就有意思了。削笔的功夫,他出去了;调色的当空,他又不见了;好容易坐下,心思却不在这。人物处于动态导致画家稳不下心来,笔也不听使唤,笔下的人物一会儿眼睛出框了,一会儿嘴出框了,眼神前后左右乱转。画家的画失败了,但这段相声成功了,一个闲不住的劳动模范形象就这样走进了相声艺术的画廊。
写好相声,还要学好逻辑学和修辞学
笔者认为,无论多少种包袱的技巧,其实大都离不开两门学问,一个是逻辑学,一个是修辞学。
逻辑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思维形式及规律的学说。学习逻辑学的目的是让我们头脑清楚,表达准确。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表达不合逻辑,那势必会产生混淆错综的感觉。而相声里的包袱,则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有意要搞乱欣赏者的思维方向,设法不让听者听得明明白白。但错综的思维又蕴藏着内在的合理元素,然后巧做调整,重归正路,让听者恍然大悟,这便叫作“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好包袱大都是这样产生的。三翻四抖的使用原理就是最典型的,前三翻都是引导观众朝着一个方向思维,最后一抖,打乱了人们正常的思维,出其不意,于是好包袱诞生了。
相声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要研究相声就必须学好修辞学。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学问,也就是对语言进行调整、加工,使语言表达得更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表现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相声之所以能够引人发笑,主要是在利用逻辑原理制造思维混乱的同时,灵活地运用修辞学的辞格来进一步完成包袱。在所有的以文字形式构成的艺术作品中,相声运用辞格的数量最多、频次最高,而且最为灵活多变。和相声运用逻辑学但反其道而行之相同,相声运用修辞学的目的也并不是要把话说得明白或正确。故意把话说得不明白,才能出包袱。
辞格有几十种,常用的有十几种。相声里运用最多的主要有夸张、比喻、谐音、借代、排比、反复等。排第一位的,当属夸张。夸张是一切幽默或喜剧作品的灵魂。夸张导致变形,变形自会引人发笑。最极端的夸张是哈哈镜,相声也可以说是文字的哈哈镜。在一般文体中,夸张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超出一定的限度就会失真。但因为相声是一种独特的漫画性的艺术,所以一般采用高度的夸张。传统相声《扒马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茶碗里淹死菊花青大骡子,烤鸭子飞到餐桌上,蛐蛐的脑袋有剧场那么大个儿,两根须子跟电线杆子一样,那俩眼睛跟聚光灯似的。虽说这些夸张都严重不符合实际,但在此处却恰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惯说大话、爱吹牛皮的人物,人们能够接受也愿意接受。像《买猴儿》《假大空》《吹牛》等相声,正是采用高度的夸张,才成功地塑造出了马大哈、假大空、吹牛者这些典型性人物。相声以讽刺见长,而夸张这种辞格对讽刺某种人物或某种现象最为有力。把一只眼的人弄到部队去看显微镜,把歪脖子的人弄到文工团去拉小提琴等,生活中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事,但这些夸张手法深刻地针砭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让人们在笑声中悟出道理,引起共鸣。通过相声来塑造的这类人物效果让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望尘莫及。
谐音,也是组织包袱的常用辞格。因为谐音最容易产生歧义从而引起人们误解,相声则恰恰利用这一点来制造包袱。相声里的谐音包袱俯拾皆是,数不胜数。比喻在相声里运用也是常见的,“好有一比”“比从何来”这样的台词听众也都不陌生。但相声里的比喻也不是规规矩矩的比喻,往往伴着夸张一同使用。另外排比、反复这样的辞格,往往在三翻四抖时更多地灵活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辞格在一般文体里是不常用的,比如苟简,在相声里运用得巧妙往往能生发出极其精彩的包袱。苟简,意即过分的简略。一般文体里,苟简用得不好会让人莫名其妙。而相声里有些经典的包袱却是苟简的杰作。像马大哈(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假大空(假话、大话、空话)、妻管严(妻子管得太严)等,不仅是精彩的包袱,而且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新词语,这也是相声为丰富民族语言作出的贡献。
作者:崔然
来源: 《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