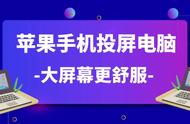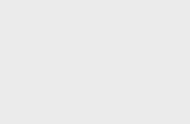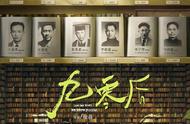该图来自网络
六1986年的某天,也就是距邓稼先逝世前四十六天,杨振宁忽然笑吟吟地出现在放射科特护病房。憔悴不堪的邓稼先神奇般地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和挚友重重地握了下手。笑容可掬的脸上,虽没老杨那样清晰可辨的老年斑,但手背上的斑斑血痕还是让杨振宁的身体打了几个颤。
来之前,杨振宁特意查阅了相关资料,放下资料的他长叹口气:老朋友的病情已不是一般的严重啊!待见到老友时,脸上的表情让人感觉比邓稼先还高兴。语调都不高,但情绪饱满。护士都惊诧于今天老邓的状态如此之好!
病房外,有一些患者在探头,他们关心的当然不是邓稼先,而是早已名震全球的杨振宁。
杨振宁是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在邓稼先眼里,更是个天才的演说家。滔滔不绝,为邓稼先展示五花八门的国际最前沿科学的最新动态。从他嘴里如水银泻地般迸出的高端物理学的名词术语,让旁边的许鹿希无法插话,甚至听都听不懂,后来她干脆就呆坐着,笑眯眯地看着两个老友海阔天空地拉国际家常。
今天的杨振宁还是像往常一样,不停地述说着国际物理学界的最新成果……

该图片来自网络
当他无意中从邓稼先口中得知,刚获得第一届国家科技进步两项特等奖的邓稼先得了两个十元——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时,杨振宁惊呆了:即使奖金比不上他1957年获得7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但堂堂一个国家科技的特等奖,难道只给10块钱?
"不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在场的九院一副院长急忙解释:
七"1985年设立的这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奖金是一万元,《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及《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都是名列第一的,共两万元。您知道,这两个奖不可能奖给某个人,即使邓院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单位里还是得按人头分。九院人多,还自掏腰包垫了十几万,这才按照十元、五元、三元的等级分下去,老邓得的是最高等级,两个十元!"
和过去任何一次交谈相比,杨振宁今天的话最少。更多时候,是用自己的双手轻轻握着邓稼先那双布满血痕的手。
作为西南联大最有名的毕业生,作为比邓稼先大两岁的兄长,杨振宁此刻在想什么呢?
他会不会想到,如果稼先当年听从了同事们的劝告留在美国,生命的走向原本不该这样悲壮。
临走,邓稼先再次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兴致勃勃地拉着老杨照了一张相!并坚持着送客人到电梯旁。
合影的时候,邓稼先想把右边嘴角的血迹擦拟一下,他抬了下手,终于没能办成。

该图片来自网络
站在一旁偷偷抹眼泪的许鹿希十分清楚,邓稼先平素最不喜照相。一旦主动提议,则必有隐情。
跟妻子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的第二天,老邓张罗着拍了张照片,这也是他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隐姓埋名;后来与赵敬璞在罗布泊合影,也是他张罗的;今天,他又喊着要合影。 四十六天之后,老邓撒手西去。
许鹿希送杨振宁下楼时,杨振宁说了这样的话:
"鹿希,我感觉稼先的时日无多了,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许鹿希悲从中来,我要做哪些准备?什么叫做充分的准备?我们婚后的5年,1953到1958年,我们用5年的时光换来28年漫长的等待。
杨振宁一时无语。
后来每当我看到这段对话时,就在想,不知老杨在说这话时是否意识到了,岁月的迁延与人事的无常。待有非常事件在彼此间发生,反而不如陌生人容易面对。

该图片来自网络
八邓稼先去世前夕,他的名字终于被解禁。虽然大部分事迹,还是不能在阳光下流淌,其工作内容和研究成果更是牢牢地被锁在保险柜中。但无论如何,邓稼先算是可以重见天日了。
1986年6月的某一天。邓稼先喘着粗气刚在床上翻了个身,一面容姣好的小护士像蝴蝶一样飞了进来,脸上写满了惊奇、喜悦和崇敬:
"呀,阿姨您也买了报纸呀!您还买了《解放日报》啊!邓叔叔,您太伟大了!您连我们都不告诉啊!"
小护士用力地摇着手中刚刚出版的《人民日报》,精致的蝴蝶结在护士帽里掩盖不住地晃来晃去!
句句都是惊叹,把邓稼先和许鹿希都逗乐了。
许鹿希激动得手一直在颤抖。28年了,中央军委终于对邓稼先解密了,终于可以说丈夫是干什么的了;孩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说爸爸是干什么的了;他们俩一定会大声,大声,再大些声地告诉所有认识的人,我的爸爸叫邓稼先,他是制造原子弹的!他不光制造了原子弹,他还制造了氢弹!他还制造了中子弹!
邓稼先似乎也被这样的情绪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