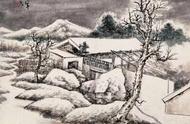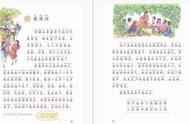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唐 李商隐)
竹坞无尘水槛清,
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一、一首静夜怀人之作本篇为李商隐隔城外宿之时,即景有感,而写怀寄情之作。
从诗题来看,李商隐所宿之骆氏亭,其所在地有数种说法,一说为长庆初年乱臣王庭凑为相士济源骆山人所筑之亭;一说为善事权相李吉甫而受到擢用的骆浚所建之池馆台榭,则其地在长安春明门外。
实则此处未明其确址,或即某骆姓之人营构于某地之林水居所;冯浩则以为应当即是白居易《过骆山人野居小池》所言,在京城东南之蓝溪;或则如杜牧《骆处士墓志铭》所言,乃骆峻栖隐之灞陵东阪。无论位居何处,“骆氏亭”都是一个让诗人立足眺望远方的据点。
从诗中第一联可知,其地临水而筑,周遭绿竹茂生如云,带有城郊水竹林泉的自然景致,而与深居城内的被怀思者之间,乃存在着“迢递隔重城”的距离与阻碍,由此遂奠定了启动相思之翅膀的基础。

而所怀思者乃崔雍(字顺中)、崔衮(字炳章),两人为对李商隐有怜才知遇之恩的兖州观察使崔戎之子,亦为李商隐之从表弟;此处直称其名,可见此诗应是二人尚未入仕之前所作,故冯浩系于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时李商隐二十四岁。
静夜怀人,作为全诗之主旨或内涵,乃是诗中常见的人生体验。在四下无声、万籁皆寂的夜晚,人类的灵魂平息了白日期间扰攘*动的浮躁浑沌,反而得以从窒闷与沉睡中豁然苏醒,以无比清明之灵视逼近心魂的深处,让真正的思念更加活跃而深沉,形诸笔墨之中,便多诚挚恺切之词。

如孟浩然有“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夏日南亭怀辛大》)之句,抒写其寻觅知音之渴切,以至于终夜辗转难眠之情状,笔调坦率热切;而韦应物《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一诗则说:“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以清雅之笔墨叙写悠远之情致,比起孟浩然思念故人时的执着浓烈,显得是淡而有味。
相较之下,李商隐此诗就比较接近韦应物这首诗,同样是秋夜的清景雅致,怀人之情也含蓄蕴藉得多,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寓情于景,借秋气之清澄明净与夜晚之寂然静默,将那一份深幽清明的思念之情委婉表出。
二、竹坞水槛寄相思这首《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既是因夜宿有感而作,故首句之“竹坞无尘水槛清”便先从宿处着墨,所谓“竹坞”,为种植竹林而四面高中央低的地方;“水槛”者,乃临水所建有护栏之台榭。至于诗中分别所下之“无尘”与“清”字,除了描绘出一种清彻不染的视野,而展现骆氏亭竹水幽然的清雅景致之外,仿佛也蕴含着使人心虑澄净的意味。

独自不寐的诗人凭栏悠思,感受到竹林中细叶吟风、水槛外清澈见底的秋景,四周沉降之夜气过滤了空中浮游之埃尘,虽然笼罩在重重秋阴之中,无法领略到“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的盛夏风光。
但在如此水清天凉、清新不染的环境浸润之下,空明的心灵反而使思绪感觉都更为纤细敏锐,而那股油然生起的相思之情,也就显得加倍透明而纯粹,带有晶莹剔透的性质。
然则,这种纯净无垢的相思之情,却不能在无阻无碍的情况下直达怀想的彼岸,那倾心缅怀的对象一方面是如此遥不可及,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是如此山阻水隔,以致对难以促膝接语的双方而言,连相思都是无比之悠长不绝。
三、迢迢万里相思意所谓的“迢递”,与迢迢、迢遥义同,于此便用以点出距离的遥远;而所谓“隔重城”者,则是在距离遥远之外更进一步勾勒出重重的阻碍。
重城,本意是宏伟高大之城,此处指长安,尤其当时长安亦有内城、外城之分,“重”字一方面是实写其境,一方面则是加强了“隔”字的效果,如此一来,这既远且隔的处境,便使得相思的双方落入到更难以相逢的绝望之中。
因此“相思迢递隔重城”这整句诗,可以说是李商隐悲剧情怀的典型表现,对李商隐而言,在理想物最终被触及之前,总不免横隔着重重的障蔽阻绝和遥远难企的空间距离,使他终究徘徊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而只能徒劳地追寻、怅然地远眺,《无题》诗中的“红楼隔雨相望冷”是如此,“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