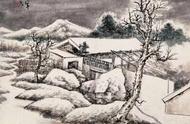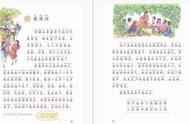就在这特属于李商隐的“远隔情境”之中,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个是导致相思之情更为纯粹,也更为强烈,因为只有纯粹的相思之情才能具备足够的强度超越距离的阻隔。
而另一个结果便是产生深受困陷的悲剧心灵,只能在绝望和孤独里另行开辟存在的意义,那就是以残缺美或凄清的美感作为心灵之安顿寄寓的所在,成为心灭肠断而一无所有的人生中的唯一所有。
四、相思无成,追寻无望于是末联先以“秋阴不散”的物候现象,象征整个外在环境所施加的浓厚压迫,虽无“万里重阴非旧圃”(《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二)、“百里阴云覆雪泥”(《西南行却寄相送者》)的四顾茫茫之意,沉重低迷之心绪却依然自在其中。
然后在秋阴不散的沉沉阴霾之外,诗中又复加以“霜飞晚”的描写,意谓深夜之际开始降霜,则在亭槛边眺望竹林水塘的诗人,应该就可以见到“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的景象,秋寒更深,绝望也更进一层。
而秋阴不散,早已使池中荷花失去阳光而黯然萎落,一旦晚霜飞降,那就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能彻底地红消翠减,再无一丝希望,遗留下来的仅仅只有几枝枯荷,如同夏季挽歌般,勉强作为完全零落前的最后见证。

至于另一种说法,则是将“霜飞晚”的现象放在一年中来衡量,解作今年降霜较晚,如此则语中犹带一丝庆幸,意谓荷花虽已凋落,秋阴亦凝结不散,然而承蒙天意眷顾,今年之秋霜竟然延后飞临,故眼前秋阴虽浓,而池上尚得以残留枯荷。
以上两种说法表面上虽有一幸一忧之别,但其实都无碍于整体诗境之内在脉络,因为夏荷亭亭如碧之美,至秋早已无从得见。
而无论秋霜是当夜初降还是迟迟未至,都还能争取到“留得枯荷听雨声”那短暂而凄清的美感。枯荷残枝,犹可听赏雨声,此中别具慧心之灵思,乃撷取自孟浩然《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的“荷枯雨滴闻”,宋代的欧阳修也于《宿云梦馆》诗中说:“井桐叶落池荷尽,一夜西窗雨不成。”

这些诗句说的都是听觉上虚拟巧喻的感官错觉,而不是风吹雨打的实有其事。风吹枯荷,摩娑如雨,仿佛雨打残枝,淅沥成韵,对诗人而言,风吹枯荷之声比诸雨打残枝之音,彼此实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若就艺术的心灵而言,那“风吹枯荷,摩娑如雨”之感虽然是从虚幻中形成的错觉,比诸“雨打残枝,淅沥成韵”的实况描写却意义重大得多,因为它无形中使得秋风与枯荷的自然关系产生质变,脱化出物我之间崭新的体验与诠释,而提升了人类的感官能力与审美内涵,有如弹奏乐器一般,一旦诗人以灵心慧眼启动想象的指挥棒,秋风与枯荷在摩娑互动的过程中便奏起了前所未有的天籁。

然而,这样的天籁固然是俗眼所难知的艺术意境,是李商隐身为“人类的感官”(维柯形容诗人之用语)的高度发挥,但就李商隐个人而言,这更是他在一无所有中唯一能够自主的创造物。
既然李商隐常常面临相思无成、追寻无望的情况,而落入“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落花》)的无情幻灭,则除了沾衣的眼泪之外,诗人唯有无中生有,才能向不断剥夺他的残酷命运挣回一些人生的幸福。
换言之,在废墟中开创想象的殿堂,虽然不能改变其为废墟的事实,却能够让废墟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处身在废墟中的李商隐唯一能够超越现实的着力点所在。
一如《花下醉》一诗乃是在“客散酒醒深夜后”的满目凄清中,逼出末句的“更持红烛赏残花”,此处“留得枯荷听雨声”(《红楼梦》第四十回林黛玉误引作“留得残荷听雨声”)也是从“秋阴不散霜飞晚”的四顾荒寒里陡然转进的崭新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