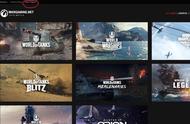在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和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重新塑造宣传的视觉景观的同时,驱动他们的装置的包豪斯美学和民主理想主义的融合也在帮助创造音乐结构和表现的平行转型。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早期职业生涯。凯奇于1912年出生在洛杉矶,父亲是一位发明家,母亲是一位记者,最初希望成为一名牧师。相反,他成为了一位新的艺术家、观众和声音之间关系的建筑师,最终重塑了艺术音乐和社会抗议的规则。就在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将图像从眼高的行中取出并在游客的头顶和脚边展示它们的同时,凯奇正在打破传统音乐音调的结构排列,并寻找新的声音来源。他的乐器包括在琴弦上粘有橡胶碎片的钢琴、收音机、木块和放大的金属片。像《胜利之路》(Road to Victory)的游客一样,凯奇的听众发现自己被潜在重要的标志 — — 声音而不是视觉 — — 所包围,并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正如拜尔扩展了视觉领域一样,凯奇扩展了声音领域,邀请他的听众进入这个领域,并敦促他们将所听到的整合成一个新的、明确的民主心理整体。
多年来,凯奇因其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转向禅宗佛教(Zen Buddhism)和随后使用偶然作曲方法而闻名。但是,几乎十年前,凯奇开始将他的音乐制作定位于与拜尔和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相同的治疗美学。像他们一样,他创造了环境,让人们可以练习当时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民主公民身份的关键心理技能。除了他1944年的作品《音乐之书》(A Book of Music)外,该作品因其“亚洲风格”而被战争情报局定期广播到印度尼西亚,凯奇并没有制作宣传品。相反,在1960年代之前,凯奇一直坚称他或他的音乐与政治无关。
然而,仔细观察他从1930年代末期发明他的“准备钢琴”(prepared piano)到1952年创作他臭名昭著的“无声”(silent)作品4′33″和举办被广泛誉为首次发生的活动时期,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同的画面。在这个时期,凯奇不断地探讨代理和交流的问题。即使美国军队努力解放欧洲免于法西斯主义和后来的朝鲜免于共产主义,凯奇也努力使他的听众免于受制于古典和流行音乐的情感操纵。他试图否定自己对声音的意志和通过声音对听众的意志的强制力。他用与更大的美国反对威权主义斗争相似的术语来描述他的努力。到1952年,对他来说,音乐情况就像十年前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和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的胜利之路一样,是民主政治可能性的一个模型。
约翰·凯奇与声音扩展领域凯奇并不是第一个打破流行音乐和管弦乐音乐传统的作曲家。自19世纪末以来,艺术音乐领域的作曲家一直在挑战管弦乐音乐的不和谐和和谐、宏大的和声和井然有序的对位。在20世纪初的巴黎,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创造了充满甜美的不和谐音符的氛围。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的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完全放弃了大调和小调音阶,开始使用十二音体系进行作曲,并催生了整个现代作曲学派。在美国流行音乐中,布鲁斯音乐家至少已经有一百年在弯曲音符、运行节奏方案和混杂人声和非人声音响。实际上,在中世纪,他们的后代,新世界的吼叫即兴爵士乐手,声称最响亮地民主化了音乐体验。在他们的多种族乐团中,独奏者平等地交换即兴演奏。如果摇摆大乐队是一个工业等级制度,那么bebop乐队就是一个对话,一个声音社区。在他们演奏的小俱乐部中,观众也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
年轻的凯奇被主要由白人和欧洲人组成的艺术音乐世界所吸引。1935年和1936年,他曾短暂地跟随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学习,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作品更多地受到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理念,特别是卢伊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的作品。1913年,鲁索洛写了一篇宣言《噪音艺术》(The Art of Noises),在其中他欢呼所有噪音,特别是机器制造的噪音,作为对传统管弦乐音调的改进。未来主义音乐家应该从周围的嘈杂声中选择声音,他解释道。他们可以敲打木头或金属,打开和关闭机器,或者尖叫、呼喊和嘶嘶作响。最终,他们要将这个声音宇宙排列成新的节奏和和声模式。通过这样做,鲁索洛写道,他们可以教导听众在生活中漫步,享受周围各种声音的乐趣。
在20世纪30年代末,凯奇在洛杉矶短暂地跟随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学习后,找到了旧金山打击乐手露·哈里森(Lou Harrison),并通过他进入了西雅图的康尼舞蹈学校(Cornish School of Dance)。1937年,他在西雅图艺术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他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抱负,这些抱负是由卢伊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设定的:“我相信使用噪音制作音乐将会继续增加,直到我们通过电子乐器制作出音乐为止。”他解释说,作曲家的使命是“捕捉和控制”世界的噪音。特别是,音乐家应该将新的声音再现技术转化为音乐乐器。他兴奋地说,借助“电影唱机”(film phonograph)等技术,“我们可以为爆炸性发动机、风、心跳和山崩创作和演奏四重奏。”
凯奇留在康尼舞蹈学校(Cornish School of Dance)直到1940年春天。在那段时间里,他遇到并开始为舞者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创作,后者最终成为他的终身合作者和伴侣。他还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倾向于未来主义理念。例如,1939年,他创作了《虚构的景观1号》(Imaginary Landscape №1)。这首作品将钢琴和中国钹的声音与唱片机加速和减速的滑音电信号混合在一起。1940年,他创作了一整个作品,围绕着在客厅里发出的敲打和刮擦声音。同年4月,他还开始在钢琴的弦之间插入物品。编舞家西薇拉·福特(Syvilla Fort)要求凯奇为她的舞蹈《狂欢节》(Bacchanal)提供非洲风格的伴奏;他创作了一种类似于传统非洲木琴的现代版本。凯奇想与打击乐团合作,但舞厅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设置鼓组。然而,房间里有一架钢琴。凯奇开始在弦之间插入螺栓和螺丝,并滑入一些橡胶和气象条,直到钢琴成为一种打击乐器 — — 他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使用的“准备好的钢琴”。
在这些情况下,凯奇似乎寻求扩展音乐范围,主要出于审美原因。然而,在二战即将爆发之际,当卢伊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和其他未来主义者拥护法西斯主义时,凯奇开始将他的音乐努力重新塑造为反法西斯解放的新兴语言。在1939年的一篇名为“目标:新音乐,新舞蹈”(Goal: New Music, New Dance)的文章中,他认为:“打击乐是革命。声音和节奏太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制于19世纪音乐的限制。今天,我们正在为它们的解放而战。明天,当我们听到电子音乐时,我们将听到自由。”当他将管弦乐的过去扔进文化垃圾桶,并赞美未来的电子和噪音音乐时,凯奇的言辞方式与卢伊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相似。但是在1939年的美国,为解放被压迫者而战的概念也有另一种价值。由于大量的流行评论,许多人认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是19世纪德国文化的产物。凯奇的修辞暗示,转向打击乐和电子音乐,摆脱19世纪欧洲管弦乐,就是为了代表强壮的美国未来而进行战争。“现代音乐的良心反对者,当然会尝试一切反革命的事情,”他写道。但是没关系:自由的美国军队将继续前进。
笼子和包豪斯在探索噪音的同时,凯奇也接触到了包豪斯。1930年,17岁的凯奇辍学,并在父母的帮助下前往欧洲旅行了一年半。他参观了巴黎,并可能参加了装饰艺术协会展览(Society of Decorative Arts Exhibition),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在其中将马塞尔·布劳尔(Marcel Breuer)的椅子挂在墙上。从巴黎,凯奇前往柏林和德绍包豪斯;当他回到美国时,他带着学校的课程目录回来了。到了1934年,他在为同行的前卫音乐家写的一篇简短文章中,可以听到他倡导包豪斯呼吁集体手工艺和个人自我沉浸的版本。他希望,他写道,很快就会有“音乐时期而不是音乐家,就像哥特式四个世纪的建筑而不是建筑师一样。”
1940年晚春,凯奇离开西雅图前往旧金山湾区,在奥克兰的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与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乔治·凯佩什(Gyorgy Kepes)和其他前包豪斯成员一起教学。这些成员现在在莫霍利所在的芝加哥学院担任常规学年的教师。正如学院的夏季课程目录所解释的那样,夏季学校致力于帮助每个学生成为“综合个体”(integrated individual)。它不仅提供视觉艺术、音乐和舞蹈课程,还提供儿童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工作课程。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米尔斯计划强调经验对塑造个体心理的力量。尽管这种强调起源于约翰·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但它也符合包豪斯的教学传统。因此,学院将包豪斯教师宣传为夏季课程的中心,欢迎莫霍利的到来,并在整个夏季举办了现代艺术博物馆1938年包豪斯展览的巡回版本。
在米尔斯学习期间,莫霍利和六位同事教授了设计学院第一年课程的压缩版,而凯奇则在一个独立的夏季舞蹈项目中教授打击乐,与卢·哈里森(Lou Harrison)一起。凯奇显然认识莫霍利和他的书《新视觉》(The New Vision),这本书是那个夏天所有学生的推荐读物。在米尔斯学习期间,凯奇甚至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音乐中的美国包豪斯设计学院视觉艺术工作的对应物”。1941年,莫霍利给了凯奇在设计学院教授声音工作坊的机会,同年8月,凯奇搬到了芝加哥。凯奇接管了学校的声音工作坊,在那里他教授了五名学生“声音实验”(Sound Experiments)。尽管学校的课程目录描述了这门课程提供了使用手到机器到电影唱机制造新声音的机会,但凯奇的教室与其他教室相邻,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是通过对话来教授这门课程的。
现代世界的声音疗法即便如此,在芝加哥期间,凯奇开始将未来主义者对越来越多噪音的追求转化为更像是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视野扩展的声音版本。正如艺术史学家布兰登·约瑟夫(Branden Joseph)所展示的那样,凯奇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地采用了莫霍利的治疗性沟通理解。就像莫霍利开始将摄影视为扩展观众感官的一种方式,从而帮助他们整合周围工业世界的视觉喧嚣一样,凯奇开始构建可能扩展听众欣赏美感范围的作品,从而帮助他们将现代世界的声音混沌听作音乐。
例如,在1942年初,约翰·凯奇(John Cage)为肯尼斯·帕彻恩(Kenneth Patchen)的广播剧《城市戴着软帽》(The City Wears a Slouch Hat)创作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声音背景。在芝加哥漫步时,凯奇用耳朵聆听了它隆隆的交通声、汽车喇叭和司机的喊叫声,欣赏其中的美感,这与卢伊吉·鲁索洛(Luigi Russolo)对环境噪音的乐趣非常相似。为广播剧创作的乐谱充满了叮当作响的管道声、警笛声、金属的轰鸣声、交通噪音、像警笛一样的乐锯声和在垃圾桶上敲出的甘美兰式的节奏。帕彻恩的剧本讲述了一个在匿名城市中沿着各种道路漫游的流浪者,穿过雨、犯罪现场和电话,凯奇的乐谱为漫游提供了一种听觉上的类比。坐在收音机旁的听众面临着与故事主人公相同的挑战:他们必须漫游城市景观,理解周围随机噪音的意义。
1942年5月31日,CBS在全国范围内播出了同一系列的节目,就像三年前他们播出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的《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一样。威尔斯的节目对许多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让他们因恐惧而逃到街上,而凯奇和肯尼斯·帕彻恩(Kenneth Patchen)的节目则要求他们在静坐中沉浸于声音中。正如凯奇后来所建议的那样,像他为《城市戴着软帽》(The City Wears a Slouch Hat)创作的这首曲子一样,旨在触发人格整合的心理过程。在他于1943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打击乐音乐会后,凯奇向《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这样说:“人们可能会离开我的音乐会,认为他们听到了‘噪音’,但随后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听到意想不到的美。这种音乐对城市居民具有治疗价值……”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凯奇显然已经吸收了莫霍利的观念,即艺术可以用来整合在工业社会中被分裂的个性。同时,凯奇转向治疗也代表了一种明确标记为“民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像“治疗”(therapeutic)这样的词语暗示了一个私人的、医学化的领域,超出了政治领域。但在1940年和1941年,在设计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设计学院的兼职教师来自这里,凯奇也在这里担任伴奏者)周围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保持心理统一和智力独立的能力,特别是在与传媒交流,尤其是大众传媒交流方面,代表了民主国家所依赖的一种自由。能够将听觉或视觉刺激整合成自己制定的整体心理图像,并在此基础上行动,区别于他那些分裂、非理性和大众化的对立面 — — 法西斯主义者,这是自由(也是美国)公民的标志。换句话说,对于凯奇的许多同事来说,治疗性的交流方式(therapeutic modes of communication)有助于创造民主的先决条件。
在凯奇时代,设计学院中最有表达能力的理论家可能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家和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当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建立新包豪斯时,他不仅恢复了德国的预科课程,还聘请了一批当地教授,包括莫里斯,开设“智力整合”(intellectual integration)课程。这些教授将帮助学生想象自己是自由、心理完整的个体(符合包豪斯的原则),他们正在接受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培训(这是访问教授专业的主题)。莫里斯在设计学院讲课数年,包括凯奇在那里的时间。尽管不清楚他是否认识凯奇,但考虑到1941年设计学院和其教师的规模很小,他们从未见面似乎不太可能。
很明显,在几个月前,凯奇为《城市戴着软帽》(The City Wears a Slouch Hat)谱写背景音乐之前,莫里斯在一本名为《自由及其意义》(Freedom, Its Meaning)的著名公众人物写作集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自由机制”(The Mechanism of Freedom)的文章。这篇文章从政治角度阐述了凯奇开始做出的许多美学选择。在莫里斯看来,要“自由”,一个人或物必须能够在没有其他力量阻挡的情况下行动。然而,为了行动,个体必须从呈现为符号的可能性宇宙中选择一个方向 — — 也就是说,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元素,而且是沟通过程的元素。像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和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这样的心理学家一样,莫里斯认为,人通过与他人互动来实现心理个体化。因此,沟通不仅塑造了个人的个性,也塑造了他们享有的生活选择范围。
为了自由,个人不需要享有无限的选择。相反,他们需要享有畅通无阻的选择过程,从摆在他们面前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莫里斯认为,选择能力代表了一种道德理想,同时也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就像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说,他认为小团体提供了一个个体可以通过相互交流实现心理机构的背景。他还建议,小组互动的原则可以在大陆范围内得到发展,当它们得到发展时,它们将更新美国的政治体制。他解释说:“民主……将涉及将小团体之间的道德关系模式扩展到社会关系的整个范围。它的目标是使每个个体都成为社会演变中有意识的决定因素。”(Democracy . . .would involve the extension to social relations at large of the pattern of moral relations between smaller groups of individuals. It would aim to make every individual a consciously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他写道,在这样的系统中,政府不是对个人施加力量,而是塑造个人进行生活选择的符号领域。正如莫里斯所说:“个人思维过程的特征……可以通过操纵个人的社会环境来控制……这个事实的含义是,人们可以被‘制造’自由或被阻止自由。”(The character of the individual’s thought processes . . . is then amenable to control by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individual. . . .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fact is that men can be ‘made’ free or kept from being free.)
凯奇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操纵人们思想的人。然而,他在1940年代的作品和写作中越来越倾向于创造一种声音和文字系统,从中个体可以在每一刻选择自己的美学未来。在战争年代,凯奇努力为自己定义作曲家在声音世界中的适当角色,以及个体音调和声音集体之间、声音和舞蹈之间的适当关系。他还与自己的性取向、在战争中的角色以及更理论层面上的人际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斗争。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已经理解了音乐制作作为一种治疗性劳动的特殊性质;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将治疗性工作的技术和目标与更广泛的尝试融合,以构建一种沟通世界的模型,在这个世界中,困扰他的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紧张关系可能会消失。
二战中的笼子:与机构的斗争1935年,凯奇与阿拉斯加东正教会大主教的艺术女儿克西娅·卡舍瓦洛夫(Xenia Kashevaroff)结婚。1942年6月,她和凯奇搬到了纽约市,进入了一个完全转向战争的大都市。当他们到达时,现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展示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和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的“胜利之路”。军队在中央公园设立了一座高射炮。甚至这个城市自称的中心 — — 大中央车站的主厅也展示了一幅巨大的爱国壁画,其中美国士兵和海员的形象在美国工厂、西部景观和一个被孩子们包围的女人的照片之间站立。在这些场景的上方,一艘巨大的战舰被坦克包围,被战机环绕,驶向远方,上面写着“那个政府……由人民……不会从地球上消失。”(THAT GOVERNMENT . . . BY THE PEOPLE . . .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凯奇不想涉足家国主义或海外战争。1942年12月,当军队试图征召他时,他向征兵局提交了一封医生的信,解释说克西娅·卡舍瓦洛夫(Xenia Kashevaroff)患有肺结核引起的致残腿伤,他是她唯一的支持者。从当时的照片中看,克西娅·卡舍瓦洛夫(Xenia Kashevaroff)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残疾,但是征兵局允许凯奇从事当地图书馆的与战争相关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他在纽约市与战争的接触使他重新思考了公共和私人行动规模之间的关系。在1948年2月在瓦萨学院(Vassar)发表的一次讲座中,后来以“作曲家的自白”(A Composer’s Confessions)为题发表,他这样说:“参与一个国家的复杂情况和一个正常运转的城市让我知道了大事和小事之间的区别,大组织和两个人在一起的小组之间的区别……我的感觉是美丽仍然存在于亲密的情况中;在公共方面想和行动令人印象深刻是相当绝望的。这种态度是逃避现实的,但我认为逃避一个糟糕的情况是明智而不是愚蠢的。”(Being involved in the complexities of a nation at war and a city in business-as-usual led me to know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large things and small things, between big organizations and two people alone in a room together. . . . My feeling was that beauty yet remains in intimate situations; that it is quite hopeless to think and act impressively in public terms. This attitude is escapist, but I believe that it is wise rather than foolish to escape from a bad situation.)
乍一看,这篇文章似乎暗示凯奇逃离了公共的战争世界,转而在私人领域寻求和平,并将追求美丽 — — 通过创作音乐 — — 仅限于亲密的人际关系领域。事实上,凯奇通过自己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来与战争的公共事实进行斗争。当他到达纽约时,凯奇还没有开发出他将因此而成名的偶然创作方法(the chance methods of composition)。在他对噪音的探索中,他已经开始扩展听众可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并开始要求他们积极地将它们编织成有意义的整体。但在战时的纽约,凯奇又转向了更具代表性的音乐创作模式,并试图有意地影响他的观众的情感。
例如,1942年他创作了《虚构的风景№3》(Imaginary Landscape №3)。这首曲子以锡制表面的快速敲击和电子警报器的升降声开头;一种有力的节奏以单一的警报器为高潮,然后是更多的警报器。实际上,这可能就是伦敦空袭的声音景观。正如记者卡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后来报道的那样,凯奇实际上是将这首曲子写成了战斗的声音类比。这样,凯奇构建了一个声音表现,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将他对战争的感受传递到听众的心中。在《虚构的风景№3》(Imaginary Landscape №3)之后,他为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的一支舞蹈创作了一首准备好的钢琴曲,名为《以大屠*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Holocaust) — — 这个标题本身就反映了凯奇正在努力寻找一种音乐语言,以将战争的暴力传达给他的听众。在1943年,他重新制作了一首早期的打击乐曲,并创作了《爱情》 (Amores)— — 一部由敲击、沙沙声和偶尔的钟声组成的四部曲,比《虚构的风景№3》慢得多、安静得多。凯奇在1943年2月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演奏了《爱情》。他告诉《时代》的记者:“我的作品《爱情》旨在唤起爱的感觉。”
凭借着《爱情》、《以大屠*之名》和《虚构的风景№3》等作品,凯奇旨在通过操纵声音来操纵听众的情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会找到无数种方式来否认他对作曲过程的控制,从把他的音乐选择交给《易经》到简单地指定一段时间来填充任何发生在演出场地的声音。但在1943年,他仍在试图用声音来表现经验并传达它。问题在于这并没有起作用。“我注意到,当我认真写下悲伤的东西时,人们和评论家往往会笑,”他后来回忆道。“我决定放弃作曲,除非我能找到一个比传达更好的理由。”
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包括他自己的,凯奇在东方哲学中找到了理由。在1943年至1952年期间,他放弃了一种表达性的发送者-消息-接收者模式的音乐制作方式,转向了一种环境、周围为基础的模式,既否认了他自己作为作曲家的代理权,又旨在增强他的听众的代理权。这个转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43年至1948年之间,当时凯奇朝着艺术史学家莫伊拉·罗斯(Moira Roth)所称的“冷漠美学”(aesthetic of indifference)创作代理权的模式努力;第二个阶段,凯奇完全拥抱了不确定性,发生在1948年至1952年之间。根据凯奇和大多数学者的说法,他在1943年至1945年之间经历了一段心理困扰的时期。凯奇公开将他的不幸归因于他未能有效地传达他的音乐,然而这些年也见证了他与克西娅·卡舍瓦洛夫(Xenia Kashevaroff)的十年婚姻的结束以及他接受了与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的同性恋关系。凯奇寻求了多种方向的救济,包括心理分析。“当我去见分析师进行某种初步会议时,”凯奇后来回忆道,“他说,‘我会让你写比现在更多的音乐。’我说,‘天哪!我已经觉得自己写得太多了。’他的承诺让我失望。”
代替精神分析,凯奇解释说他拥抱了“东方哲学”(oriental philosophy)。他第一次接触到印度艺术史学家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eraswamy)的著作是在他和克西娅抵达纽约后不久,他们曾短暂地与学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住在一起;1943年,卢·哈里森(Lou Harrison)向凯奇展示了《易经》。但据凯奇说,与年轻的印度女子吉塔·萨拉巴伊(Geeta Sarabhai)的一次相遇才开始改变他的作品和他对音乐与心灵之间适当关系的理解。萨拉巴伊是由艺术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介绍给凯奇的。他们同意交换课程,凯奇教萨拉巴伊作曲,萨拉巴伊教凯奇印度音乐和哲学。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他们每周见面几次,有时还有卢·哈里森一起。从萨拉巴伊那里,凯奇学到了印度音乐处理“永恒的情感” — — “英勇、情色、奇妙、欢乐、悲伤、恐惧、愤怒、可憎和它们共同趋向平静”的方式。他还声称学到了“音乐的目的是调节和使头脑清醒,从而使其容易受到神圣的影响,并将一个人的感情提升到善良”。
当萨拉巴伊回到印度时,她给了凯奇一本《斯里·拉马克里希纳的福音》(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凯奇狂读有关神秘主义、心理学和东方的书籍。他重新阅读库马拉斯瓦米的著作,并研究了卡尔·荣格的人格理论、迈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著作,最终阅读了老子的《道德经》。每一本书都似乎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转向“冷漠”而非有意识的交流是实现内心平静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对于作曲家还是观众。到了1948年,凯奇开始echo库马拉斯瓦米的话,认为创作艺术就是“模仿自然的运作方式”。对于凯奇来说,模仿自然意味着要远离19世纪管弦乐音乐的“大事”,远离战时的公共生活,甚至远离和声,因为凯奇认为和声已经“成为西方商业主义的工具”。取而代之的是,凯奇试图找到永恒情感的音乐等价物,特别是它们倾向于的平静状态。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变得对他的作品产生的声音模式漠不关心,甚至与制作过程保持独立。在作曲的层面上,这意味着他将转向节奏作为组织声音的手段,而不是和声。如果和声结构将音乐演奏者集中于单一的表现性目标,那么凯奇认为节奏结构则在声音之间开放了空间,并允许在作品中出现几乎普遍的音调范围。对于凯奇来说,最重要的是,节奏结构使作曲家对作品的整体形状负责,但不一定对可能在其中产生的个别声音负责。
正如音乐学家大卫·尼科尔斯(David Nicholls)所说,一件作品特别有效地展现了凯奇在这个时期与自己的代理权斗争的结果:为准备钢琴而作的奏鸣曲和插曲(Sonatas and Interludes)。凯奇从1946年2月开始创作这首曲子,历时两年,最终包含了20个乐章,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正如凯奇所描述的那样,这首曲子似乎属于他早期作品的情感表达线。他从库马拉斯瓦米的书《湿婆之舞》(The Dance of Shiva)中汲取灵感,并试图“用音乐表达”它所描述的印度教传统的“永恒情感”。然而,正如尼科尔斯所示,凯奇并没有将特定的情感映射到个别乐章上。即使是作品中的每个元素都有自己的情感色彩,作品整体并没有表达永恒情感的范围,而是构建了一个声音模式的脚手架,听众必须在其上构建自己的情感反应。换句话说,凯奇以这样的方式构建了这首曲子,以便他可以为听众提供感受永恒情感的机会,即使他自己对他们是否实际上感受到这些情感并不在意。
同时,凯奇开发了一种方法,可以配置作曲和钢琴,使它们各自具有表现力。凯奇后来解释说,他以更多或更少的数学模式构建了这首曲子:“前八首,第十二首和最后四首奏鸣曲采用不同比例的AABB节奏结构,而前两个插曲没有结构重复。这种差异在最后两个插曲和第九到第十一首奏鸣曲中得到了交换,它们分别有前奏,插曲和后奏。准备钢琴相对复杂,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完成。”换句话说,凯奇建立了一种比例系统,并将其排列到一个机器 — — 准备好的钢琴上,该钢琴可以同时产生所需的广泛比例,并且由于其弦之间的螺母和毡,还可以引入更多或更少的随机音调。
在1949年的文章《现代音乐的先驱者》(Forerunners of Modern Music)中,凯奇试图概述《奏鸣曲与插曲》(Sonatas and Interludes)背后的理论基础。他在那里写道,“音乐的目的”是“启动灵魂。灵魂是不同元素的聚合者(迈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它的工作充满了平静和爱。”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无调性声音多样性的节奏结构具有精神目的:它打开了听众的耳朵,让他们听到自然的随机性和音乐消失了用于有意传递情感信息和操纵观众的世界的声音。凯奇已经建立了一种他当时认为是自我否定的实践,代替了自我表达。凯奇已经将他的创造力至少部分地交给了音乐机器和组织机器与表演者关系的系统。他通过构建可能限制它产生的音调范围的过程的竞技场来构成了一种声音系统。同时,他让听众自由选择这些音调以获得愉悦。他认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是精神上的转化:“音乐的内心之路现在通过自我否定来引导自我认识,它的世界之路同样引导自我无私。”
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正是这种精神转变成为了凯奇后来转向不确定性的根源。但在他谈论路径和自我认识的同一篇文章中,凯奇也用更政治的术语来描述自己。他写道,无调性是一种克服和维持更“模糊音调状态”的方式。在这种状态下,决定音调情感影响的责任从和声制作者(无论是19世纪还是现在)转移到了听众身上。事实上,凯奇写道,作曲家的工作就是在其中建立一个新的环境,使这种更分散、个体化的代理权转移得以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作曲家类似于战后的城市规划师。在声音世界中,凯奇认为,“就像在一座被轰炸的城市中重新建造的机会一样。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找到勇气和必要感。”
凯奇的比喻隐含了微妙但重要的转变。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接受了莫霍利的艺术理解,认为艺术是治愈被工业社会破碎的心灵的一种方式。在这里,1949年初,他将音乐创作视为战后重建的实践。他的措辞可能反映了他私人的渴望,即在早期婚姻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生活,但它也反映了凯奇非常清楚的战后政治氛围。在1940年代中期,凯奇回忆说,转向东方的美学意味着面对由最近与日本的冲突塑造的普遍观点:“在战争结束后,或者紧接着战争之后……人们仍然说东方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分离的实体。西方人没有权利宣扬东方哲学。正是由于库马拉斯瓦米的影响,我开始怀疑这不是真的,东方思想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比欧洲思想不可接受。”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最终成为他1959年的“无题演讲”(Lecture on Nothing),凯奇甚至更进一步,将自己描绘为在美学领域为自由而战:“我发现我更喜欢噪音,甚至比我喜欢音程还要多。我喜欢噪音就像我喜欢单个声音一样。噪音也曾被歧视过;作为美国人,我被训练成感性的,我为噪音而战。我喜欢站在弱者这一边。”
在凯奇用战争塑造的术语描述他的工作的同时,他试图将他几年前与莫霍利一起开发的治疗取向应用于战后环境。在他的文章“作曲家的自白”(A Composer’s Confessions)中,凯奇再次将音乐视为心理整合的工具。
我开始阅读荣格有关人格整合的著作。每个人格都有两个主要部分:意识和无意识,而这些部分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分散、分裂成无数种方式和方向。音乐的作用,就像任何其他健康的职业一样,是帮助将这些分离的部分重新整合在一起。音乐通过提供一个时空意识消失的时刻,使组成个体的多样化元素得以整合,从而使个体成为一个整体。
尽管更加关注整体心理学的莫霍利不会引用荣格,但凯奇想要创造一个美学背景来促进心理整合的愿望却呼应了莫霍利的治疗理念。这也反映了凯奇对战争的反应。1942年,《城市戴着软帽》(The City Wears a Slouch Hat)的混沌声音源于芝加哥作为一个工业时代城市的事实。汽车引擎、警笛声,甚至是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所有这些声音都是现代大规模制造业所可能产生的。到了1940年代末,凯奇几乎不再谈论工业城市,而是谈论“大事物”和“小事物”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音乐应该如何与两者相关。他在1940年代末认为,音乐制作者必须帮助听众摆脱流行音乐中故意制造的公共和谐。听众不应该成为来自遥远权力的情感信息的被动大众接收者。“这是一个古老的制作和使用音乐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变得更加整合,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他解释道。为此,人们需要进行一种美学国际关系。人们需要接触亚洲,特别是新独立的印度国,并采用凯奇认为是其文化特定形式的创造性机构。“如果一个人像东方人所说的那样无私地制作音乐,也就是说,不关心金钱或名声,而只是出于制作音乐的热爱,那么这是一种整合活动,他将会在生活中找到完整和满足的时刻。”
黑山学院与不确定性的追求凯奇很快将这个愿景转化为对等级音乐秩序的反抗,他认为其表演风格和声音结构越来越像法西斯主义的声音类比物。纳粹德国的独裁者通过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来强制执行他们的权威。在威权社会中,指挥线和通信线是平行的,并且都从上到下流动。在民主社会中,就像在民主心灵中一样,平等的关系得到了维护。他们可以通过一种通信方式来维持,其中个人和国家都为一个词汇和图像领域做出贡献,自己选择相信谁并与谁交往,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自由状态。
在1940年代的后半段,这种逻辑也渗透到了凯奇的写作和作曲中。他也致力于打开听众的感官,特别是对于那些以前被宣布为音乐敌人的声音。他也旨在创造一个跨越国际界限的机会领域,通过制作桥接东西方的作品来实现。他也是一位专家,尽管是美学专家而不是社会科学专家,因此,他致力于建立组织系统,使个体听众可以在他通过作曲创造的领域中自由地移动,学习如何体验音乐厅外更广阔的世界。
将凯奇的表演想象为政治行为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些奇怪。但如果是这样,那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社会、心理和美学关注在这个时期的重叠程度。这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尤其如此。今天,大多数作家将这个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农村山区的小学院记忆为一所艺术学校。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校友名单读起来就像是战后美国艺术和文学的名人录。在1933年成立和1956年关闭之间,学校聘请了从包豪斯难民约瑟夫(Josef)和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到散文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和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教师。学生包括画家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雕塑家肯尼斯·斯内尔森(Kenneth Snelson)、电影制片人斯坦·范德比克(Stan VanDerBeek)和作家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Francine du Plessix Gray)。特别是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尽管相对孤立和经常财政不稳定,学院汇聚了一代在大萧条或战间期欧洲成长的艺术家和一批年轻的美国人,他们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之后,将塑造未来三十年的前卫艺术。
很少有人记得,像现代艺术博物馆或米尔斯学院这样的艺术创新中心一样,黑山学院也拥抱了二战期间推动民主士气的人格理论。黑山学院由约翰·赖斯(John Rice)创立,他是一位充满魅力和争议的古典学教授,离开了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的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并带走了几位同事。赖斯和他的同志们希望建立一所学校,以约翰·杜威阐述的实用教育原则为基础:学生将通过共同的经验协作学习,从而获得学术知识和个人洞察力。他们将艺术置于课程的中心,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艺术提供了个人心理发展所依赖的互动体验。就在学院开学前,赖斯和一位同事向玛格丽特·刘易斯汉(Margaret Lewisohn)求助,她的丈夫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任职,同时也是该博物馆的建筑策展人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他们想知道是否可以推荐一位教授来领导学校在艺术方面的努力。约翰逊推荐了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尽管当时他不会说英语,但阿尔伯斯曾在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的指导下教授包豪斯的主要课程。他也正在寻求从纳粹德国移民。
当阿尔伯斯来到美国时,赖斯聘请他管理一所已经专注于以艺术为基础的个性发展和民主社区的学校。阿尔伯斯认识到这两个元素都是包豪斯的熟悉元素。但在黑山学院,莱斯和他的同事们用特定的美国术语来表达他们的追求。1935年秋天,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一位通讯员来到黑山学院,并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他经常与赖斯会面,并在笔记本中记录下他的想法。在1936年的一篇哈珀杂志文章中,他报道说,赖斯告诉他:“大学的任务是使年轻人达到智力和情感成熟;智力,我指的是智力和情感之间微妙的平衡。”他建议这项工作对民主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赖斯解释说:“我在很大程度上责怪希特勒主义是由于德国教育造成的。”德国学校专注于“把头脑塞满事实,从而为希特勒准备了一群情感幼儿,准备屈服于他的煽动。”在1942年的回忆录(I Came Ou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赖斯回忆说,从一开始,“黑山学院就是为了民主教育而设立的。”它的教室和社区需要模拟民主进程。艺术将提供锻造新型公民的热度。赖斯写道:“我们说,民主人必须是艺术家。我们说,民主人的完整性是艺术家的完整性,是关系的完整性。”
到了1940年代末,赖斯已经离开了。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因与一名学生有染而被逐出学校,同时因其有时高傲的风格而得罪了许多教职员工。尽管如此,他对民主和培养亲民主个性的强调仍然存在。1946年6月,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和未来的社会学家查尔斯·珀罗(Charles Perrow)搭便车来到黑山,并在那里住了两年。珀罗回忆说,当他到达北卡罗来纳州时,“黑山是……国家对民主治理、文化创新和性自由的即将关注的全息图像。”随着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结束,黑山的学生们试图建立一个民主社区,就像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所描述的开放自我的开放社会一样。他们还在应对生活在“圣经带”中的要求。他们沉浸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逃离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卡伦·霍尼(Karen Horney)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以及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他们容忍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即使周围的城镇不允许。早在1944年,他们就试图整合学生群体,那一年夏季学期就录取了黑人学生,后来在1945年的常规学年也是如此。到了1940年代末,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看来,学院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更民主的战后美国社会的原型。
那个社会的核心是一种新型人:拥有整合、平衡心理的人。从最早的日子起,这所学院就通过培训学生不仅在艺术方面,还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来培养这种心态。在战后的几年里,教师们提供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学、生物学、化学、数学、几种外语,甚至还有速记和打字,这都得益于学院的办公室经理。尽管黑山学院从未获得认证,很少有学生在这里呆超过两年,但它与美国一些最精英的大学,包括哈佛、耶鲁和拉德克利夫,保持着紧密联系。
1945年,学院与哈佛的联系帮助加强了其对民主和个性关系的关注。那一年,学校聘请了约翰·沃伦(John Wallen),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他的导师是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来教授心理学课程。在1940年代中期,奥尔波特的写作和研究开始集中于通过心理干预减少社会紧张局势。例如,在1944年,奥尔波特和他的学生里奥·波斯特曼(Leo Postman)召集了一群波士顿警察,以便让他们面对自己的种族主义并消除它。奥尔波特已经认识到,个人个性和良好社会的发展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当沃伦来到黑山学院时,他带来了奥尔波特的信念,即多向、人际交流可以同时赋予个人力量并建立更具凝聚力的社区。在他的心理学课程中,沃伦教授了弗洛姆和霍尼,以及他们的观念,即与弗洛伊德相反,童年并不会不可逆地塑造个人心理。个性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塑造和重塑,社会也是如此。为了证明这一点,沃伦将他的一个班级变成了一个集体自我分析。学生们要观察彼此和沃伦本人的关系,从而更加了解群体心理学的一般真理。在他的课外时间,就像戈登·奥尔波特试图为波士顿警察进行一种群体治疗一样,沃伦试图组织学生成立团队,以便走向周围的山丘,激励当地居民采取社区行动。
对于沃伦和许多学生来说,他们聚集在他的魅力愿景下,“群体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他们刚刚经历的各种全球冲突。查尔斯·珀罗(Charles Perrow)问道:“聪明而有创造力的个人能否聚集在一起,还是注定会被不可避免的人类邪恶所毁灭?这听起来很重要,但它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另一方面,对于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和更加关注艺术的学生来说,自我和社会改进的道路将建立在艺术劳动之上。正如珀罗所回忆的那样:“此时的黑山学院被分为两派。一方面是社区和民主治理的理念,它在黑山学院目录中宣布,但实际上是由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约翰·沃伦(John Wallen)首次提出的。另一方面是艺术美学成就的理念,这将使治理问题自行解决,也就是说,那些实现理想的人将成为当局。”
约翰·凯奇为萨蒂(Satie)辩护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冲突在黑山持续了两年多。它主导了有关课程和招聘的讨论,并在有关学院食品计划、建筑甚至围栏的谈话中出现。到1948年初,艺术倡导者已经基本上打败了沃伦派,并且沃伦已经离开了校园。就在他离开几周后,约翰·凯奇和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来到黑山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他们正在前往西海岸进行他们定期的巡回演出,并询问是否可以停留几天进行表演和讲座。学院很高兴有他们的到来,尽管没有提供报酬。在他们逗留期间,坎宁安跳舞,凯奇首次公开演奏了他的奏鸣曲和插曲(Sonatas and Interludes)。黑山学院社区非常兴奋。对许多人来说,凯奇和坎宁安看起来像是志同道合的灵魂。正如一位学生所说,他们的访问“在创造和回应方面照亮了学院”,并提供了一个场合,“一个人自己最深的目标被另一个人的活动或言语所支持”。
也许他们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解决了社会活动和艺术创作之间的校园冲突。例如,在演奏奏鸣曲和插曲(Sonatas and Interludes)之后,凯奇发表了一篇关于他作品性质的演讲。他的言论直接涉及到学院的关切。他认为,音乐艺术的最高用途就像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一样,通过作品的秩序来整合一个人的全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凯奇同时验证了艺术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活动的力量,描绘了它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暗示它可以产生社会秩序的影响,这通常被归因于社区组织。艺术家的抱负不必与社区建设者的目标相冲突;相反,它们可以是同一件事。因为艺术作为一种心理整合的力量,甚至可以引发新的社会秩序。凯奇告诉观众:“由于整合可以在陌生人中认出自己,一个新的社会可能有一天会通过我们自我协调从目前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中慢慢形成。它始于音乐,终于共同的人性。”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凯奇所说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是什么意思,但当时在黑山学院的观众可能会认为他指的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两者兼有:第一,工业世界的混乱,而莫霍利和其他包豪斯校友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艺术可能是治疗的方法;第二,当时在校园和全球政治讨论中回响的威权主义和民主力量之间的深刻心理社会分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自我协调”(self-won coordination)这个短语都可以描述同一时刻由奥尔波特、斯塔克·沙利文(Stack Sullivan)、莫里斯和其他人推广的民主社会。对于社会科学家和凯奇来说,要实现心理整合就是要将自己的心灵重新赢回。然后,人们可以离开以自上而下的人类群体控制为组织形式的社会,进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心理上完整的个体可以相互认识,因此作为平等者协调他们的互动。
黑山学院的学生们非常喜欢凯奇和坎宁安,他们在离开时送给他们食物、画作和素描。约瑟夫·阿尔伯斯对他们的表现印象深刻,邀请他们回来参加当年的夏季课程。与核心课程一样,黑山学院的夏季课程也偏向于艺术,但也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例如,在1947年的夏季,埃里克·科勒(Eric Kohler)就讲授了一系列特别受欢迎的主题演讲,包括“世界政府”和“个人危机”。在1948年的夏季,莱奥(Reichian)心理学家和常驻黑山教授唐纳德·卡尔霍恩(Donald Calhoun)教授了“文化与个性”和“弗洛伊德主义与社会科学”,而联合国新闻编辑比阿特丽斯·皮特尼·兰布(Beatrice Pitney Lamb)则讲授了“苏美关系与联合国”的课程。
1948年,除了这些相对国际主义的课程,阿尔伯斯还组建了一个新的教师团队。整个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拥有欧洲和美国教师的混合,大多数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很有名。在艺术和音乐方面,许多教授来自德国。然而,那个夏天,阿尔伯斯招募了半打年轻而极具创新精神的美国人。在一个星期内,学生可以跟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一起学习舞蹈,跟约翰·凯奇一起学习音乐,跟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一起学习绘画,跟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一起学习建筑,还可以跟约瑟夫·阿尔伯斯一起学习色彩理论。他们还可以与一群天赋异禀的同龄人一起工作。那个夏天的学生包括雕塑家肯尼思·斯内尔森(Kenneth Snelson)、未来的电影导演亚瑟·彭恩(Arthur Penn)和未来的建筑师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以及其他近70人。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对美国艺术界未来二十年产生了非凡的影响,间接地也影响了美国反文化运动。那个夏天,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一组学生建造了他的第一个测地式穹顶(geodesic domes),这种建筑形式将在未来的几年里既用于美国的宣传展览,也用于回归自然的公社。凯奇和富勒成为了朋友,他们的相互喜爱将塑造他们的工作和公众形象,影响着艺术家和反文化叛逆者的理想。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和他的妻子维拉(Vera)与凯奇和坎宁安关系密切,后来资助了凯奇在录音带上制作音乐的首次尝试,即1952年的《威廉姆斯混音》(Williams Mix)。威廉姆斯夫妇还与凯奇和前黑山教授M.C.理查兹(M. C. Richards)一起创立了门山合作社社区(Gate Hill Cooperative community),这是一个集体生活的实验,比回归自然的运动早了十年。
查尔斯·珀罗(Charles Perrow)在夏季逗留期间回忆说,夏季课程“闪耀着一种使常规课程的基本冲突突然显得肤浅的光辉。”对于凯奇来说,夏季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对音乐中的和谐一致性进行攻击,并且在他的观众中,许多人认为这是对最近让德国向世界施加其自己的黑暗统一愿景的国家的攻击。在整个夏季期间,凯奇演奏了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的25个半小时作品。在简短介绍音乐和演讲萨蒂后,凯奇会弹钢琴,有时在餐厅里,有时在他的小屋里,而学生和教职员工则在外面的草坪上休息。在同样的几周里,一位德国出生的键盘手和新的黑山教授埃尔温·博德基(Erwin Bodky)提供了一场有关贝多芬音乐的研讨会。在周六晚上,他还会演奏其他古典音乐。直到夏季中期左右,凯奇和博德基的两个系列似乎没有冲突。但是有一天晚上,凯奇在演出前发表了一篇演讲,很快就让整个校园陷入了混乱。
这次演讲后来以《萨蒂的辩护》( Defense of Satie)为题发表。在演讲中,凯奇攻击了和声,赞扬时间作为音乐的适当组织原则。他认为,贝多芬这样的人物,以其强调表现力和和声统一,已经让音乐走上了歧途。“贝多芬代表了船只从其自然平稳的航向上最剧烈的偏离,”凯奇大声说道。凯奇认为,音乐应该朝着印度的方向发展,那里的节奏和时间长度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音乐的结构,以及朝着法国的方向,萨蒂在西方环境中展示了时间长度的力量。在凯奇的描述中,萨蒂和匿名的印度人都没有必要将单一的统一声音模式强加给他们的听众。相反,每个人都构建了一个形式(由时间长度构成),在这个形式中,各种声音都可以相互遇见。“在萨蒂的连续性中,民间曲调、音乐陈词滥调和各种荒谬的东西都出现了,”凯奇写道。“他不会因为欢迎它们进入他建造的房子而感到羞耻:它的结构是坚固的。”
仅仅三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凯奇的听众,特别是在场的许多德国难民,无法忽视他言论中的政治色彩。德国人贝多芬将声音绑在一起,使它们行进到表达他的意愿的单一目的。凯奇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扭曲并几乎摧毁了西方音乐的自然文化。法国代表萨蒂和来自新获得自由的印度的无名音乐家,没有强加自己的意志。相反,他们建立了坚实的结构,让声音自由。贝多芬音乐会的听众被声音去个性化并集中到步调一致的和声中,是音乐的闪电战的受害者,凯奇暗示。另一方面,萨蒂的自由法国听众或印度的自由公民,被声音包围,他们可以在其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他们的内心生活。为了避免他的听众误解他更大的目的,凯奇在讲话结束时宣布:“现在可以建议音乐的最终意义:它是将本质上矛盾的元素带入共存的问题……也就是,法律元素……[和]自由元素……整个过程形成一个有机实体。因此,音乐是一个与个性整合问题平行的问题: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中,这是意识和无意识心灵的共存,法律和自由,在随机的世界情况下。好的音乐可以作为良好生活的指南。”
凭借这些话,凯奇唤起了对心理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理解,这在社会科学的辩论中几乎同时占据主导地位。像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斯塔克·沙利文(Stack Sullivan)和甚至Horkheimer一样,凯奇认为个体心理必须将意识和无意识元素融合成有机整体,一旦做到了,个体就能过得好。对于凯奇和社会科学家来说,过得好意味着生活在一个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立行动的社会中,尽管也要在专家设定的边界内行动。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他的著作中,约翰·沃伦(John Wallen)在黑山学院,都希望通过建立小组来改造个体人格,使成员之间可以根据手头实验或项目的限制相互沟通。凯奇希望通过建造坚固的房屋,让多样化的声音在统一的形式中生存,而不是通过统一声音并将其对抗耳朵来转变他的听众。在这个意义上,凯奇的音乐制作不仅与个性的整合相似,而且与一种表面上民主的创建和管理整个社会的模式相似。整合个性和创建容忍个体多样性的社会,这些项目在1948年同样困扰着凯奇和关注建立新的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和外交官。那个夏天在黑山学院,凯奇的表演和整个学院都成为了原型 — — 小规模的组织权力实验,回响着并在一些参与者的心中,可能有一天会塑造正在进行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治实验。
声音的世界,自由的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凯奇将他在《萨蒂的辩护》( Defense of Satie)中所赞扬的策略扩展为他最终成为最著名的美学原则和实践的一部分:“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至少在早期阶段,不确定性通常指使用凯奇所称的“偶然操作”(chance operations)来制作音乐。例如,在1952年的一篇文章中,凯奇解释说,他最近使用《易经》的帮助为12个收音机创作了他的《虚构的景观IV号》(Imaginary Landscape No.IV)。与他早期的作品一样,凯奇将作品组织成时间长度,每个时间长度都可以作为其他时间长度的结构微观世界,这得益于他设计的平方根公式。然而,这一次,他还抛掷了三枚硬币,以获得《易经》的神谕建议。这些硬币产生了六十四卦的图案,凯奇随后使用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变换将其转换为声音的模式。基本上,他通过一系列随机的呼吁来确定了作品的结构。
多年来,传记作者和音乐学家通常将凯奇采用偶然方法的雇用归因于他与禅宗佛教的同时遭遇。大约在1950年左右,凯奇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禅宗大师铃木大拙(D. T. Suzuki)上课。这些课程,就像他早期阅读的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和阿南达·库玛拉斯瓦米(Ananda Coomeraswamy)一样,强调否定自我,开放感官,体验整个宇宙。对于铃木来说,宇宙是一个整体,发生在其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好或坏的。在这些条件下,意图不再重要。正如凯奇所说的那样,“‘错误’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旦发生了任何事情,它就是真实的。”
然而,即使他的转向不确定性反映了他与铃木的接触,它也表达了凯奇与社会科学家共同担忧的权力和沟通焦虑。例如,他写道,在《虚构的景观IV号》(Imaginary Landscape No.IV)的情况下,易经使得“可以制作一种音乐作品,其连续性不受个人品味和记忆(心理学)以及艺术文学和‘传统’的影响。声音进入以自身为中心的时间空间,不受任何抽象概念的限制。”换句话说,作曲的偶然方法使声音摆脱了服从独裁作曲家的意愿甚至是遵循压迫性文化规范的需要。声音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或者,用20世纪40年代末的乌托邦政治语言来说,它们可以在作品的统一中享受自己的多样性。
在1958年在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一次讲座中,后来发表为《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凯奇详细分析了偶然性在他的作品中的作用,并承认了他的美学对政治的影响。他将自己的新方法描述为一种平衡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组织声音的方式。凯奇冷静地审视了自己的作品,特别是被许多人认为是他第一部完全不确定的作品《变化之音乐》(Music of Changes),他担心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位美学独裁者。凯奇借助《易经》创作了这首曲子,但他解释说,这首曲子只是在创作过程中使用了偶然性程序方面是不确定的:“虽然偶然性操作带来了作品的决定,但这些操作在演奏中是不可用的。在《变化之音乐》(Music of Changes)的情况下,演奏者的作用就像是承包商,按照建筑师的蓝图建造一座建筑。”作曲家可能会享受自由,将自己与“任何可能性”联系起来,凯奇写道。但演奏者在作品下受苦。因为他“无法从自己的中心表演”,演奏者“必须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愿望融入到作曲家的中心中”。也就是说,他必须将自己的愿望与作曲家的愿望融合在一起,尽管作曲家可能使用了偶然的方法,但他还是成功地创造了一组几乎完全限制了演奏者的音乐指令。凯奇总结道:“这些声音虽然只是声音,但它们聚集在一起控制了一个人,演奏者,这使得这个作品具有弗兰肯斯坦怪物的惊人特点。这种情况当然是西方音乐的特点,其杰作是最令人恐惧的例子,当涉及到人道交流时,只会从弗兰肯斯坦怪物转向独裁者。”
凯奇担心他的音乐可能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这反映了他与禅宗无关的担忧。在本文中,他探讨了自己的作品以及卡尔海因茨·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和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等现代主义者的作品,几乎没有关注音乐的声音方面。相反,他专注于创作和表演的组织。他谴责自己和其他人将有创造力的乐手变成顺从的“工人”。事实上,凯奇正在攻击他在1948年批评的同样的力量。正如贝多芬的和声将应该独立的声音聚集在一起,将它们统一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抹去了它们的个性一样,现代作品,包括他自己的作品,有时迫使演奏者屈服于独裁艺术家的意志。
这种隐性法西斯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对于观众来说,就是听到一系列声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先无法预测,而必须由听众自己即兴创造。对于表演者来说,就是停止服从隐形权威的命令,而是进入一种“在不确定情况下保持警觉”的状态。这意味着他要转向“梅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基础”,从中所有的无常都流出并回归。在实际操作中,转向一体化的神秘体验意味着进入一个分布式的表演者和声音领域。在他的演讲中,凯奇认为表演者应该分开并部署在整个表演区域。这样做会释放声音“从它们自己的中心发出并相互渗透”。它也会让音乐家获得“独立行动”的自由。最终,它将防止表演者和观众的群体化。凯奇写道:“当人们挤在一起时,他们会像羊一样行动,而不是高尚的行动。”
如果专制主义作曲家集中声音和人,反专制主义者则采取了民主的方法。就像凯奇对萨蒂的版本或者说像奥尔波特和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一样,作曲家需要开发一个结构,使每个人和每个声音都可以完全独立自由地存在。1952年夏天,凯奇创造了两个旨在实现这些原则的事件。第一个发生在黑山学院,被称为剧场作品#1(Theater Piece #1)或有时称为黑山事件(Black Mountain Event)。在1948年夏天之后四年,凯奇和坎宁安回到了黑山。那时,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全年居住的艺术家的家,他们庆祝了一种领域的交流方式,包括领导学校的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和学生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51年秋天,劳申伯格完成了他所谓的白色绘画(White Paintings)。这些只涂白色油漆的大画布成为了场地,周围的光影在其上演奏。正如凯奇看到它们时所承认的那样,它们似乎模糊了绘画表面和三维空间之间的界线。接下来的夏天,凯奇、劳申伯格和其他人阅读了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剧院及其双重性》(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这是黑山诗人M·C·理查兹(M.C. Richards)最近翻译的。阿尔托长期倡导一种剧院,其中,正如他所说,“演员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做。”(the actors are not performing / they are doing)阅读阿尔托之后,凯奇和其他人创造了被广泛称为第一次“发生”(Happening)的事件。
在事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仍存在一些争议,但通常可靠的卡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描述了晚餐后在黑山餐厅的聚会。在学院成员在椅子和桌子上散坐之后,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凯奇站在梯子上发表演讲,默斯·坎宁安在观众中跳舞,身后跟着一只狗,大卫·图多(David Tudor)在钢琴上演奏了凯奇的作品,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和M.C.理查兹(M. C. Richards)朗读诗歌,视频和静态照片在劳森伯格的白色画作表面闪烁,这些画作悬挂在天花板上。活动结束后,参与者拿起一系列放置在椅子上的茶杯,走开了。
多年来,评论家们将这一事件描述为阿尔托的无墙剧院愿景和美国艺术中新兴的领域美学的典范。但在凯奇与机构和权威长达十年的斗争背景下,这也代表了他在音乐创作中发展的环绕美学向男女和身体世界的迁移。在他的剧场作品中,凯奇释放了他的表演者 — —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从未是他的表演者 — — 让他们独立行动,但又相互协调。他们在剧场中塑造了他在声音中理想化的世界:一个多样互动的世界,每个个体的声音和人都完全个性化,同时又是整体编排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会利用“发生”(Happening)所提供的审美和政治自由,将其作为新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型。同时,1952年8月29日,大卫·图多(David Tudor)在纽约伍德斯托克演奏了凯奇的作品4'33"。以下是该作品的完整乐谱:
I
TACET
II
TACET
III
TACET
注意:这个作品的标题是其演出总时长,以分钟和秒为单位。在1952年8月29日的伍德斯托克,纽约,标题是4'33",三个部分分别为33"、2'40"和1'20"。由钢琴家大卫·图多(David Tudor)演奏,他通过关闭键盘盖子来表示部分的开始,通过打开键盘盖子来表示结束。然而,这个作品可以由任何乐器手或乐器手组合演奏,持续任何长度的时间。
通过4'33"和剧场作品#1(Theater Piece #1),凯奇解放了声音、表演者和观众,使他们摆脱了音乐独裁者的专制意志。所有的紧张关系 — — 作曲家、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声音和音乐之间的关系;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消失了。虽然他转向了他认为更加民主的作曲和表演方式,但凯奇并没有放弃对局面的所有控制。相反,他作为一个美学专家,发布了指令,设定了行动的参数。即使他拒绝了独裁者的指挥棒,凯奇也接管了经理的电子表格和备忘录。由于他慈善的指导,听众和音乐家都可以自由地听到世界的声音,并在那一刻认识自己。声音和人们在多样性中统一,自由地行动,处于一个明显的美国音乐宇宙中 — — 一个最终摆脱了独裁者但不失秩序的宇宙。
编译自:Fred Turner的《The Democratic Surround》的一章“The New Landscape of S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