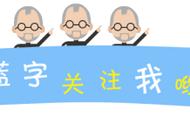湘西凤凰县拉毫营盘石板寨城西门,飞檐翅角,雄伟壮观。图/卢睿
云贵东缘,武陵腹地,号称有着十万大山的湘西,少有盆地。放眼望去,山连着山,山叠着山。湘西作家蔡测海写他小时候在山垭口眺望远处,“远处是大山,再远处还是大山”。湘西的山单个来看,并不显高大威猛,但数量一庞大,行走其中,人就觉得渺小。有外地人说,一入湘西,便像是进了山脉的海洋,山脉像波浪一样此起彼伏。走进湘西,人的腰杆会不由自主像山一样挺得笔直。这是湘西人的傲骨。
按理,这样的山脉容易让人绝望。事实上,湘西的人们,不管是在山脚,还是山腰,抑或是山顶,他们大多数时候是快乐着的,脸上是有着快乐的笑容的。
这笑容的发生,应该还是和他们生活着的山有关——无论大山小山,山脚总有一涓小溪或是一条长河,如蔡测海所说,“东边是高山,西边是高山,两边山给河流让出一条路,任它缓缓地流,任它有一个好的前程。”
蔡测海还说,不能在山上居住的鱼虾,在小河里有个好世界;不能在水里居住的鸟兽,在山上有个住所。“水通情,山知理”,人住在这样的山水里,便是“在情理之中”。
从前慢,慢慢在湘西
经常去湘西的朋友都知道,湘西多古镇、古村。
古镇多在河边,例如沅江边上的浦市,酉水边上的王村(芙蓉镇),洗车河边上的里耶,沱江边上的凤凰,清水江边的茶峒(边城镇)。
有人说水是湘西的血脉,这些古镇邻近血脉,更多些滋养,更多些活路,也就更多些热闹。
古村则多在山上,例如花垣雅酉镇有着中国第一石头村的扪岱村,凤凰山江镇的凉灯,古丈的梳头溪和排茹村,矮寨的家庭村,花垣的十八洞村。
湘西是有棱有角的,山是湘西的筋骨,生长在筋骨上的这些湘西人,更多些硬气、更多些质朴,待人接物也更多些热情。
山阻水隔,湘西的发展节奏就好像总慢那么半拍。历史上,这一慢,就让外面的人对湘西有些看不起,就认为湘西是封闭的,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湘西人相对就要“蛮”一些,神神鬼鬼一些,就有了湘西赶尸和放蛊的传说——到上个世纪了,还有人揪住沈从文,问赶尸是不是真的。
沈从文和他被问到同样问题的老乡一样,认为这个问题“傻不可言”,不过,他还是“尽了义务”去回答,猜测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想满足自己的荒唐幻想”。
山里其实没那么荒唐,山里的一切虽然慢了些,精神上也从巫傩到了孔孟,经济上也从狩猎到了农耕,山里其实也有源流千古的史诗、乡贤、政商军事、歌舞和画艺。
历史上慢下来的那半拍,到今天,就因祸得福。未被工业浪潮灭掉的手工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被拆掉的吊脚楼成了风景;未被工业污染的山山水水让湖南这个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成了国家森林城市。

湘西土家族摆手舞,湘西人硬气、质朴、待人接物热情。组图/麻老先
边城: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
很多湘西人向外地人介绍湘西时,会这么说:“湘西美,美在沈从文的书里,黄永玉的画里,宋祖英的歌里。”
很多人是通过沈从文最早“接触”到湘西的,他凭一己之力把湘西的各种美好带到了世界的面前。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说《边城》,沈从文展开了一幅理想世界中的湘西风俗画,随着画面的展开,翠翠,这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情窦初开的少女和围绕着她发生的故事也徐徐展开。
“小背篓,晃悠悠,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的这首《小背篓》,把湘西的山山水水全装了进去。
翠翠是湘西众多温柔腼腆又炽热多情的女子中的一个;小背篓也是湘西承载着乡愁的众多物件中的一件。湘西的山水盛产美好的人性、人情,充盈着乡愁。湘西的山水也盛产记录、传播这美好人性、人情的作家与艺术家。
沈从文之后,短篇小说《远去的伐木声》,作家蔡测海让和翠翠一样美好的女子阳春随着木排去了远方;70后作家田耳,这位沈从文的凤凰老乡,他的成名作《衣钵》,写湘西的一个年轻人如何子承父业成为道士,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其中有着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之乡愁。

雨后惹巴拉。
湘西的美不浅薄
洗车河像一条折了又折的水袖从东北方向的群山间摇摆了过来,在捞车村接了也是水袖一样一摇三摆流过来的靛房河,合在一起后,继续水袖一样往西南方向荡了出去,弯弯曲曲流入了酉水。
捞车村有国家级的土家织锦工艺传承人刘代娥,她在村里开了个织锦传习所。她织锦的丝线,是用植物染料染的。黄色来自于栀子,蓝色来自于蓝靛草和猪鼻孔草;红色来自于九月过重阳时采的叫“狗屎泡”的植物……这些可做染料原料的植物果实或根茎,她原先是去山上或田间、道边去采,现在,她种了些在附近的山上。她家院子里也种了一点点。
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传承人,刘代娥有很多机会离开捞车村,事实上她也去过凤凰、张家界等旅游景点开店,但她更喜欢不那么忙的生活节奏,所以,她情愿回到老家。
湘西有不少像刘代娥这样愿意守着故土的手艺人,我所知道的,永顺万坪镇的付业林也是这样的一个手艺人。从湘西到处可见的背篓可知,篾匠的生意至今还不是很差,付业林虽是篾匠出身,但不是普通的篾匠。他能够剖出比头发还细的蔑丝,能够织出指甲盖大小的精巧小背篓,他靠他的竹编手艺成为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银饰锻制、踏虎凿花、挑花、印染、手工年画等,很多手工艺人散落在湘西的一些村落或集市里。他们平日住在吊脚楼,走在青石板铺就的乡间小路,湘西的山山水水好像特别滋养这些手工艺人,这些手工艺人不急不躁,他们做出来的手工艺又装点了湘西的山山水水。这些人让湘西的美,多了时间的磨炼,厚重不浅薄。

土家族毛古斯。

苗族巴代上刀梯。
能把野菜吃出美味的人
湘西人的坚韧和随遇而安,体现在湘西的餐桌上。有段时间,我想起湘西,就会想起蒿子粑粑。
在湘西,用来做蒿菜粑粑的“蒿”是青蒿,一种菊科蒿属植物,常长于山脚溪边,有异香,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一年生的它们二月底或三月初开始把它们嫩嫩的羽状裂片的叶子从湿湿的地里撑了出来,清明节前,它们一般都能长到三寸或者五寸。与此同时,山上或路边梧桐树的新叶也已经舒展开来。上一年的糯米和籼米,看对糯的喜欢程度,按比例(一般是7:3)各取一些磨成粉。先取少量米粉和捣碎的去了涩的青蒿加温水在热锅里搅拌——这叫“打纤”。待锅里的米粉和青蒿成了糊状,再把它们舀出与其它米粉攉在一起,揉匀,再揪出来压成一个个椭圆状,包上盐菜肉丁、剁辣椒肉丝、辣子豆腐或香黄豆加糖等,用桐叶包好后上锅蒸熟。
蒸熟后的蒿菜粑粑,桐叶的清香、蒿菜的异香以及米粉和其它佐料的香交融在一起,香气扑鼻;最外层的桐叶变成了褐色,但里头被它包裹着的蒿菜粑粑却仍是好看且让人有食欲的青色。
我其实不大算吃货,主要是湘西太多美食了,让我不由得不想起他们。例如此刻,我想起的是湘西的猕猴桃,我曾在凤凰古城和浦市古镇买过集市上的野生猕猴桃,鸽子蛋大小,非常甜。湘西人工种植的猕猴桃也非常诱人,尤其是十八洞村的红心猕猴桃,九分甜一分酸,甜而不腻,味道极富层次感。
我有些庆幸我不大喜欢吃酸,我要是喜欢吃酸,想起湘西的泡菜,怕是会坐不住,恨不得马上买张城铁票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湘西,不论在土家山寨,还是苗族村落,家家户户都有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那是腌制酸菜的工具。
湘西诱惑人的美食还有腊肉。湘西多山多水多寒湿,很多人家的火塘是终年不熄的。一口火塘就是一个厨房,取暖,吃饭都在这里。火塘上方,悬挂着满架乌黑油亮的腊肉,香气绕梁。
湘西艰苦的自然环境,反而塑造了它独特的美食风格。
湘西的血性曾误会为匪性
在湘西,有一段历史会不期而遇。在湘西,常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1950年,解放军进军湘西,有两个侦察兵看到了真实的“湘西赶尸”——赶尸匠并不是靠什么法术或者口令指挥尸体赶路,而是自己把尸体做一番处理后背在背上,背回死者家里。
秘密一揭开,有人觉得像是上了大当,我倒从这个揭开的秘密里看到了湘西人的重情义、对生命的珍重以及对家乡的热爱。
湘西人是有着热血和担当的,他们不仅热爱着自己的家乡,也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家乡有人来犯,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乡,国家有人来犯,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的这种热血和担当,往往也容易引起误会。
2009年7月,我曾去过保靖县葫芦镇一个叫印山台的古村。给我做向导的,是位退役军人。
他一路指点,那块平平的、现在种了花生的山顶是土人(即土家族人)庆祝丰收的地方,那个山头有废弃的烽火台,那边有长满了树的旧战壕。我望向他所指的方向,尽皆苍翠,仿佛争战从没发生过。直到到了一个叫营盘寨的地方,看到石头垒就的城墙,看到爬满了苔藓的城门,旧时驻兵的格局仍较好地留存着,才相信向导所指并不虚。我们遇到了一个在田间劳作的老人,那个老人没忘他赖以生存的田土是百余年前驻军所开垦,“我们吃的全是军粮军土。”老人说,他的曾祖父是从沅陵来到印山台当驻兵的军士。
同行的保靖文物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保靖有古汛堡18座,炮台18座,碉堡19座,卡门楼12座,石边墙遗址2段。《保靖志稿辑要(卷三)》对此有记载,“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汛堡卡碉百二十一座,古丈坪连保靖县境内汛堡碉楼六十九座。”
史志和我们的现场勘查,证实了保靖明清古军事城堡与凤凰、吉首、古丈、花垣的军事城堡和边墙是连在一起的。这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的存在,证实了彼时湘西土著遭受的误会之深。
张家界的魅力湘西民俗风情剧,有一场是“湘西赶尸”,这场戏再现了湘西将领罗荣光在天津大沽口的战事,罗荣光和他众多从湘西带去的部属壮烈牺牲,最后赶尸匠把他们全都带回了湘西。情节有夸张,但罗荣光为国牺牲却是历史事实,乾州古城至今还留有他的故居。
虽然常被误会,但国家危急时刻,湘西人的大义却往往感天动地。明嘉靖年间,倭寇来犯,湘西18岁的土司彭翼南带领3000土家兵千里迢迢奔赴沿海抗倭,他爷爷老土司彭明辅不放心他,又带了2000士兵跟了过去。就凭这,永顺老司城的遗址就值得去看一看。
战场上,湘西人的勇猛是出了名的。抗战期间,从淞沪会战到最后的湘西会战,都有湘西的热血男儿身影。
2015年,我在凤凰县扭仁村的一个古宅见到一根旧日椎牛仪式用的木柱。当地的民俗专家告诉我,椎牛仪式上,牛倒下后,旁边围着的年轻人就拿弯刀冲上去割一块肉,用衣服包了,赶紧就往舅舅家跑,把那块肉交给外婆外公,往桌上一摆,磕个头就打仗去了。
我此前的了解,椎牛仪式是最隆重、最盛大的祭祖祀典,听了这个说法之后才知道这个仪式的发起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为什么要送一块肉到舅舅家呢?因为我们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还一块肉到母亲的娘家,就表示不欠母亲家什么了,打仗就不管不顾了。”专家这么一说,我便对湘西人的血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片土地越美好,爱这片土地越深,动荡时期捍卫这片土地的决心就越强,而像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爱这片土地越深,就越想着安居乐业,喝一杯苞谷烧,沏一杯古丈毛尖或黄金茶,好好享受着眼前的山水风光。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