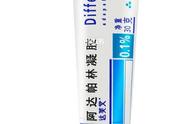《儒林外史》结尾,作者写到市井四大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
四大奇人,究竟奇在何处?
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外在身份与内在精神世界的错位。
看身份地位,这四位都是市井小民,靠操持着世俗的“贱业”勉强度日;看其内在精神风貌,却是比当时读书人境界更高的知识分子。
季遐年,无家无业,在寺院里安身,却擅长写字,不学古人,自创格调。(这和王冕自学画画差不多,也只能这样了,穷人家的孩子,按部就班接受艺术培训毕竟不现实,只好将之归于天赋,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那种。)
王太,祖上种菜卖菜的,到他这一代,连菜园子都保不住了,只好以卖火纸筒子为生,然而,他喜欢下围棋,水平很不一般。
能诗善画的盖宽,以前家里开当铺,他像杜少卿,仁慈宽厚,很快沦落到变卖田地房产的地步,开了一间小茶馆、每天挣五六十个钱糊口。
荆元是个裁缝,大概因为心灵手巧,也擅长弹琴作诗。
一个人能否被称为知识分子,并不能只看身份。
就像范进、匡超人之流,虽然通过科举做了官,但是思想和品行却仍是落于下流。
四大奇人虽然社会地位低下,骨子里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琴棋书画,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专属标志,绝非一般俗人轻易能够涉足。
陶渊明隐居田园,据说也有一把无弦琴,大概他并不会弹,只是时时拂拭,聊以寄托情怀。
大观园中,也只有林妹妹精于琴技。
学书法,需要下苦功,智永禅师的笔冢,怀素的千棵芭蕉,王羲之家门口的池塘,都是铁证。
至于下棋,更是和仙人有扯不清的关系。晋人王质烂柯的典故,就是棋与仙人的缘分。

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再有兴趣和时间,才有可能亲近艺术。
凡夫俗子,挣扎在社会底层,每天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用来忙着解决吃饭的问题,成为艺术家的概率有多大?
所以,这四位奇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就形成了奇妙的落差。
也许有些不现实,但不妨将其理解为作者未来知识分子的希望。
那就是要能谋生,在物质上要能养活自己。
只有经济上能独立、不贪求,才能避免在精神上依附他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所以,四大奇人的行为在一众钓名沽誉的人群中间,也就显得格外奇特了。
季遐年,简直是摆谱的明星,牛得不行。他写字之前要斋戒一天还要磨墨一天,还不要别人来磨,要用别人用坏了的不要的笔来写,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还得他高兴了情愿了才写。倘若不高兴,任你多大的官,拿多少银子来,他也不写。写字得来的钱,自己吃了饭,剩下的就随便给了穷人。施御史的孙子叫他写字,却又以貌取人慢待他,他就大骂:“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人家无欲无求,真牛!
王太,下棋胜了国手,不吃人家的酒饭,不要赢来的银子,只觉得“心里快活极了!”这是热爱的境界,绝非“国手”之流借以博取名利。
荆元,安心做裁缝,他说:“我们这个贱业,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他不与读书人相与,“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盖宽,随遇而安,诗画自娱。
他们多才多艺,个性洒脱,对生活保持着淡然、超然的态度,过着类似于“隐士”的生活。他们放弃了传统知识青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选择,不为八股而活,不为帝王而活,只为自己而活。琴棋书画,在他们这里,是纯粹的艺术享受,是独立的精神追求,而不是景兰江之流雅得太俗的假名士,也不是历来士人借以获得晋身之阶的工具。君不见,当年的帅小伙王维诗书画俱佳,却也要凭一曲《郁轮袍》谒见玉真公主,再奉上诗作,以期获得贵人的提携。

四大奇人的生活,真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吗?
他们找到了艺术这个安身立命的精神支点,似乎可以安之若素了。然而,奇人不可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隐士生活不过是无奈之下的自我放逐。
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在明清封建末世衰落的社会背景下,大家都不会有好的结局。王太祖上的菜园子都保不住,盖宽最终只得去给人家坐馆,社会经济的萧条可见一斑;王冕最后家里是“蟏蛸满室,蓬蒿满径”;盖宽所见的泰伯祠,已然倒塌荒芜,器物柜子都没有了……

四大奇人的理想生活,只能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内心平静,就像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梦醒后环顾四周,仍是无路可走的悲凉。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每一个人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都要依赖于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担当精神,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