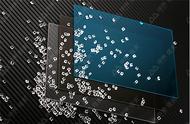第六十六集 (上)
卷首诗
孤军作战凌绝顶
遍地风流学心经
神欲静时心在飞
飞电传真到天明
第一章 池塘、江湖、海和天
“千万不要越过墙那边去。”
唐乃子在养伤的时候,一再叮咛过唐烈香。
“为什么?”
“这儿是少保府,”唐乃子用手指了指地上,然后又指了指外头,“那儿是神侯府。”
“是因为少保府与神侯府是对立的?”
唐烈香眨了眨眼睛。她看到画眉从这院子飞到那个院子,又看到燕子从那个后院飞到这后园来。
鸟可以。
人不可以。
鸟比人自由?
——如果鸟真的是自由的,为何有的又会给人们捕获,关在笼子里?
她住在少保府里,就见过园子里豢养了不少鸟,都关在笼子里,有的笼子大,有的笼子小,各种各式的鸟儿都有,不过林子里的鸟虽凶险但有自由,笼子里的鸟,没太大的凶险,但却失去了自由,万一也失去了宠爱,只怕也没有了活下去的权利。
她也偷偷到过相爷府,那儿的院子里有更多的鸟,更多的笼。
它们很美,颜色鲜丽,鸣声婉转动听,令人神迷。
但它们多活不久长。活不多久,就凋谢了,像经过狂风暴雨的花儿一般,凋零萎落。
唐烈香总是觉得它们活不久长是因为它们活得不开心。
所以,她听到它们唱很动听的歌,但却不是快乐的歌声。
她觉得歌声很忧伤。
她也认为那些给关在笼子里的鸟,唱出来的歌儿跟外头听到的鸟鸣,或者她睡醒时听到树上的啁啾,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一种歌声快乐。
一种歌声忧伤。不分哪一种类的鸟,不同方式的叫鸣,但是分两种感觉:
快乐的 忧伤的
在外头的鸟鸣很快乐。
在笼子里的鸟叫声忧伤。
快乐是因为自由。不快乐正是因为失去自由。
在唐烈香的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可是,好好的鸟,可以在偌大的一片天空飞,又没有人给它们划分界限,为何却给困在樊笼之中?
那当然是因为人。人要抓住它们,把它们变成禁娈,变成宠物。
也因为它们要觅食,要停止飞翔,落定下来,回到它们的巢,建筑它们的家,哺育它们的孩子。这就是它们遭擒而落在笼里、失去自由之故。
可是,一旦它们困在牢笼里,就没有了它们真正的家,没有了自由,再也没有开心时的欢歌了。
这些,在唐烈香心里,生起了很强烈的感触:
要回到自己的天空。
不要失去属于自己的自由。就算为了必须的觅食,也一定要小心谨慎,决不要因而失去了自由和自主。
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家,一旦维护不了自己的家园,也维护不了自己。
失去了这个,心里就不会快乐,生命就会逐渐萎谢,不如死了算了。
对唐烈香而言,她心里确是这样想。所以重要的是:不可以给抓住!
“我们暂时寄居在少保府,就必须跟神侯府的人对立了吗?”
有一次,唐烈香很认真的问她的母亲。
“问题是这样:少保府收留了咱们。少保府跟神侯府明显有怨隙,而少保大人于咱们有恩,我们欠了他的情。如果少保府和神侯府的人冲突起来,咱们肯定只能帮蔡少保,不可以帮神侯府的人,反过来对付少保府——这在江湖道义上是大忌。”
“如果神侯府做的是对的事,而少保府做的是不对的事呢?”
唐烈香虽然年纪还轻,但她来自唐门,还跟她母亲面对过许多追*场面,也可以说是从江湖上一路闯了过来,蔡京父子权倾天下,官宦勾结,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事,她也听说了好些,明白了不少。
这方面,她心里分明。有些人,对善和恶、是与非、对与错,从小就很有分际,心中有分寸。
但这并不代表他知道了、明白了,就一定去做好的而摒除坏的,只做对的而不去触犯错的,知道和实行常常是两码子的事。
“我们不管事情对不对,只看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帮谁。”唐乃子狠狠地道,“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才会告诉你:我平生最讨厌的话,就是那些什么‘对事不对人’、‘帮理不帮亲’的狗屁废话。要是帮理不帮亲,谁跟你亲?对事不对人,那谁做你的好朋友,最需要你伸援手时,一定倒了大霉!——这些人只是拿这种大道理来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大义灭亲,亲疏不分,无情无义,我不喜欢。”
“只是大家都这样讲,可能也这样想,”唐烈香长大了些,成熟了些,之后,便有这样的反问,“我们独排众议,独持己见,岂不是成了众矢之的,人所菲薄!?”
“其实那些人也只是说一套、做一套,能做到的有几?”唐乃子反问:“我们都是宋廷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宋辽交战至今,更知道辽人掠劫我邦子民,侵我山河。可是,宋廷对辽也一样背叛负义,*戮屠掠——那么,请问,我们是该帮理还是帮亲?对事还是对人?辽人*了过来了,我们是宋人,老娘管*的理!咱就管亲!你来侵略我们,我宰得一个是一个,*得一双就是一双!这时候,理何在?事何存?只有站在一条阵线上对付另一条阵线,融合一帮人里灭掉另一帮人——你不灭他,他就灭你,不然,你得先灭了自己人,成了他的人,这样,不如还是跟自己人灭了他人,如此简单,但最实际,比那些夸夸其谈什么大道理讲法治讲真理的他娘的痛快多了,直接多了,也不虚伪多了!”
唐乃子说这种话的时候,眉宇间有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尽管她满脸病容,以及眉宇间仍有掩饰不了的愁容,但这种英侠之气还是使唐乃子有一种来自内心激烈出色的美艳,不是庸脂俗粉可能比拟的。
“其实法治是什么?到底只是名正言顺的保护了皇帝和皇权。礼法是一种约束,崇儒是为了稳定政权。但我却没有见过有几个讲法的敢讲到天子头上的。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哪个同了罪?还不是成王败寇来得直接干脆!不然,拿龙袍打几记蟒鞭,往龙椅踹几脚蛟棍,撒把泥埋了件官服,拿当太子师傅、帝皇侍书的去抄家灭族,就可以免了皇帝的罪。这就叫法理人情吗?那些当什么侍书、太傅、洗马的可冤极了,说不定,皇帝太子,还没念过书,也没上过他的课!”唐乃子嗤地笑了一笑,“嘿,嘿嘿,嘿嘿嘿,我说,诸葛正我这些人就拿这套唬人的道理,去维护皇权。蔡攸、蔡卞,则同样拿这套老法子,去颠覆皇权。至于蔡元长,他?最是高明!以无厚入有间,逍遥物外而自在物内、格物其中,你看,他光拿着变法和复辟,两条极端的路,他却游转无间,随风转舵,左右逢源,任其摆布:改革派的王荆公既重用他,保守派的司马光也提擢他——他把一切法都唯我是用,这才叫舍我其谁、唯我独大!”
唐烈香当时就怯生生的问:“娘,那么,你是赞成蔡京所为了?”
唐乃子道:“不,我不喜欢他,我只是推崇他能这样周游其间,完全不受道德、礼教约制,而把一切教条、法制乃至传统、学养,全为他在世俗中充作高攀的石阶。但我讨厌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的人。我就做不到,起码做不到这么绝,那么狠。所以,当蔡京力邀我投相爷府时,我还是宁可选了少保府。”
“那么,少保府和相爷府的分别是……?”唐烈香很想知道她现在究竟是寄生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这对父子一个货色,没啥分别;”唐乃子说:“不过,一个像粪桶,一个像沟渠——两者一定要选其一,我只好选了臭沟渠:至少,它还有流动,只要有流动,有一天,也许,就能把我们送回池里塘里,江里湖里,甚至大海天边去!
第二章 汉刘、唐李、宋姓赵
其实,不只在少保府养伤闭关之际,唐烈香也问过唐乃子甚至唐老太太一些她心里的疑惑:
“为什么在这时候在武林,总是以一家一族一姓求发展呢?为什么要固步自封、划地自限呢?以同一姓氏、同一族人为基础,这样岂不正妨碍了吸纳天下精英、包容世间豪杰的雄图,也阻碍了往外扩展、师夷之长的大志?”
唐烈香问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在唐老太爷子打算这次选拔唐乃子为未来‘唐老奶奶’衣钵传人之时。在门内人称为‘唐老太太’的唐梦蝶,与唐公公联合推翻了唐老太爷子原拟唐乃子为‘唐老奶奶’的刍议,当时,唐乃子本来已出类拔萃,建功无数,在门内已让人戏称为“小天王”。可借在重大事情出了意外,犯了门规,使唐老太太抓住她的弱点,让唐老太爷子下令逐她出门。
唐烈香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位,但对自己家族自囿为“唐门一族”而不求容纳百姓万家的优秀弟子,竞万世之功,而感到忧虑不解,所以有问于唐老太爷子。
当时,唐老太爷子的回答是:
“秦朝统一天下,二世而终,君主姓什么?”
“嬴。”
“……不姓秦?”
“不。”
唐老太爷子笑了。
他很欣赏这个唐门里出类拔萃的小女孩。
他知道她很聪明。
有一次在唐门门内:十岁以下的孩童发射暗器的选拔赛中,在限定短促时间内,唐门四位轻功最高的护法:唐*阵、唐失神、唐水月、唐水善,成了活靶子,可是这四人未精于发放暗器前,已练成闪躲暗器大法,谁也无法击中他们。
然而唐烈香却放弃了第一阵。
她掠上了小山丘去。
选拔赛进行的地点就是唐家堡的花园。名字很独特,也很随便,就叫“红之院”。看起来只是个歌舞升平、胭脂花粉的所在,但唐家堡里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来自这么一个看似一片繁花如海,绿树盛荫,听似夜夜笙歌、婆娑起舞,貌似纸醉金迷,耽于逸乐的地方,但唐家堡的决策,就多来自这个看来防守松懈、繁华明媚的所在。
当唐家堡强大时,在这儿发出的命令,栽培出来的子弟,便足以名震西南、席卷蜀中。
当“蜀中唐门”十分强大的时候,这儿培植出来的唐门精英,这儿发出的指令,便足以影响整个武林,甚至改变江湖的历史,乃至可以左右朝政,沸腾天下。就是掌握朝中的七尺昂藏,也得听取这西南一隅一姓一族的意思:否则,屠龙护法,皆由她“下旨”。
掌管这一族人生*大权的,便是“唐老奶奶”。
———就连唐老太爷子也曾代任过“唐老奶奶”。
“唐老奶奶”是一个代号。
一个真正掌握“蜀中唐门”的主持人物,照惯例统称“唐老奶奶”,且不管是男是女,年轻年迈,一概如是。
(有关蜀中唐门的来龙去脉故事,请看〇六年修订版的《神州奇侠》以及续传:《蜀中唐门》。《神州奇侠》故事系列已完成的共有:正传:《剑气长江》、《两广豪杰》、《江山如画》、《英雄好汉》、《闯荡江湖》、《神州无敌》、《寂寞高手》、《天下有雪》八部。后传《大侠传奇》三部:《刚极柔至盟》、《公子襄》、《传奇中的大侠》。外传《大宗师》四部:《血河车》、《逍遥游》、《养生主》、《人间世》。别传是:《唐方一战》。其余续作,概非作者所出,敬请垂注。)
“唐老奶奶”的任务之一,便是选拔接班人,甚至是隔代接班人。训练唐家子弟成为武林精英,也是“唐老奶奶”重要任务之一。
唐老太爷子发现还是小女孩的唐烈香,离开了原地,登上了假山,然后才发暗器。也就是说,在限时内达成任务,唐烈香一开始就处于下风。她牺牲了首段时间。但却争取到了最好的成绩。她把那段时间用作争取了制高点。然后她发出了暗器。暗器当然没有淬毒。也没有露锋吐尖。那只是“不具*伤力”的武器——幸好不具备强大的*伤力,否则,只怕轻功高明的四大护法都得死在唐烈香的手上。她虽迟发暗器,但居高临下,四大护法这才掠起,她的暗器认一个中一个,发一枚着一枚,让四个轻功高强的人站不住脚、藏不了身、也接不下来。
唐老太爷子顿时眼睛发了亮。
他知道唐烈香就是唐乃子的女儿。
他知道唐烈香原本不姓“唐”。
可是当他遇见人才之时,就像嗜弈者遇上了一局*着,一流剑手遇上了一把好剑,顶级*手接到了个不可能刺*的任命,他还是眼睛都发了光,心里也发了亮。
“为什么你放弃了前面的时间?”
他问小女孩。
“打不中打来干啥?”
小女孩天真的反问。
唐老太爷子知道这反问并不“天真”,反而使他心里一震。
“为什么选取那么高的地方出手?”
“居高临下,一目了然,何况发射暗器,往下射力道更劲,覆盖面更大,更省功夫。”
唐老太爷子也没再说什么,只是自此之后,他虽日理万机,忙的分身不暇,但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回答唐烈香的提问。
那一次,他就反问过唐烈香:“汉朝呢?皇帝都姓啥?“
“刘。”
“对,姓刘。”唐老太爷子闷哼一声,道,“不管东汉西汉,大家要取天下,争天下的时候,还是得打着‘刘’姓这旗号。”
“是的。”唐烈香年纪虽小,但对历史掌故都很留心,“刘备的名号是正统汉室,人称‘刘皇叔’,争取了不少民心,刘表也一样打正旗号,连一向睥睨天下的曹操,也得奉侍刘姓天子才以令不臣。连孙策也一样要打扶助汉天子的主意。”
“便是。”
唐老太爷子道:“这便是了,秦皇姓嬴,汉室姓刘,他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全是姓嬴的、姓刘的,但在秦皇修建万里长城之内,莫不是战国七雄的豪杰精英;在汉室中,罗网的是天下英雄好汉。但他们打的旗号,仍是秦、汉,其实,实行的是:家天下。“
“我明白了。”唐烈香自小就很聪悟。
“你说说看。”
“唐代是李氏皇朝,本朝是赵家天下,”唐烈香遂眼睛发亮,“真正掌握大权、保帝座的是姓李的、姓赵的,可见将天下人才尽收旗下,只要把住实权便可以了。”
“便是。”唐老太爷子说,“其实,每个国家、区域、民族、地方……都是一样的,语言不同,肤色不同,风俗不同,信仰不同,划地自囿,同声共鸣的,联成一体,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了,尽管也可以收揽许许多多的人才。其实谁不是这样子?哪怕再过千年也如是。只不过,可能在旗号、名称上变易一下,可能唤作‘发梦二党’,头儿可能是姓李的、姓陈的,也有可能是姓汪的、姓海的,姓武的、姓林的,但手上有的是百家姓千家名的能人志士,都是一样,全一样,还是那么些强人在当家当政,主掌大局,然后英明的就把管治权力分给有才之士,若是腐败的,就给奸宦贪官架空了、腐蚀了、亡国了。其实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样。”
第三章 英雄的虎泪 小白的嘲讽
“哪怕再一百年、两百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人性本如是,只是形式上有变换,唬人有更唬得人离魂弃魄,诓人的照旧把人诓得给啃光了都不知晓,骗人的把真正有情有义的人都为他不平而卖命做尽无情无义的事,感人的继续让人落下英雄的虎泪而已。”
唐老太爷子说:“只是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以为这样打着家族的旗号眼界忒也不小了。其实还肯用姓氏为号,只是老实点,直接些,像‘老字号’温家,像‘山东神枪会’孙家,长孙飞虹、公孙自食,全变成姓孙的了。‘六分半堂’,为雷家所创,但堂下高手,姓雷的不逾半数!‘飞斧队’余家,‘太平门’梁家,‘下三滥’何家……莫不如是,只要首领够强、够悍、够明智、够号召力,一样可能把天下的精英聚于一门。”
唐烈香正为老爷子的理据找出实例:“像‘封刀挂剑’后的‘小雷门’,雷卷手上一样有戚少商等的外姓高手……”
唐老太爷子道:“像‘连云寨’和‘东堡、西镇、南寨、北城’,除了主事人之外,其他高手,都是从外边召来、雇用、请动的,不也一样可以壮大扩展!就连‘大连盟’冷总盟主请来了凌落石,‘七帮八会九联盟’的组合,还有‘自在门’、‘金风细雨楼’、‘天下帮’、‘发梦二党’,也都如是。再说,咱们唐门也有很多高手,原也不是姓唐的。你不就是本非就姓唐的么!尽管姓雷姓苏的,还是楼里堂里的主力,但组织中的大将,还是有各种姓氏,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手,比起来,打着姓氏为门派的,只是实在一些,也传统一些,其实,哪一帮哪一派,乃至哪一国、哪一朝,不还是明里能者占其位,暗里还是江山我有,外人不留!”
唐烈香笑着,脸上酒窝深一个、浅一个,“只是有些人比较虚伪。”
唐老太爷子笑着拧了她一下,“只是有些年轻人没有经验,学识浅,见识少,看不透。”
唐烈香偏了偏头,说:“也许有些人喜欢批评人,说人家气量狭小、气势弱、气度不足,但他们其实比那批评的对象还差长安到洛阳那么远!”
唐老太爷子爱惜的扪了扪她的鬓角,“那么,你年纪那么小,又为何能看得懂这个?”
唐烈香娇丽的灿笑了起来:“那是因为我有‘老爷子’的指导。”
唐老太爷子慈祥的笑了起来。
“慈祥”,这形容他的面貌和手段而言,很少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不过这次例外。
——对这聪慧的小孙女,他就算想装不慈祥,也禁不住打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慈和。
“那也不是,只不过,你年纪虽小,却可以接受新的事物去思考想一些自己可能未想过的事情而已,”唐老太爷子问:“你可知道怎么才知道,一个人还是年轻?一个人已经年老?”
唐烈香仰视着唐老太爷子,她知道他老人家一定会说下去的。
“一般都以为年纪大了,就是年老;年纪小的,就是年轻。”唐老太爷子感喟道,“其实这是个误区,并不如是。”
“我知道了。”
“你说说看。”
唐老太爷子鼓励这个小孙女。
“还肯接受新事物,新的思潮,就是年轻,不然,就是年老,或者幼稚。”唐烈香试探着说。
“还有。”
在一旁的唐乃子加插一句。
唐老太爷子微笑道:“你也说说看。”
“还肯动真情的,敢去爱的,就是年轻,就未年老;仍敢信人,虽年长心仍年轻;只会疑人的,纵年轻心已老了。那些只会骂人的、伤害人的,其实人,活着也与死人无异。”唐乃子别有深意的说,“不管对友情、爱情、亲情都如是。不懂得这个的人,也许便会嘲笑人为何年纪那么小也会发生爱情,年纪那么大了也会动真情,其实,嘲笑和不解这种情感的人,才是老化了,或是太幼稚的小白痴、老妖怪。所以,有些人,一开始就老了,有些人,到老还未老,当然,还有些人,因为在感情上遇到重伤挫折,不老也老了。”唐乃子把话说的特别重。她那是别有所指。唐老太爷子只闷哼一声,一时没有接话。唐烈香那时还不知就里,说:“那么小白的嘲笑,其实只嘲笑了他们自己的愚昧。”她习惯省略的叫“小白痴”为“小白”,就是在唐门弟子里,也有很多这种“小白痴”,因为自己不懂,所以才笑人痴。
她一概统称之为“小白”,单一个白,少一个字,以存厚道。
不过,这回唐老太爷子却正色指正了她:“你说话还是得当心。江湖上,有一个绝顶高手,是一个怪人,他爱上了一个女子后,后来却因痴于武而失去了她,到他醒悟原来人生来一趟,不是为了求道就够了,如果是,那只是一个躯壳在寻找自己的魂魄而已,只有情,才弥足珍贵。而且,他也失去了自己,忘了来时的路,一定要找到那个‘她’才能找到‘自己’。他后来寻寻觅觅,却再也找不到他的那个她了。大家只知道他叫那女子做:‘小白’——小心你把那些‘小白痴’去了末一个字,却惹着他了。咱们‘唐家堡’谁也不怕,但像他那种异人妖仙,不知来路,疯疯癫癫,本身就是‘大白’一个,还是少惹为妙。”
唐烈香听到了,也记住了。
那一次,年前,他们祖孙三人,曾在蜀中唐家堡的“红院”,有过这些对话。
所以,这一回,匿伏在“少保府”养伤的唐乃子、唐烈香母女,也延续这一话题有另一番对答。对蔡攸的说法,唐烈香母女都没有答允,蔡少保也并无逐客、翻脸之意,只不断施加压力,多方催促,所以,最好,还他们一个情,了却恩惠,不欠人情。
至于“相爷府”跟“神侯府”两帮人马的冲突,她们大可不理、不管、不插手,明哲保身为重。何况,就算要打抱不平,也得先敉平自己唐门的内乱,解决自己身上的危机,摆脱自己同门的追*,再说其他的吧!因而,唐乃子在养伤之余,一直叮咛唐烈香,不可以逾矩一件事:不要管“神侯府”的事。只留在“少保府”,让唐乃子的伤逐渐、也快好起来再说!
还有一件事物,万万不可逾越:
墙。
第四章 记起是因为曾经忘记
唐烈香从来不越过这墙。
她也不打算越过这墙来。
她知道蔡攸也是非同小可、极尽奸诈之士,要不是唐乃子和她一度给同门逼得走投无路,而要取得治疗又必须借助少保府的资源与人力,她们也决不会投靠少保府。她们在少保府待了两年余,唐乃子的伤毒正复元中,但痊愈甚缓,要完全恢复还谈不上,蔡攸已遣人四度跟她们提起的三个条件,除了一个,唐乃子已勉力“点到为止”的参与之外,其他两项,则能拖就拖,可延即延,虽碍于情面,不好断然拒绝,但也是打算一旦康复,还情报义,可以立即抽身,马上就撤。
她不好把姿态放绝,除了因为有求于人、寄人篱下之外,实际上,蜀中唐门也有把柄落在蔡京手里,她自己也有要害落在蔡攸手中。她自己本来也不愿意住得那么靠近“神侯府”。
因为“神侯府”是由诸葛正我主事。
诸葛正我自从叶哀禅退隐江湖、生死不知后,俨然已是“自在门”的掌门人。天衣居士不能算是“自在门”代表,他太淡泊名利。元十三限也不算,江湖人口里不说,心里清楚:他已沦于魔道。只有诸葛正我可以光大“自在门”的门楣。何况他已因护驾有功,保国有功,给册封为“神侯”,权重京师,虽以一人之力,也足以影响江湖,号令武林,澄清君侧,群奸辟易。不过,唐乃子本就不想沾“自在门”任一人的边。她跟这个门派有缘,不,更且,有怨,甚至可以说,有仇。
她会有“今日”,之所以负伤,须要疗毒都可以说是“自在门”的人带给她的祸患。她根本不想翻过那面墙去。虽然,少保府与神侯府只是毗邻。但对她而言那是天涯。
——那是她记忆深处,不想翻开的一页。
或许,她想回到那一页从前,但却不愿再记起这个努力忘记的记忆。而且,当你努力想忘记一件事的时候,其实已正在记起。记起的时候正因为曾经忘记。
唐乃子真的不想翻过这一栋墙。有时候,她也留意到这一面墙,心里也想到过:墙那边是什么?
——他还在不在?
——他还会不会回来?
——她要是见到他了,会怎么做?
——*了他?
——不睬他?
——告诉他阿香是谁?
——还是原谅了他?
——甚或是:自戕算了!?
不知道。
还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是谁也不得而知的。
有时候她也庆幸:幸好世上有墙。
人造了墙,把自己困在里边,便称之为家,冠以同一个姓氏,以别所出,于是武林中的老字号温家、黑面蔡家、蜀中唐门、封刀挂剑小雷门、金字招牌方家、流动静指一窝蜂刘家……全源出于此。大而化之,殷商周秦汉晋隋唐……每一个朝代,均来自于此。建了一个城墙,筑起了一个城池,日后,墙内便是自己一家人,关起来打打**,任宰任剐,皆无怨怼,但墙外的人,便是外人,既是外族,必有异心,也有其心可诛。
人就是这样,一个族一个族,一个家一个家,一个门一个门,一个帮一个帮,一个派一个派,一个会一个会,这样玩着里里外外、你虞我诈的把戏,而把大家分隔、分割开来的,就是墙,对了,墙,就是墙,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匙的,还是开不了的,在外的,还是只在心里的墙!
唐乃子根本不想越过墙去。她根本不想沾手墙外的事。也不欲管人家墙内的事。她只想好好养好了伤,治好了病,然后撒手就走,如果他日蔡攸有难,她才江湖救急,还他一个情,那就了事。
可是世事总与愿违。伤一直未好全。病也未痊愈。
毒,未清。
情,未偿。
而外面追兵,依然噪动,声讨围剿,仍然劲急。
唐乃子一向性急。
现在,她也只有按捺下来,因为,急不得,欲速反成败。
她有一天,也要走出这四面围墙,同时,突破她心里的围墙,可是,在达到这层次之前,她要依附在这墙下,把伤养好再说。
墙内可以得到庇护。墙外有自由。但凶险。也许,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以及,没有绝对自由的好处。
问题是:你怎样选择?怎么作抉择?
唐乃子一再叮咛唐烈香莫要去逾越那一栋墙。
唐烈香本来也没意思要越过它。
她常到后院习武,练发暗器,有时,闲来闷时,也吹吹笛子。
“少保府”的后院很大,甚至花园很多,几乎每一所亭台楼阁后面前方,都有院落花园,她只不过占用了一个小小的场地,还用了一个号码为代名,少保夫人也乐于她在院子里玩,且不管她是练功放暗器还是吹笛寻乐子。
她注意到院子后面的墙。墙外的那一方,听说是另一个院落,那儿树木蓊郁,偶有花香,她听说那边就是“神侯府”里的后院,“一点堂”的后花园。
她更注意到这院落有一道门。
后门。
门上有一个铜锁,已锈蚀,谁也没给过他们锁匙,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是留有钥匙?看来,只要一发力,就可以扯断。
——不知道“一点堂”门那边也有没有这一道锁?
还是,只有“少保府”这儿可以开过去,然而,“一点堂”那儿却开不进来?
唐烈香心里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是因为她已生起:“要不要越过去这一面墙?”疑问的时候了。
她有这种想法,开始时只是因为一段音乐:
箫声。
箫声凄怨。
——有时,还十分凌厉。
总的而言,无论凄怨或是凌厉,如泣如诉,还是欲断欲续,都表达了一种孤独傲岸的性情。
这是谁呢?
——谁家吹箫画楼中,断续传来断续风。
这激起了唐烈香的好奇。
不知怎的,听到这箫声,她就生起了一种奇特的情愫:
像是与自己的前生,忽然相逢;又似与自己的后生,素面相见。
幽幽怨怨,七曲九回,繁花落尽,繁华散尽,生死以之,不离不弃,千秋万载,泪影笑颜,心情尽聚合在这越岭悲尽了秋意,越墙落尽枫红的一段箫韵里。
——怎么那么熟悉啊!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吹了如许落寞,对人世间有如许情怀,却又如许冷漠傲慢的一种个性?
她忍不住要寻觅。
她以为是一个落拓、苍桑、含冤忍忿的中年汉子。
甚至是一个孤独、失意、怀才见逐的老年士大夫。
她没想到的是:那是一名少年。
少年无情。
第六十六集(下)
第五章 将你心换我心才知相忆深
她没想到吹出那样幽怨和凄厉箫声的,竟是一位苍白少年。
她初窥见他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
她看到的是一团气质。
一种冷傲、寂寞、凄寒的气质,是的,是气质,尤胜于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是一种:“宁可天下人不解我、仇视我、漠视我,我也决不因而去接近人、讨好人、伤害人”的态度。
透过他的眉宇,以及他的箫声,表达出这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诠、千言万语化作寂灭无声的感应。
还有他的寂寞、无依。
——以及伴随的自恃与傲慢。
然后唐烈香又发现了一点:一点让她梦魂牵系,不能或忘的特征:
他是坐在轮椅上的。
他的腿是废了的。
她瞥见他,是透过窗。
幸好,世上有围墙的所在,往往也有一个出口:
那就是窗。
窗在身体里是灵魂。
在体外就是眼睛。
于是她看到了他,在他还未看到她的时候。
那一次,她还看见他落寞的在院子里,落寞的轻咳,然后,用洁白的手绢抹拭,她还瞥见上面沾染了一抹惊心的殷红:看来,他还有病!
——而且,还病得非常严重!
于是,她惊心,她动魄,不知怎的,她关注他,关心他,与他和箫调韵,互诉心曲,她还主动递给他吃的东西,找藉口见见他,聊几句也好,让他不孤单,不寂寞,不一个伤心,就这样,她才安心,才不牵罣——不,只要回到她和娘亲安排住宿的‘五一七阁’之时,她又不知怎的,心里又不安起来了,又牵罣他来了。
——那个孩子,可是安睡了没有?
(怎么他让人如许不安?)
——那位少年,今天不知快乐些吗?
(怎么我会如此牵挂?)
她也不明白。
她常与他箫笛应和,好像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交流了很多很多的心声,大家已交往了好久好久,已完完全全没有了隔阂。
音乐,要比语言直接,要比文字感人。
从耳及耳。
以心传心。
——有时候,要将你心比我心才知相忆深;有时候,要以一曲还一曲方知心意浓。她以前一直只以为娘亲的二胡,才是最忧怨、凄凉、哀恻、缠绵的。
——想必,母亲也常常惦念起她那一段哀怨缠绵的故事吧?
她总觉得母亲的二胡,如泣如诉,凄绝悲凉,令她听了,很不开心。
可是,无情的箫声,那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抒情,又不落于悲情,反而有一种冷眼看世间、袖手傲红尘的气概,使她不只于为其悲,还关其心,切其情。
所以她认识了无情。
——而一直不敢向娘亲坦承。
更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自从她发现有人挑衅袭击无情之后,在她心中是有了这盘算:万一无情遇难,自己是不是该翻过墙去救他?
如果这样做,就会破了例。
逾了矩。
犯了忌。
破了禁。
后果不堪设想。
问题是:
她做不做?
——越不越墙?
做,还是不做?
她看见院子里一树桂花,正盛开着,有些枝桠已伸展过墙头。
而从“一点堂”那儿(他们已共同称作:“寻梦园”却不知有一日,这“寻梦”的名义却为蔡京所夺),也有一树千里香,有些花瓣正因风送落到她这儿的院子来。
所以,她所处的院子里,有桂花,馥,也有千里树,香,遍地风流,风送暗香。她知道自己已别无选择。
做。
一定做。
必要时,翻墙就是翻墙。
逾矩就是逾矩!
破禁就是破禁!
有一段时候,她没有出现,没有应合无情的箫声,原因是她躲着。
她试图逃避。
那是因为唐乃子发现了这件事:
从她女儿的神不守舍、若有所思上。
从那自遥远庭院传来的箫笛同奏,音韵共鸣里。
于是,她有问于唐烈香。
阿香只有告诉了她的娘亲。
她母亲的脸色,愈听愈沉,愈听下去愈冷峻,愈说到后来就愈铁青,烈香以为她娘的旧患又告复发。
她知道原来箫声来自神侯府、一点堂、一个少年。
那个少年传闻里姓盛——诸葛先生的首席弟子。
她猜测他是谁。
她倒抽了一口凉气。
———她跟“自在门”的人有过一段“孽缘”,以致给人嘲笑小香是个“孽种”!但她决不想要再有这种“孽障”,却决计没想到她至亲的女儿又步入了“孽尘”!
她也知道了烈香的女儿家心事。
她一直不愿意自己再跟“自在门”的人沾上关系。
她控制住自己。但控制不了阿香。
———偏生是:小香跟她少时是一样儿的脾气,一个样的烈!
“我能阻止你们的交往么?”
她随即看见烈香的眼里有光。
——有光是因为有泪影。
“那么,你得尽量减少见他,尽量减少跟他交往,尽量不要跟他合奏……就算,万一,你守不住,你也得守住这面墙,不要翻过墙那边去……”唐乃子只好改口说,“当然,他也不能翻过墙来。”
“他是翻不过这边来的。”唐烈香说。
带着抗议。
“我知道。如果他翻过来,那么,我只有*了他。”唐乃子凝肃地道,“若果是你主动翻过去,那么,按照唐门的规矩,我得*了你,不然,他一定要娶了你,然后,跟我们回蜀中唐门。”
她正色道:“这,没有挽回余地,也没有折衷办法,否则,我也不待这伤好了,押你回唐家堡受罪吧!”
她一字一句的说。
“或者,”唐乃子说,“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了他。”
第六章 墙和窗
“我现在就去*了他。”
“不。”
唐烈香挽住了唐乃子的袖子,指尖碰触到她的手腕,心里一阵疼。娘怎么又消瘦了,以前她记忆中的娘还是比较丰腴的,现在,好像一阵风都能吹得起。她又生起一种凄凉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娘表现得越倔强,她就觉得越凄凉。
“娘,用不着。他翻不过这墙来。”她说,“只有我翻得过去。要*,就*吧。” 听了这句话,唐乃子心里喊了一句话:只怕要出事了。
她看着唐烈香,既不恨,也不忿,甚至没有懊恼。
但她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年轻时飞扬的自己。
她心里*了一声,但外表却十分酷烈的道:“我有伤,再半年就好了。要是不好,也不留在这儿了。好歹,得要回去一趟,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不希望在这时候没有了你,也不想你亲眼看到那个少年为你而殁。你明白么?”
“这样好吗?娘。”唐烈香冰雪聪明,当然听得懂唐乃子的意思:“我有时只跟他聊聊天,用笛声应合他的箫韵,或者,给他吃好吃的东西——我不翻过墙去,你也不必*他,好吗?”
唐乃子爱惜的抚摸了几下女儿的头发。看到她的眼神,她就心软了下来:事实上,她认为女儿的眼睛流露出来的灵光,并不太像她自己,而是像那个人。
那个曾叫她梦魂牵系的人。
——那个几乎毁了她一生的人。
那个叫她吃尽苦果,但回味犹甘的男人。
她每次看到这种眼神,她就会心软:
事实上,她就因为心软而误了大事,害了半生。
“好,”她为了掩饰自己心软了,也想让唐烈香不那么忧虑,所以故意说:“那么,就只有等你翻墙才*了你,好吗?”
“娘要*我,现在就可以了,”唐烈香陶醉在唐乃子抚挲她额前的感觉里,觉得这一刻很幸福,便说:“何必等翻墙?”
唐乃子看着这张姣美的脸孔,忽然间,心中动了一个念头,让她自己也大吃了一惊。
她马上敛定心神,转移心思,随意的问:“他……很爱吃东西?”
“不,他胃口不太好,吃得很少。”唐烈香道:“我只是爱看他吃东西,希望看他多吃一点……他那么瘦弱,像那些水仙花的叶指一般……我就着意他多吃一点什么的,也爱烧东西给他吃,看了就很满足……”
唐乃子又怜惜的看着她女儿。那少年胃口不佳,她当然明白,那已是侥幸了。刚才那种念头已一闪而过,完全消失了。
“你怎么把食物给他?”
“窗。”
唐烈香回答。
窗。
是的,窗。
世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墙。
——隔绝外界、世间的围墙。
但幸好,墙上总是有一个活路:
那就是窗。
窗。
那是墙的眼。
心灵的远望。
墙和窗,就像脸孔和镜子,一体的两面,再进一步,就是门。
打开门,就离开了墙,或许,走进另一处围墙里。
关了门,就是墙里的世界。
窗常常挂了帘。
——“金字招牌”方家方前辈,常在辞章上寻问:“美丽的帘影背后,是什么?”但谁又知晓:“黝黯的门打开之后,匿伏着的又是什么?”
唐烈香是这样答允过唐乃子。
可是,一旦等到无情在“寻梦园”遇险之时,唐烈香可啥都不顾了。
无情翻不过墙来。她就翻过去。
——死,也要和他死在一起!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她不知道。
她只是这样做了,绝无挽回余地,虽九死而不悔,也不管后果是什么,后事如何!
人总会有激情的一刻,不然不算活过。
唐烈香现在就是这种情怀。
无情在与她并肩作战那一刻,也有一种生死不过尔尔,唯情可大可久,不泯不灭。
所以他们都活过。
因为他们都激情过。
他们且不管千年百年后,百十世后,有人嘲笑他们,何等愚昧,何等痴騃,不为家国民族,不为真理大义而战死,只为了你,只为了我,为了我和你,而拼出了真火,豁出了生死,他们可不管这个。
因为嘲笑他们的人,压根儿没尝过这一刹的激情。
他们只是曾经存在过世上。
没有活过。
不曾爱过。
可是,唐烈香一旦闯进了一点堂,全面参与,全力出手,就没有了回头路。她已经翻过墙来了。
虽然,她不是真的翻墙而入,而是扭断了锈蚀的铜锁,打从后门走了进来。
——但那已不是墙内的世界了。
唐乃子一直有留意“一点堂”这方面的风吹草动,有时候,她还故意以二胡奏乐,截断无情和烈香之间的互诉衷曲。
同时,也提醒他们:莫越雷池一步。
可是现在雷池已越过了。
还流了血。
*了人。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唐乃子眼看唐烈香和无情不敌,她可不能任由他们丧命。
她只有翻过墙去。
全面参与。
——没有回头路。
本来还是有后路可以退的。
唐乃子本在子夜运功疗伤,运气疗毒。
她也发现最近不知怎的,功力很有点阻滞,恢复得颇不惬意。
驱毒也遇上了瓶颈,有时候,不但进度不如前时,而且余毒未消,反扑更烈。
这使她非常担忧。
气恼。
她知道已不能长期匿伏在这儿。
她必须要重返蜀中唐门。
她还有心念的人。
心悬的事。
何况,决不能让烈香风华正茂之际,全耗在这里:这会太委屈了她的!
光是为了这点,唐乃子说什么也得离开少保府,面对追*与排斥、围剿和叛将,决一死战,重回蜀中,重建唐门。
她深知阿香的性情。
她就跟香儿一样,心里同样抱持着:“不可以道殉情,那是非人道,只可以情殉道,这是有情道。”这个想法,而这个说法,当“唐老太太”,亦即是当今唐门代任掌教“唐老奶奶”之位的主事人,在江湖还是号为“命犯桃花,一笑*人“,在武林中还保留本名为唐梦蝶之时的名言。
不过,当唐梦蝶成为“唐老太太”后,主掌“唐老太太”大位之后,权倾西南,号令唐门,天下廿一户暗器名家、大师莫不以“唐老奶奶”为尊,也许,她的初衷就变了,看法也不一样了。
或许,还是没变,仍然一样,但人在江湖,一入唐门,有许多事,你不想做,可是,一旦坐上了那个位子,你不得不做;有些人,你不想伤害,不敢得罪,但是,一旦你到了一个处境,却不得不出手,不能不处置,这便是做人做事极大可悲之处。
可是,唐乃子还是怀念她。
她想念唐门。
怀念唐老太太。
——虽然,怀念的同时,也感觉到害怕。
以及恐惧。
第七章 没有后路可以退
也许就是因遗传性情,或者根本是因兴味相投,唐乃子最怕的是:
唐烈香沉不住气!
——还是翻过墙去!
可是,世事多与愿违。
唐烈香真的就沉不住气。她真的就越过墙去。
唐乃子一面运功调息,一面紧密注意后院打斗之声,事态发展,一旦发现不妙,便马上催动内力,拉奏二胡,希望能儆示唐烈香回头是岸。
——趁还有后路能退。
可惜,唐烈香已作了选择。
她一旦走了进来,没有无情,就没有后路可以退。
也许,在蔡卞“太保府”主力还未倾尽*到之前,唐乃子或者还可以强加扯走唐烈香,全身而退。
可是,她连二胡尚未收好,已遇上了一个人,阻了她一阵,一阵子。或者说,那人“遇”上了她。
不,找上了她。
唐乃子知道她所住的地方,机关有几重。何况,“少保府”是什么所在,当然门禁森严。看来,蔡攸是提供了一个清雅幽闭的地方,名为“五一七”,那只是一个代号,这地方正好供她养伤,让她母女,好食好住,好睡好穿,但实际上,这儿任何人出入,若未经少保夫人同意,不是能出不能进,就是能进不能出,不然就是进不了出不得,横死当堂。
也许,只通往院子舒舒气还是可以的,但要直赴“五一七”,不但谈何容易,也比上蜀道还难。
可是,这人一下子就来到这儿。
一下子就来到她面前。
她知道这决不是“少保府”的人。
她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她一嗅就嗅出这人决不简单。
——“少保府”决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当惯了奴才,无论他趁主子不在的时候怎么撑,还是撑不住能真正自主那个味来,脱不了当惯奴才那种味道来。
这个人则完全不同。他的气势独特。——最独特之处就是:他根本不像是个“人”。或者说,人类。她听说过这个人,这个“怪人”。
这是唐乃子心里的感觉。
她曾经遇上一个真正让她心动的男人:那人像是一个英雄,令她无由的心倾,但后来变得像个仇人,使她深心饮恨。
她也遇上过一个像是彬彬君子的人物,结果,最卑鄙的无赖也抵不上他的下流无耻。
就是前者让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再也不敢轻易为人付出真情。
便是后者令她了解什么男人才是真正的“虚伪”与“可耻”,使她懂得一句话:“天要下雨人要犯贱,是谁都阻拦不了的。”
但眼前这个人显然不是。
他不属于任何一类。
他是不能分类。
“二胡是你拉的?”
他炯炯有神的看着她,劈面就这样问。
“是。”
如果不是见此人如入无人之境,她一手暗器就招呼过去,才不会回答这个人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奏‘此情可待’?”
“什么?”
“此情可待。”
“谁跟你此情可待!?”
“你刚才奏那曲子:”那人用手指了指她的二胡,“此情可待。”
“哦,这曲子叫‘此情可待’么?”唐乃子道:“我还以为叫‘追忆’。”
那人冷哼一声:“那是我和小白合谱的曲子,你怎么会奏的?”
“哦!”唐乃子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了:“你找小白?”
那人忽然紧张了起来:“小白在哪里?告诉我!”
唐乃子住在“少保府”久了,她也侧闻了一些事,更是发现了一些奇事,知道轻忽不得,当下沉住气,道:“你找她干什么?”
那人的脸容一下了扭曲了起来,他脸上本来好像平静无波的湖水,却忽然给一石击碎了宁谧,皱纹一波一波的折叠漾散开来,又似海浪一样,一波比一波更壮阔,可是,忽然又给抚手折合,又恢复了成波平如镜的颜脸:唐乃子从来没有看过人的脸会在刹那间有那么强烈变化的。
“你告诉我,她在哪里!”他嘶声道,“没有她,我就虽活犹死!”
“没有她,我就再没有后路可以退,再也回不去了!”那人嘶吼道:“告诉我,她在哪里!?”
唐乃子压根儿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可以体会对方的情急。
“这儿姓白的高手有两个,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他们武功都很高,人也很冲动,都是性情中人。”唐乃子试探着问,“你不是找他们吧?”
那人气咻咻道:“我找教你这首曲子的女子。”
唐乃子心中忖:果然。“哦,那是姓温的,人是绝顶的漂亮,但名字很怪,是三个姓氏,合并起来,就叫温李白。不过,我们都习惯唤她作:‘小白’。”
“小白,小白。”那人气管里发出了一个像哮喘一般的呼啸,“一定是她了,一定是她了……她在哪里?她——她在哪里?”
唐乃子一身是胆,平生胆大,但却不知怎的,一直不敢与那人四目相对,而今,见那人明确的有求于她,她才敢盯着对方的眼睛,反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敢不告诉我!?”那人冷冽的说了一句,忽然又转温和起来,“你中了毒,积毒未消,新毒又深;你受了伤,内伤未愈,余患复发。你帮我,我也可以帮你。”
唐乃子听得心中一动。还一震:他怎么一眼就能看出来——!?
于是不敢怠慢,道:“她就住在‘少保府’的‘轩辕轩’里,”她说,却觉得不知怎的,眼睛一阵赤痛,人也一阵晕眩!
“她的兄长就守在她的隔壁,此外,这儿门禁森严,温小白姑娘是一向给严加保护的,你不一定找得着她,找着了也未必见着,而且少保府高手如云,你也未必对付得了——”
“好,谢谢。”那人脸容又一波一波的扭曲、伸展、起伏不已。“你说的‘轩辕轩’何在!?”
唐乃子立即大致描叙了一下。
但没想到的是,她说着说着,忽然发现那怪人仍在直视着她,她一对上了视线,心头一震,恍惚间,竟一时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她,失神了。
她的视野模糊了,不,清晰了,眼前却出现了: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布满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建筑物,然后,两座相对相倚的最高大楼,在冒着冲天浓烟,在吐着可怕火焰,有一幢还给异物拦腰截断,那异物也在燃烧着,建筑物逐渐轰然垮塌,街上人们,争相走避,凄惨莫名……唐乃子忽然觉得自己就身在其中,在另一处高楼遥望这一切,也不知怎的,她一生*戮无算,*人如麻,此际忽然热泪盈眶……遍地繁荣,竟成一片残垣败瓦。
然后她又仿佛看见自己比较熟悉的地方,一个杜鹃花似海,繁花盛开,澄湖碧水,清净天池,忽然变成满目疮痍,泥泞污染,残桥败架,散布腐朽,垃圾遍地,完全变成了一个面貌……遍山风流换来一池污浊。
另一处黑发黄肤的一群人,忽然穿上古服,*气腾腾的往一神庙步去,看似参拜,势似赶赴一场久违了的仇*……另一地也是黄肤黑发,游冶于海角丛尔小岛,那花园里有巨大形貌的大耳老鼠、懒猫和癞皮狗不等,穿梭活跃其中,但那些游客观众,有的攀栏爬树,有的喧哗呼啸,有的就在草地野餐小解,有的干脆在长椅瞌睡、赌博,还有的干脆脱掉鞋子,当众捽搓脚趾……遍地风流,也遍地邋遢。
又一处只见黑发黄肤的百姓,人人讨论一些唐乃子完全听不懂的人,看不懂的事,没听说过的东西,以及讨论一本唐乃子闻所未闻的书:谈话争先恐后,唯恐不时麾或落后。内容涉及,什么大分歧象征,什么摸拉泥沙的微笑,什么爷须复活,什么神母马力雅……都说是什么密码,每件事都很有学问,十分神秘,反正唐乃子都听不懂,只知人人争论不休,个个的高见,意见从来没人听,只抢着说,争着表现……甚至有人放言,这时候,再来讨论自己文化里已拥有的唐诗宋词、史记汉书、诸子百家、琴棋书画……已经是太落伍了,太老土了,居然是要给当时当地的人鄙视的……!?
这到底是什么世间啊!?
——人间,还是地狱?前世,还是来生?
唐乃子觉得很迷茫。非常迷惘。
为什么会这样?
——人,怎会变成这个样子!?
到她忽然警省的时候,那人已不在眼前。
——奇特的是:她的内息,感到这几年来前所未有的舒畅与充沛。
(他到哪里去了?)
(是去找小白了吗?)
(少保府能任由他找谁就找谁的么!?)
(怎么自己会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异象!?)
(刚才的幻象,只是因为自己走神了吗?)
她可管不着那么多了。
她听到喊*和砍*声。
她知道女儿已投入了墙那边的战场里。
她别无选择:她飞身赶去——*入战场。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