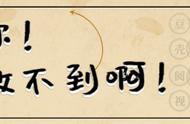野孩子乐队演唱的《黄河谣》,曾被误以为是民歌改编,其实是野孩子原创的。/《乐队的夏天》
2006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城市民谣的纯真年代》一文,那正是“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时候。《贤良》《在路旁》《这个世界会好吗》……民谣圈里浪潮滚滚,人们把这一年称为“新民谣元年”。
但在文章末尾,作者不无担忧地提到:“它的出现,能否改变流行音乐的格局,并不是首要问题,而纯真年代的城市民谣,一旦进入主流操作的层面,会否如校园民谣末期的模仿和迷失,才最让人担心。”
十几年过去了,这段话仿佛是已经实现的预言。民谣的出圈与堕落同时发生,在最初那帮民谣听众看来,这一切可能比想象的还要糟。

离开京圈,还能不能谈民谣?
和文学、电影一样,大多音乐往事,也都要追溯到北京。上世纪末,所有年轻人都想去北京,那些热血和理想,只有到北京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音乐就像普通话的推广一样势不可挡,偶有唱方言的,也多是普通话的近亲。
五条人还被认为是一支民谣乐队的时候,曾被《南方周末》授予“年度音乐奖”。
《南方周末》是这么说的:“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

获奖专辑《县城记》,是五条人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豆瓣音乐
这份恩赏余波不绝,马东至今还在追问五条人,你们知道得这个奖是因为你们的歌词吗?
谈论歌词比鉴赏曲调门槛低多了。五条人用方言吟咏的是南方的土地,而这曾被北方的影子遮盖多年。
乐评人杨波深爱五条人,但对于他们的获奖十分诧异,当年赶着给五条人颁奖的公共媒体里,“不乏《县城记》面世时我拼命向其推荐望其推广而其以‘他们太小众了’为由拒之的媒体”。
在杨波看来,那些奖项不过是所谓的“专业权威”显摆话语权和超凡品味的机会。“作为一份公共媒体,它一年仅选出的一张唱片应以公共性为前提,这是只做了一千张的《县城记》恰恰缺乏的。”
相隔十年,如今五条人一次次淘汰和复活,与当年的授奖如出一辙。节目里的嘉宾个个都爱他们——爱他们的不羁、风趣,但节目里的嘉宾也个个都不屑他们,五条人在台上演出,他们不用耳朵倒用眼睛,只看歌词板和舞姿摇摆。
这是北方音乐圈一贯喜好,他们爱前辈(京圈前辈),爱世界(西方的、所谓先锋或实验的),甚至也说得上爱民族(尤其是方言、民俗音乐),但对于像五条人这种脱离北方圈子传统框架的音乐和音乐人,似乎总带着一种遛鸟盘核桃的观赏劲儿。

无奈,一夜之间全网遍地都是“阿珍”和“阿强”。在节目里被嘉宾们避而不谈的五条人的音乐,竟然受到如此多观众的热捧,比起节目里那一亩三分地,缴械投降的五条人倒真是立足世界,放眼乐夏。
当年万晓利唱:“我真的来到了北京,背的不是书包却是吉他。”十多年前,当无数心怀理想的民谣音乐人奔赴北京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接受了京圈音乐文化的宰制。
如今的朋克教父、SMZB乐队的吴维,曾在北京混过几年,后来还是回了武汉。“顶楼的马戏团”乐手梅二评论他:
“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梅二与五条人交情不错,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演出时经常互相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