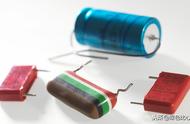野人山的大劫难,震惊全军,轰动全国。
记者、作家向朗姆茄纷至沓来。画家叶浅予先生也来了,听说有一个女兵爬出了野人山,特地从军部赶来给我画画,准备拿到重庆去展览。
画完后,叶先生把画像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画夹里,抽出一张送给我。
我当时不知道叶先生的名气,只觉得重庆派来的一定很有名,把这幅画小心收藏了。
没想到,正是这幅画,在我后来最绝望的时候,投来了第一抹曙光!
朗姆茄有一个美军医院,师里原有女兵都死在野人山了,国内运来的补员兵也都是男的,我成了这里唯一的中国女兵。
这偌大的军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女人,就是我们廖耀湘师长的太太,她是乔装打扮随驻印军抵达的。
廖师长夫妻二人感情很深,廖夫人在战争时期也一直跟随左右。他们特别接见了我这个特殊女兵。
劫后余生,在印度,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到1942年底,至朗姆茄训练的兵力已达32000多人。训练场上*巨大的标语牌:“下劲苦练,*回缅甸!"
第二年秋季,部队开到野人山边缘地区,进行丛林适应性训练去了,每个连队只留下个把弟兄照看营房,许还山已经跟着部队出发了。
这时我已怀胎数月,即将临盆了。在美军老医生的帮助下,我的女儿哇哇落地,我给她取名叫“竺兰”,纪念她的出生地。
伴随着孩子的出生,中国远征军报仇雪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战斗打响后,廖夫人邀我陪她前往印度的旅游胜地葛伦堡度假,我人在风光秀丽的葛伦堡,心却日夜牵挂着野人山中的战事,牵挂着连孩子的面都没见着的许还山。
好在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我与廖夫人成天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在豌町西南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胜利贯通。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驻印军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怀抱。
在朗姆茄留守处的人员,也接到命令,由中印公路回国。消息传到留守处时,我抱着女儿竺兰高兴地跳起来,激动的泪水不知不觉夺眶而出。
出国已经三年了,日思夜想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怎么不叫我激动万分呢!
车队登上畹町大桥,望着手持鲜花,夹道欢迎的人群,我的双眼又一次模糊了。当初出国时,也是此情景。
在云南曲靖,我与许还山匆匆见了一面,战火又把他招向湖南芷江。我们在芷江相逢,随后开去上海,不到三个月,又开赴东北战场。
1946年,我孤身一人在上海分娩了第二个女儿。
一个无职业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不知为何,东北战场上的许还山一直杳无音信。不得已,我带着两个女儿,踏上了千里寻夫的征途。
东北战事吃紧,部队调动频繁,我拖着两个孩子在战火中辗转一年多,也没能见到许还山的面。
我想,肯定是他军务很忙,不好请假。
女人的心,常常太善良,太天真!

1947年尾,我在锦州附近的汤干子镇,终于找到了许还山,他是团里的卫生队队长。
我一路奔波虽很疲劳,但心情激动得不能入睡,靠在床铺上等待丈夫的到来。直到深夜,他才回来。
可他轻轻推开门后,见到我连句话都没有,看了眼孩子后,就木然地坐到凳子上。沉默许久,才望着我说:“桂英,我对不住你。”
许还山有了其他女人,对方已经*了,他说不能对不起她。许还山走了,我带着一对孩子睡了,泪水湿透了枕头。
第二天我含泪登上返回沈阳留守处的火车,东北解放前期,在许还山的安排下,我回到他安徽老家怀宁县的乡下。
家中只有婆母一人,由于祖上传下了一些家业,家境还算殷实。不知是婆母性情怪癖,还是许还山有话于她,我们的到来,婆母多有不悦。
到1948年春,许还山从东北给婆母来信,让我回长沙,随信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合影。
婆母从此翻脸不认人,成天骂我死不要脸,赖在她家。亲人的侮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多少个夜晚,我想跳水自尽。
可看着床上熟睡的女儿,孩子投胎投错了门,我解脱了,她们尚小啊。不能重走我这个没有母亲的老路。
在婆母的欺辱下,我忍无可忍申请了离婚,在新政府的保护下,家中的不动产房屋和田地一分两半,与负心的丈夫和狠心的婆婆一刀两断了。
好在我有些文化,镇上小学聘请我当了一名老师。后分配到容岭小学执教,在这里四年,我也经人介绍,与一位姓谢的基层干部结了婚。
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起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可生活再艰难,又怎能与野人山中的困难相比呢!
然而,一个政治风浪打来,我被吞没了。
“反右”运动开始,老师都要向党坦白交待历史问题。我想来想去,自己一个孤儿受尽磨难,有什么可交待的,便把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讲了出来。
这下可闯了大祸了!
远征军?远征军是干什么的?一个女人出过国,耸人听闻!
便顺藤摸瓜,审问起来:“你出国究竟干了哪些事?”、“你与外国特务有哪些联系?”
该说的,我都交待了,稀奇古怪的传闻在教师间散开了,说我是暗藏在大陆的女特务,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钦佩我,我的老实是装的。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不知所措。会场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我成了批斗对象,主持人让我把黑历史都交待岀来。
小组批斗后,大组又进行复斗。我被批斗数月,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从未有人告诉我。
就这样,我被下放到了偏远的农村,第二年老谢也跟着我下放了,不久他又染上了肺结核病,被肺病活活折磨死了。
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一个也没躲过。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几度来抄我的家,我怕叶浅予老先生为我画的画被抄出来,给我罪加一等,便含泪把画和照片全烧了。

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才看到了希望。
小女儿不能上学,大女儿不能入团,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我一辈子抬不起头不要紧,让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我死不瞑目啊!
可我等了七年,那场大战仍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着,没人提及,我的平反也就无从谈起。
时间进入到1985年,这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总感到这年要发生什么事儿。
这种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
在这一年,党和国家开展了隆重的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的讲话、文章中,对中国岀兵缅甸作战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省城一家医院工作的二女儿来信告诉我,她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孙立人在缅甸抗日有功获奖的情况,虽然夹在报缝里只有几百字,它还是令我们全家欣喜。
因为它是一个信号:中日缅甸之战可以公开报道了。
护士长何珊临死前的一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她要我把野人山大劫难告诉世人的遗嘱。
是啊,我这个侥幸活下来的人,现在是时候把那段经历公诸于世,这也许就是老天让我活着的意义。
于是,我背着子女,偷偷地动笔了。
我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没有栖身之所,靠在子女身边轮流生活,文化程度又不高,要再现四十年前的那场经历是困难的。
我从儿女们给我的零用钱中节省下一点钱,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用白纸装订了本子,到哪里就背到哪里。
夜晚孩子们都睡下了,我便开始一点点回忆,一点点记下来。在泪水浸泡中,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回忆录。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叶浅予先生仍然健在,是北京的大画家,便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推荐发表我写的回忆文章。
叶老仍记得我这个爬出野人山的女兵,他立即把我的回忆文章转交给《新观察》杂志社。不久,文章在《新观察》刊登了岀来。
第一次尝试的成功,使我的胆子更大了。
我多次找有关部门,申请组织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査,给予平反。接待我的同志一翻档案,说,你有啥要平反呀,本来就没有给你定什么罪,戴什么帽子呀?
我的档案里只有关于“错误思想严重"、“历史问题复杂”的记载。
天呐,这些年来,批了斗,斗了批,都是因为乡下一些人乱来一气。
1990年6月的一天,当我从怀宁县信访办公室,用颤抖的手接过退休通知书和退休金时,我热泪盈眶。
这年我已是七十高龄了。
晚年我努力清醒地活着,接受了很多媒体、志愿者的采访,子女们不理解,他们担心我激动,害怕我出事。
我一遍遍重复讲述那段地狱中爬行的日子,只为世人不要轻易遗忘,那些永留野人山中的白骨与忠魂。
他们还挣扎着想要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