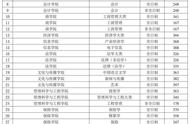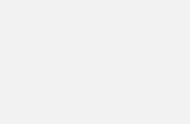作为白家的长子,白孝文的降生,为白嘉轩带来了全部的信心和希望,他自出生起就注定要成为宗教的样板。
白嘉轩非常“严厉的注视着孝文的行为规范”,从日常言行到行事谋略,甚至到床第之事,他都以“未来族长”的标准对其予以约束。
他的一番苦心教诲和监督,表面上看是成功的,成年后的白孝文,行为端庄,非礼不为,无疑是白鹿原上的“道德模范”。
在父亲的控制下,白孝文表面上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早已生出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强烈反叛。

一旦遇到同样反叛的田小娥,出轨和欲罢不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田小娥虽然在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压制下,成了人们指指戳戳的“烂女人”,但她毕竟是秀才之女,生于书香门第之家。
从小在秀才父亲身边长大的她,自然会受到诗书的熏陶和影响,嫁给郭举人做妾后,虽然没有得到善待,但郭家终归是富贵人家,田小娥还是跟着长了不少见识。

诗书的熏陶和见识,让田小娥有别于其他女人,她不甘于逆来顺受,她要用叛逆和不羁来反叛这个压制人性的社会。
如果抛开身份和境遇,单从出身和幼时的生长环境看,白孝文和田小娥无疑是登对的,一个是秀才之女,一个是饱读诗书的世家公子,两个人在精神上是非常契合的。
白孝文从她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满足。
田小娥身上的叛逆和不羁,更是白孝文家里,那个大他三岁的婆娘所不具备的。
没被田小娥引诱前,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白孝文都是压抑的,情感上他和大自己三岁的婆娘无话可说,生理上,为了自己的身子,他要听从父母还有阿婆的管束,连床第之事都不能自己做主。

新婚不久,父母看他脸色灰暗,眼睛周围总有一个晕圈,便推出阿婆限制他和媳妇的床第之欢。
阿婆先是教训孙媳:
“马驹(白孝文乳名)十六还嫩着哩,你要是夜夜没遍没数地引逗他.....把他身子亏空了,嫩撅了,你就得守一辈子活寡”。
然后夜夜坐在白孝文窗外:“马驹俺娃好好睡,婆给你当狼”。直到窗内传出白孝文匀称的鼾声才回屋去睡。
他的父亲白嘉轩更是干脆地训斥他说:
“你要是连炕上那点豪狠都使不出来,我断定你一辈子成不了一件大事。你得明白,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
长期处于封建礼教和人欲禁锢下的白孝文,对那些被动接受的道德规范,从内心是憎恨、排斥的。
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不是人们眼里的“道德模范”。
田小娥的出现,虽是诱惑而且极不光彩,但她身上的叛逆和不羁,恰好极大的激发了白孝文内心压抑已久的男性渴求和反叛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