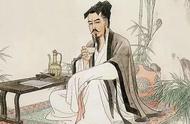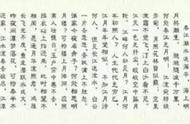自古以来,物极必反,对诗的评价也一样,当一首诗被太多人吹捧,就会有人跳出来反对。《春江花月夜》被网络上许多人吹捧为“孤篇圧全唐”,于是便有站出来说它被高估了,甚至有人认为《春江花月夜》就算不上是一篇优秀的诗作。
“孤篇压全唐”的说法,显然是标题党所为,因为没有任何一件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压倒别的文学艺术作品来获取自己的艺术地位。而那些认为《春江花月夜》不算优秀诗作的人,要么是没有仔细品味过它的美,要么就是故作惊人之语,博人眼球。
我认为,《春江花月夜》在诗中的美学高度,相当于《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美学高度。不过,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没有其它小说能达到《红楼梦》的美学高度,而在诗中,前有《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后有李白杜甫李商隐的顶尖作品,都能跟《春江花月夜》一样达到诗的至美境界。
当然,这都是一己之见,最重要的还是一起来一个字一个字都读《春江花月夜》,看它能带给我们怎样的美的享受。我个人学识有限,以下内容,是我在整理前贤的相关文章的基础上,融合一些自己的看法。

先说张若虚其人,关于张若虚的记载很少,仅知他是扬州人,曾当过兖州兵曹这样的小官,神龙(武周皇帝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的年号:705年正月—707年九月)年间,张若虚与贺知章、邢巨、包融这几个吴越之士,名扬上京,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
张若虚的诗,仅存两首,另一首为《代答闺梦还》,平常无奇。
《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旧题,属“清商辞曲”中的“吴声歌曲”。最早以此题写诗的是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但其诗作已佚,在张若虚以前,还有三个人留下过《春江花月夜》诗,分别是隋朝的隋炀帝和诸葛颖,以及初唐的张子容,但他们写的都是五言四句或五言六句的短篇,而张若虚写的是七言长篇。
张若虚虽在当时有些名气,但没有留下诗文集子,在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中,也没有选他的诗,《春江花月夜》一诗,是被选入宋郭茂倩(1041年-1099年)编的《乐府诗集》,才得流传下来。
二、《春江花月夜》细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全诗,共十八联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字,从押韵的情况来看,这首诗每四句押一个韵,全诗就像由九个独立的七言绝句串联起来的,但又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从内容上来看,此诗可分为五大段。
第一段为第一句到第八句,总写明月之夜,春江潮涨,以及春夜花林的美景,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美好意境。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水自上而下,潮水自下而止,两相鼓荡,便连成一片。一个“平”字,表面上平淡无奇,却写出了浩渺无边的景象,有千钧之力。浩渺的江海上,一轮明月与潮水一同升起。地球上的潮汐现象,本就是海水受到月球的引力而产生的,当然诗歌不是科学论文。明月与潮水共同向上升起,具有一种动态的美感,用”生“而不用”升”,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一种生气,能引起人精神情感上的生发之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滟(yàn)滟:月光随水波荡漾的样子。明月升空,月光撒向大地,因为水面反射的月光更多,所以江上的月光更加明亮,更能吸引人的目光,水波流动,造成了种月光随水波流动的视觉幻象,于是月光与江水,将诗人的目光带向遥远的地方,于是诗人发问,哪里的春江,没有明月照射呢?
王世海说:“何处”是问,问便涉及到所问的主体。主体者何? 不是春江,也不是明月,而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个主体“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感角色,而是一个具有明确主体意识的人,是他主动来问春江花月夜。但是,无论春江还是月夜,是没有意识的,是不会回答“人”的问题的,所以,人之所问,问的不是诸物,而是自己,是自己在这些诸物中到底在做么,又在追求和实现什么,从而引发出的是“人”对自我存在状态和价值的思索和探究。这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宛转:曲折。芳甸(diàn):开满花草的郊野。甸,郊外之地。霰(xiàn):小雪粒。
这两句点出“花”字,江水绕着开满春花的郊野流转,明月照在花林之上,散射出粼粼光彩。一般认为,霰在这里的意思,是指花反射的月光就像小雪粒反射的光,我认为霰是在传达月光的颗粒感,光线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雾气中),会让人看到很多微小的颗粒。花在如霰的月光中,就有了一种朦胧的感觉。
花的出现,给春江月夜,带来了温暖艳丽。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汀(tīng):水边平地,小洲。
上句以霜喻月,即写月白如霜,又含着月光带来的微寒之意。莫砺锋说:“妙在诗人并不说月光如霜,而是直说‘空里流霜’,从而把诗人在月光中久久站立的感觉真切地传递给读者,读之浑如身临其境。”因为是春天,所以只是微寒,所以不觉其飞。
下句写远处沙洲上的白沙,与月光浑成一片,看不分明。
《删补唐诗选笺释会通评林》中,周启陞(shēng)说:“空里、汀上二语,状月光极静幻。”
第二段从第八句到第十六句,写空中明月引发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纤尘:微细的灰尘。皎皎:洁白。月轮:指月亮,因为月圆时像车轮,所以称为月轮。
“江天”二字,总揽前八句所写景物,月夜之中,是看不见颜色的,只有明暗,于是天地之间,也就只月光一色了,于是天上的那一轮明月,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事物,而对明月的注视,则将人引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徐增《而庵说唐诗》:“江畔那一个人最初见月,江月又那一年初来照人,见人自人,月自月,初无交涉。自因月之有照,人之有见,遂弄出无限风光,无限烦恼来. 直无可奈何之事也。”
谁人第一次看见明月?自有人类,抬头便能看到明月,诗人问的显然不是这个,而是在问,第一次看到月亮的人,他为什么要看月亮?他看到月亮时内心在想什么?是不是也与诗人看到月亮时的感觉一样?只有当月亮对人类产生了影响,人类开始真正思考月亮,人类才是真正第一次看见了月亮。
这一问将我们的视野、思绪由眼前景引回到了“见月”的最初时刻,引回到了人类自我觉知、觉醒的那个原点。如此一来,眼前景象与历史时空中的原点便得到一次最直接的汇合、沟通,而人的所思、所感、所望也在这种共在时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铺展、生发、会通。
明月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照耀人类呢?这一问将问题推向更深广的客观宇宙,因为不管人思不思考月亮,月亮始终高照于空,这一问相当于问,人类诞生于何时?明月诞生于何时?甚至宇宙诞生于何时?
第一问问人生,第二问问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