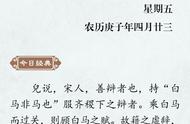那公孙龙在论证这一话题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诡辩”呢?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他将“白”和“马”这两种概念进行了拆分,这是“离坚白”派经常使用的论证方式。他认为,白是颜色,而马是形态,颜色和形态的组合肯定不能用单一的形态来表示。
在此之后更是进一步举例。如果是寻求形态的“马”,那么黄马、黑马都符合要求,但是如果是寻求白马,那么黄马、黑马就都不符合要求了,如果白马是马,那么两次所求一致,怎么会出现结果的不同呢?
面对诘难者从公孙龙的逻辑出发,提出“所有有颜色的马都不是马”的反问,公孙龙的解释就又回到了“白”与“马”是“命形”和“命色”的观点上来,形成了逻辑上的死循环。
而针对诘难方将“白”和“马”视为同一事物不同属性的观点,公孙龙的论证更为巧妙。
公孙龙利用上一回合对方的论点来驳斥这一观点,既然对方根据公孙龙的观点提出“黄马”也不是马,那么就是认同颜色和形态是两种事物。既然将“黄马”和“马”区分开来,那么又将“白马”和“马”统一看待,这不是逻辑上的矛盾混乱吗?

而公孙龙最终的观点其实只有一句话: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也就是说,增设了限定条件的概念和没有限定条件的概念是不同的。
可以看到,通过两个回合的激辩,其实公孙龙所说的“白马非马”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白马”不是“马”,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区分概念的内涵,将代表抽象概念的“能指”与代表具体物象的“所指”区分开来。
这种研究语言的方法,西方索绪尔等人从17世纪后才开始进行系统地研究,而中国在公元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一问题了,只不过因为“实用性”的原因并没有进行下去。
《坚白论》:名家“离坚白”派用以阐述政见的思维逻辑和“白马非马”并称的逻辑命题,公孙龙提出的“离坚白”同样十分著名。
这一争论是通过一块坚硬的白石引起的,公孙龙认为,同一块石头中,“坚”和“白”是分离的,这显然又是一个违反常识的观点。

公孙龙在这一篇作品中,先是通过“白”是视觉、“坚”是触觉的分别,来说明“坚”与“白”是不可同时被感知的,这就是所谓的“离”,其针对的是诘难者所认为的“坚白”两种特性共存于一石之中不可分离的观点。
而在诘难者举出“坚”是石之坚,“白”是石之白,所以两者是共存于“石”中的观点后,公孙龙认为,“坚”与“白”不是石头固有的属性,而是特征。不会因为没有石头就不存在“坚”和“白”两种属性。所以,“坚”与“白”的分离,才是形成了事物共性和个性的差异。
并且,公孙龙借这一观点提出,感觉是不可信的,只有思维的论证才是真理。一块“坚白石”,拿在手中的感觉不如经过思考之后的逻辑更为真实。
名家“诡辩术”,其目的和作用都有现实意义公孙龙这等名家人士,其实是想用“诡辩”的方式来制止刀兵。
诸子百家之中,所有的主张其实都是为了现实服务,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来终结乱世。像道家用“无为”,法家用“刑律”,儒家用“礼义”,而名家所用的就是“诡辩”式的思维方式。

公孙龙和惠子一样,都主张“偃兵”。他们认为导致乱世的出现,是因为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征伐是没有必要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用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来,国家间的战乱其实就变成了双方的一次辩论,谁能占据道理,就看哪方的辩士更为优秀。其所依靠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看重的“名分”,希望以此来使得“攻伐”一方变成“无名之师”,进而消弭战争。
这就和孔子所说的理论有相通之处:
《论语 ·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种想法自然是失败了,但是其逻辑思维的精彩论证却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并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程。
后世很多大儒都对《公孙龙子》进行评价,比如儒家的荀子就曾评价名家:
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类似的评价历来多有,但有趣的是,各朝代学者都是否定公孙龙“诡辩”的行径,却没有人能在逻辑上找到他的漏洞。所以有人感叹,如果最初所学不是儒道墨法,而是名家“诡辩”,那么同样会认为儒墨等学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