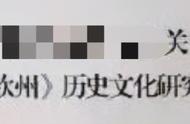最近决定重新去读一些经典,今天想起上大学时特别喜欢的阿城,于是重新读完他的代表作“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阅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以前总是莫名崇拜经典,尤其是看《棋王》,当时惊为天人,一句句“卧槽”在心里百转千回,觉得写小说写到这个境界,就是绝顶高人了。

今天再看,依旧有震撼的感觉,尤其是写斗棋的那段描写,感觉那些人物都能站起来自己走动,可谓是栩栩如生。但不如之前的是,中间有好几个地方,我竟然卡顿了一下,尤其是阿成在试图用一些比较大的词来*的时候,读起来总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读棋王还尚可,再读树王,孩子王,这样的虚张声势就显得更为明显,总觉得它的表述里有慌慌张张的东西。
后来在看阿城的自述时,我发现阿城自己也发现了自己文章的问题,并且毫不讳言:
《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风流”系列,虽然在学生腔和文艺腔上比“遍地风流”有收敛,但满嘴的宇宙、世界,口气还是虚矫。当时给一个叫俞康宁的朋友看,记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随即避开小说,逼我讨论莫扎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当时他已经将三个乐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练完,总觉得第二乐章有不对劲的地方。我说第二乐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属于撒娇式抒情。这一瞬间,我倒明白了《树王》不对劲的地方。

看完这部分,不得不感慨阿城这个朋友很有点水平,并且阿城也能迅速能归纳出一个“撒娇式抒情”,不得不说自省能力很强。文人常常矫情,尤其在写作的时候往往陷于一种做作的表演欲中。如果真的到了圆融的境界,那么情感不需抒发就能流溢于文中。最可怕的就是,矫情而不自知,这才是写作最大的避讳。

所以写文章如同谈恋爱一样,越是深情,越要克制,否则情绪一泻千里,于人于己都是负担。所以李敖说,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他是懂得这个空间的。哪怕胸中丘壑层峦迭起,越是在创作中懂得如何留白,给作者和读者之间留一个想象空间,容人揣摩、解读、自我发挥、“我注六经”。
所以阿城的文章,功底深厚,但那些卡顿的地方,确实是有“撒娇式抒情”的成分,有一种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牛逼的洋洋自得。这个毛病,我感觉我更严重。有时候已经不是简单的撒娇,而是要满地打滚要亲亲抱抱举高高了。同样矫情的人可能会心有戚戚焉,但其他人看了怕是要做噩梦的。
所以说过犹不及,矫情太过,与毫无感情的表达,一样是文章的大忌。真正的情感是自然而然流溢出来的,任何的刻意雕琢或者强行造作,都在影响我们的表达。

留得余韵三分在,好使船行到尽头。自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