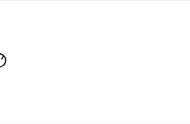从佛学入手研究佛教史的人会有一个成见,就是认为不懂佛学和梵语就研究不了佛教史,研究佛教史离不开佛学和梵语。所以,这一类人(包括我在内)得到很晚才能认识到吕澂(1896-1989)之外还有陈垣(1880-1971),作为佛教史家的陈垣并不精通佛学和梵语。这个道理挪到西藏学上也是一样的。从前,我在西藏学方面是只读图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和王森(1912-1991)这类学者的作品的,直到很晚才认识到图奇之外还有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王森之外还有柳陞祺(1908[一作1909]-2003)。正如柳在《应当争取有一个更大的藏学研究队伍》(1991a)和《我学习藏族史的经过》(2002)中总结的,佛学(包括佛教)和藏语不是西藏学的全部,西藏学并非事事离不开佛学和藏语。

柳陞祺在拉萨
柳陞祺注意到,初到西藏的人都会觉得好像事事都离不开佛教,但是只要住的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凡是在西藏之外可以遇到的事情,同样都可以在西藏遇到,西藏人也是人,西藏并非那么特殊。既然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即使不懂佛学或藏语,也未始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研究。柳在《我的学习研究历程》(1986a)中更是提出,与佛学上的中观唯识之见,新旧密法之争相比,西藏的世俗政府组织,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学制,对西藏社会生活所起的影响反而要更大一些。其中的理由应该就是比起佛学上的宗见差别,组织和制度更能代表人类所共有的某种东西。柳还注意到,旧时西藏僧俗上层在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十分贫乏,乃至于外国人书中所常言的四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许多拉萨人竟懵然不知。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是和宗教纠缠在一起,甚至就连王统记、王臣记、宗派源流、名人传这一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传统史书,拉萨三大寺都视为“外学”,不让僧人阅读。柳陞祺的西藏学研究正是集中于剥离了西藏的特殊性而体现了人类共同性的世俗历史、政治、外交和社会这些方面。
柳陞祺生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简称民族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王森和邓锐龄(1925-2023)一起不仅代表着民族所在西藏学方面,也是在整个学术方面最好的传统。与现在社科院的科研人员或科研工作者的所谓科研成果不同,他们的著述都是经过长期广博涉猎后再专精化的结果。柳在四十五岁左右才真正开始对近代西藏史的科学研究,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他在西藏学方面的主要著述已经基本收进《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2008a,简称《文集》)。书名既然带有“藏学”和“汉文卷”的字样,说明柳的著述在藏学之外还有非藏学,“汉文卷”外还有“外文卷”(《文集》的《编后》说会有英文卷)。这种书名设计可能就是为将来出版“非藏学文集”和“藏学文集(外文卷)”留有余地的(本文在引用柳陞祺作品时使用的编号,请参看文末的《柳陞祺部分作品及相关文献编年目录》)。
至于坊间流行的《西藏的寺与僧(1940年代)》(2010a,2014c)和《拉萨旧事(1944-1949)》(2010b,2014d),内容其实全部辑自《文集》,本身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不仅如此,两书在选文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以《拉萨旧事(1944-1949)》为例,《“商上”》一文(2010b,71-77页)本来是属于考证性的文章,不知为何竟出现在第一部分“往事记忆”里。《“商上”》原题《浅释“商上”》,最初是提交给1986年8月在拉萨举办的藏学讨论会的论文,1986年7月14日完成于北京,有1986年7月社科院民族所的打字油印本(1986d)。与这个打字油印本相比,收进《文集》的版本不仅在文字上有不少差异,而且还多出倒数第二段里的一大段内容。另外,《拉萨旧事(1944-1949)》书名中的“1944-1949”似是给所选文章圈定了一个时间范围,但是书中第二部分“一组手稿”所收文章以及不属于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的两篇长文,主要讲的却都是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的“旧事”。

1986年8月在拉萨举办的藏学讨论会的论文
关于柳的生平史料,除《文集》所收个人回忆性文章以及与邓锐龄的往来书信外,还有侯艺兵摄影撰文的《柳陞祺情系西藏五十秋》(1999),民族所的讣告《柳陞祺研究员逝世》(2003a),伍昆明(1943-2006;柳陞祺于1964年招收的藏族史专业研究生)的《纪念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先生》(2003b),李晨升的《柳陞祺先生生平》(2003c),郝时远、格勒主编的《纪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2008b,简称《纪念论集》),以及十分重要的《柳陞祺先生致邓锐龄先生书信补辑》(2009,简称《书信补辑》)等。虽然柳的生平大体框架已在,但是还有不少细节有待澄清。就算是已知的部分,叙述也嫌不够详确。我购藏有多种柳陞祺的档案文件和亲笔书信,掌握或见过不少与其生平著述有关的稀见史料,它们对于发掘未知和更详已知都有较大的价值。下面就将这些档案、书信和史料刊布出来,并对其中所涉时地、人事、书刊等略做考辨,以纪念这位杰出的西藏学家去世二十周年,以及他与沈宗濂(1898-1978)用英语合著(实为柳独自完成,见下文)的《西藏与西藏人》(1953b,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出版七十周年。
《履历表》
我购藏的柳氏档案文件主要有三种表格,就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工作成果调查表》(简称《调查表》)、《履历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简称《评定表》)。三表均装于一个社科院民族所专用的牛皮纸纸袋中,纸袋上有墨笔写的“柳陞祺”三字,其来源是社科院民族所的档案。其中第二种《履历表》是复印件,字不是柳陞祺的,也没有填表时间。但是,从表的印制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于1977年5月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资级别变动情况”一栏后来补填(字体不一样)有“科研 四级 207元 1982.10.民族所评定”等来看,至少是填写于“文革”结束后从社科院成立到1982年10月之间。
在表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柳虽声明“文化大革命中,将过去日记,填写表格等散失殆尽,此次所填简历,全凭记忆,大致正确,年月等可能稍有出入”,但表中“主要简历”一栏所填的,还是了解柳氏生平的第一手材料:
1915-1921 杭州第五小学及高小 学习
1921-1925 杭州宗文中学(旧制) 学习
1925-1930 上海光华大学(包括预科一年) 学习
1931-1940 伪财政部松江及川康监[盐]务管理局 英文秘书
1940-1942 成都光华大学分校 英文讲师
1942-1943 成都光华大学分校 英文副教授
1944-1949 伪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英文秘书
1949-1952 印度国际大学 (自作研究)
1952-1958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讲师
1958-1959 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讲师
1959起 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最后三个阶段特别注出证明人是杨玉山(民族所管理科研的行政人员)。至于其他阶段为何没写证明人,柳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解释说:“我于1944年去西藏,1952年自印度归国,与旧时亲友,失去联系,关于归国前经历,除民族所李有义、陈乃文两同志能部分作证外,无法列举证明人,特此说明。”李有义(1912-2015)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和柳是1944年同时入藏的同事。陈乃文(1931[一作1933]-)是继沈宗濂之后担任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的陈锡璋(生卒年不详,原任主任秘书,有遗作《西藏从政纪略》[作于1963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九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116-150页,后又摘入内部发行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2月第1版,108-140页],颇为重要)的女儿,后来与长她二十多岁的柳陞祺结婚。
柳就读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时,于1925年春曾与同学一起谒见来杭的九世班禅(1883-1937),后来还撰有《忆九世班禅》(1994)一文记其事。此文初刊于《中国西藏》1994年第2期,收入《文集》时也做了标注,不知《文集》的《编后》为何又以为是“首次面世”(2008a,907页)。另外,检1926年9月出版的《光华大学章程》,在“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生”中有柳的名字(72页),证明《履历表》中填写的“包括预科一年”确为实录。1931年至1940年,柳分别在松江和川康(自贡)两地的盐务管理局工作,但没有确记何时由沪入川。根据柳在《缅怀老同学赵家璧》(1997)一文中提到的“1938年春,我离开上海到了四川”,可知他离沪入川的时间大概是1938年春。
据陈乃文口述的《西藏五年》(2007),柳在国际大学(陈文作“泰戈尔国际学院”)时已和她订婚。当时陈的父母(陈锡璋、赵克仁)欲回国,陈也想随之回国念书,但又不愿离开柳,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后经父母和柳的劝说,陈还是留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陈文作“国际学院中国院”)读书,并于1949年10月与柳结婚。两人在印时主要靠沈宗濂为合写《西藏与西藏人》预支的一笔费用生活。1952年7、8月间,书稿完成寄往美国沈处,在随后的两三个月中,柳陈二人在印度各地稍做游览,最后于1952年年底回到中国。回国后,陈进中央民族学院(简称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书,1961年毕业后进学部民族所工作,1989年1月退休。“主要简历”虽然填写柳在民院研究部(民族所前身)任讲师是从1952年开始的,但在“何时何地参加工作”一栏却填写“1953年春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
从《履历表》“家庭主要成员姓名、年龄、单位、职业、政治情况”一栏,我们知道柳陞祺有一子柳晓明,一女柳晓青(《纪念论集》前面图版部分第6页上部有柳与两个子女的合影)。但在“爱人情况”一栏,填的却是十个“无”字。从别处的资料来看,陈乃文后来与陈燮章(1933-2017)结了婚(2018),但不知结婚的具体时间。根据孔网上架的一封陈乃文因与新华通讯社产生房产纠纷于1986年2月21日致该单位的书信(https://book.kongfz.com/215702/3363469667/;2023年11月2日读取),其中已经提到她的丈夫是陈燮章,而非柳陞祺,可见当时她与柳已经不在一起了。该信还提到她的长子是“印度出生的归侨”,这个在印度出生的长子只能是她和柳的孩子,换言之也就是柳晓明。由于柳晓明生在印度,所以最晚也得是1952年(也就是柳陈回国之年)出生的,考虑到《履历表》说他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七岁,那么填表时间至少还可以上推至1980年之前(1952 27=1979)。如果我们的推测无误,那么柳陈二人可能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不在一起了。
从陈乃文《西藏五年》称“女儿晓青”,柳晓明、柳晓青合写的《〈西藏与西藏人〉及相关的人和事》(2008b,19页)以及柳晓青独撰的《西藏与西藏人》汉译本(2006,2014b)《译后》(写于2006年6月8日,256页)称“母亲陈乃文”,可知柳晓青也是柳与陈所生。柳晓青比柳晓明小三岁,也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但是具体年份不详。关于柳和陈不在一起的原因,柳氏兄妹没有讲过,《纪念论集》中更是没有一篇文章言及,包括陈本人写的《诚挚的怀念》,内中消息只能从柳晓青撰《淡定人生》中提到的“爸爸的一生经历了婚姻的变故,事业上的挫折等世间烦恼”窥知一二(2008b,26页)。
在“有何专长,懂何外国语文、民族语文,熟练程度如何”一栏,填有“英语(阅读、写作、口语,一般可以,但近年荒疏不少)法语(阅读专业参考书)”。早在光华读书期间,柳就是大学二年级国语英语演说级际锦标队中的英语队员(《光华年刊》第3期[1928年]),曾得校内英语演说第二名(同上)。有关柳历年参加校内和校际英语演说比赛的详细情况,还可以参看1930年出版的《光华大学五稘纪念册》卷一载记部分17、22、25-26、27、31等页。在1935年6月出版的《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的“文艺”栏,刊有《光华大学十年来之课外作业》一文(97-99页),在“智能之竞争”一项曾举曾克源、周宸明、柳陞祺等在英文演说及辩论方面的成绩为例(99页)。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柳陞祺英语口语能力之一斑。除《西藏与西藏人》外,柳还发表过不少英语文章,翻译过几种英语文学的古典名著(均见下文)。至于他阅读并研究过的有关中英、中印和汉藏关系的英语史料,我怀疑今后中国有谁能在准确性上超过他。

大学二年级国语英语演说级际锦标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