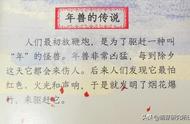王大鹏
通常来说,我们说某个人不说“人话”带有某种侮辱的意思,但是在科普这个问题上,“说人话”可能是科普人员需要掌握的一种技能。当然这里的“说人话”意指说普通公众能理解的话,或者说就是要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毕竟科研人员经过“十年苦修”而习得的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不太可能期望普通人能够“一夕顿悟”。那么这就需要我们采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从受众的视角去思考和看待问题;不过也有人并不认同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只满足了某些特定的受众,也就是具有很多“前置知识”的受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也许某些消费科学内容的人本身就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呢。而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的受众,或者说让更多的人理解科学,那么“说人话”依然是必须的。
在谈到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的很多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记者会抱怨说科研人员不“说人话”,不会讲故事。实际上,他们这里谈到的是受访人员无法将专业术语进行转化,这会使得访谈人员和受众“如坠云雾”,继而不得要领,我们也丧失掉了一次开展科普的机会。
当然,我们这并不是说术语不好,而是说术语应该用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学术交流过程中。这就好比足球运动员与球鞋的关系,不是说他们不能穿球鞋,而是说最好不要在室内穿球鞋,球鞋最适合的场所是球场上的草坪。术语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节省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共同体的集体认知。“隔行如隔山”,如果你不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你可能真就不明白某些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从学术交流撰写大众传播的时候,就需要警惕对专业术语的使用。实际上,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的诅咒”。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专有名词-Robust,中文翻译成“鲁棒性”,根据《牛津词典》中的解释,在科学中使用“Robust”时所采用的含义是一个系统或组织有抵御或克服不利条件的能力。但是在翻译成中文时,我们一时难以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即使是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可能一下子也完全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
那么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在向公众进行科普的过程中用到了“鲁棒性”这个词,但是又没有解释它的意思,我们又怎么能期望受众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呢?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其他的还有“视界”、“坍缩”、“量子纠缠”、“熵”等等。当然,在科普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一个核心原则,那就是科学性,否则就会走向“有普没科”的极端。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考虑的是,科学家或者科普人员所强调的科学性与公众视野下的科学性是不是一个意思,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有多少重合度,又存在多大的差异。
同时进行术语转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科研人员要对这个术语有着透彻的理解,也就是说欲让比人明白,需要自己先明白。正如卢瑟福说的那样,“如果你不能跟实验室擦地板的女工解释清楚你是做什么的,那这就说明你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
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干草堆中的恐龙》中说,“我将科普文写作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种为伽利略模式,主要是关于自然谜题的知识性文章;第二种则为圣方济各模式,主要是关于描写自然之美的抒情散文。”同时,他又在《奇妙的生命》中认为,“我在每一次撰写所谓‘普及读物’时,都极力维护一条个人原则。(“普及”一词的字面义令人向往,但现已被贬损,带有简化或添油加醋的意味,好像这样的读物应该如同轻音乐,读起来无须费神。)我相信——就像伽利略完成他那两部巨著,是以意大利语对话的形式,而不是用拉丁文写就的说教纲要;就像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写出他那高超的文章,不用一条术语;就像达尔文出版他所有的书籍,都是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一类科学读物,既适合专业人士阅读,也能让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读懂。尽管科学的概念数量丰富,意义多样,但不必有所妥协,不必经过扭曲的简化,也能以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较之学术出版物,面向一般读者的读物在遣词造句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但只限于将令行外人士感到迷惑的术语和措辞去掉,而概念的深度绝对不可有所不同。”
从上述这两段古尔德关于科普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在倡导“去术语化”或者对术语进行转化,其目的无外乎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
所以,好的科普要尽量“去术语化”,要尽量“说人话”。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来源: 光明网